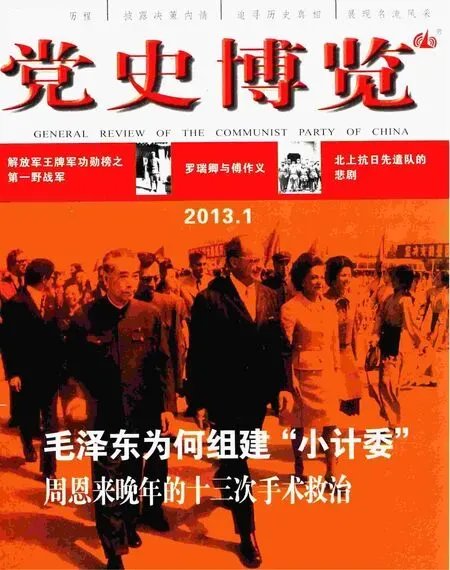板门店停战谈判采访追忆
■ 罗昆禾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
有幸被选中赴朝采访
1953年6月,随着朝鲜战争双方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组织记者团去开城采访。
我当时在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当记者。6月初的一天上午,社长方唯若找我谈话,告诉我被组织选入赴朝记者团,到开城参加停战谈判采访。得到消息,我兴奋得几天没休息好。虽然我1937年10月从河北任丘县入伍,抗日战争时期一直跟随贺龙在一二○师当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又随彭德怀从事新闻报道,但现在要到战火纷飞的朝鲜采访,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我到北京报到后了解到,记者团由京津沪各大报社选派的61名记者组成,由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处的邢石操带队。《人民日报》有李千峰,《光明日报》有方明等,军队记者有我和沈阳军区的杨清宇。女记者有三位,两位是天津《大公报》的,一位是新华社的。
记者团在北京集中后,乘火车到了安东(今丹东)。在安东休息、准备了三天,主要工作是看地图、材料,学简单的朝语对话。志愿军安东办事处根据总政的通知,给我们派来了警卫班、炊事员,办好了护照,还配属了4辆卡车、无线电器材、军用地图、枪支和粮食等物资。
6月22日下午,我们乘坐卡车过了鸭绿江。朝鲜边境检查站查验了护照后,记者团一行便进入了朝鲜境内。
我们之所以敢在白天行军,是因为新桥(原桥被炸毁)附近的防空炮火密集,加之敌我双方开战两年多以来,中国空军日趋强大,三八线以北的制空权已在我方手中,附近机场的我方战机可随时升空,敌机已不像战争初期那么嚣张。虽说比过去安全多了,但我们仍然小心翼翼,生怕路上出差错,出发前就做好了防空观察、疏散等预案。
由于工兵和当地群众的维护,公路比较平坦,也没有敌机扔下的定时炸弹、铁三角之类的破坏物。司机又是老手,夜间只开小灯就可以在公路上飞驰。车过新安州后,看到许多群众都在路边搭棚、挖洞而居。
新安州是朝鲜的蜂腰部,在志愿军把美军赶过三八线后,他们又想重演仁川登陆故技,妄图在清川江口一带登陆,从背后攻击志愿军。毛主席早料到了这一手,他在一次国务会议上说:“好吧,打就打吧。”有人说就他这淡淡一句话,就把敌人吓退了。其实,志愿军做了充分准备,调集了重兵,组成西海岸指挥部,深沟厚垒,构筑了坚固工事,准备把来犯之敌消灭于滩头,敌人见此才没敢轻举妄动。
新安州是座小城,与平壤、介川、阳德都是美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介川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座城内到处都是一个个直径约一丈的弹坑,树木只剩下断裂的树桩。美国恃强凌弱,以这种残暴的手段对付平民,让我们特别愤慨。
我们一行路上的食宿,都受到当地居民的关照。当炊事员把米饭送来时,朝鲜阿妈妮就用大铜碗端来酸菜。这种菜微酸,味道十分鲜美。有位记者对阿妈妮说:“高麻斯米大(谢谢)!”阿妈妮一听,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我们带有朝鲜币,虽然阿妈妮婉拒,但我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价付钱。志愿军入朝时,毛主席曾谆谆告诫:“尊重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不动朝鲜一草一木。”我们记者团当然也要遵守。
我们一路上没碰到敌机的骚扰。快到开城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显得特别激动,有人大声呐喊,有人引吭高歌。
见证停战签字
1951年6月,朝鲜战场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感到再打下去会越来越困难,被迫与中朝方面开始停战谈判。起初,美方建议谈判在元山港内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并来函说:“丹麦政府将很高兴提供这条船。”在美国盟友的船上谈判,哪有我方的便利?于是我方提出将开城作为谈判地点。经过多次文电往来,对方同意将会场设在开城市高丽里广文洞来凤庄。
开城是一座古城,位于三八线以南。我们到达这里时,看到战争痕迹并不明显。街道虽然不宽,但显得古朴,街面上全是平房,两旁有不少专卖高丽参的店铺,有的招牌还是汉字。街上人来人往,一片和平景象。人们的装束和北部一样,妇女穿长裙,老汉戴无翅的乌纱。
我们到开城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报到,将人员、物品交割完毕后,放下重担,全身轻松,美美地睡了一觉。
谈判代表团有一个新闻处,由新华社国际部的沈建图(1955年去参加万隆会议途中飞机被炸遇难)和陈伯坚(抗战时任胶东根据地《大众报》记者,20世纪80年代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负责,沈建图兼任记者团团长。沈建图是归国华侨,自幼在国外读书,英文水平很高。他写新闻稿用英文起草,中文略逊。阎吾说沈建图有次讲话,把“狠狠地打击敌人”说成“狼狼地打击敌人”。
我们记者团到达第二天,谈判代表团“队长”李克农(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设宴欢迎我们。他希望大家把停战谈判报道好,把志愿军的伟大胜利、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宣传好。接着,他说由于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安排学习、参观。随后,给我们举办了短期学习班。首先给我们讲课的是“指导员”乔冠华,他当时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把谈判以来的种种情况、背景材料,向我们作了系统的介绍。他说,自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停战谈判,已历时两年,谈来谈去,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一是交换战俘。
关于第一项,美方总是企图把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捞到。例如:他们提出要我们让出开城地区,退回三八线以北。中朝方面以南日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双方都要退出越界的地区。我方在西线后撤,美方在东线后撤,东西拉直,恢复战前原状。
这时,美方又耍赖,说只谈西线,不谈东线。原来他们在东线越过了三八线。他们多占的不撤,却要我方撤,当然被我方代表拒绝。美方无理搅缠,又说开城距汉城不远,威胁汉城的安全,所以必须把开城交给他们。我方反驳说:“汉城离开城不远,威胁开城的安全,你方是否必须把汉城交给我们?”并向对方明确指出:“你的是你的,我的还是你的,这样的谈判是没有诚意的。”
相持不下,美国谈判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在退出会场时,他狂妄地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于是,战场上又是炮火连天。这就是老秃山、上甘岭战役的背景。
美军精心策划的多次进攻战,毫无进展,且碰得头破血流,伤亡很大,于是又提议开会,硬着头皮回到谈判桌前。战场上碰钉子,谈判桌上说不通,美方又提出一个歪理,说他们有“海空优势”,应该得到补偿。我方代表微微一笑,根本不予理睬。
交换战俘问题也是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南端的人民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撤退,从而遭受重大损失,很多人被俘。美方凭这点大耍花招,提出一对一的遣返原则。这样他们就可以扣下一些战俘留在韩国或送往台湾。针对美方的诡计,我方提出全部遣返原则。
听了乔冠华的介绍后,我们对朝鲜战争当时的状况和停战谈判有了全盘的了解和认识。
我方谈判代表团有位关处长,也向记者团作了补充报告,他还邀请了开城文史馆的专家,向记者们介绍开城的历史。
在培训和参观期间,我还了解到谈判中许多有趣的细节。在谈判桌上,有时双方没有话可说,就对着吸烟。他们的烟吸完,就伸手越过“中线”,拿我方人员的烟抽,结束时随手把我方人员剩下的烟也拿走了,恐怕这也是谈判史上特殊的景观了。有时谈判双方相对无言,我方就提议休会,第二天照旧。有时刚坐下,双方均不发言就宣布散会。
1952年3月下旬至4月初,第二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在限修机场和中立国提名两个问题上陷入僵局。会议开到4月11日,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采取了“到会即提休会”的办法,以阻挠谈判的正常进行。每天,哈里逊夹着文件包懒洋洋地步入帐篷,不等坐稳便急切“建议休会”,并起身退出会场。有时只开两分钟的会议,后来越来越短,最短的只有25秒钟。在国际性会议中,哈里逊创造了25秒钟会议的“世界纪录”。
1952年5月22日,哈里逊接替乔埃成为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他又拉开了“逃会”的序幕。6月7日,谈判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哈里逊提议休会3天,到6月11日复会。南日将军当即建议6月8日继续开会,哈里逊则说:“6月8日你方尽可到会,但我方将不出席。”说完起身离开会场。中朝方面称这种行为为“逃会”。
6月17日哈里逊第二次“逃会”,27日第三次“逃会”。7月13日以后,美方连续单方面宣布休会7天,“逃会”升级。9月28日,美方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设置障碍,并单方面宣布休会10天,“逃会”再次升级。10月8日,美方又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使谈判陷入破裂的边缘。
在参观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现象。谈判的棚子就搭在路边,有两个朝南的大门。西门由我方出入,由朝鲜人民军站岗;东门由对方出入,由美军站岗。美国兵头戴白盔帽,腰佩手枪,背手而立。这些美国兵见记者团有女同志,又耸肩,又挤眉弄眼,流里流气的。
西门里一位人民军军官,见到我们带大批穿便衣的,有的还带着相机,知道是记者团的,就向我们敬礼,和我们握手,连连说:“大家辛苦了。”一口地道的汉语,令我们很奇怪,问他怎么会说这么标准的汉语,他笑着说:“我原来是晋察冀军区的。”

开城城外的原谈判地点来凤庄是一座东方式庭院,花草树木,古典幽雅,庭柱上有汉字楹联。可惜年代久远,记不清它的内容了。接着,我们又去了开城的南门楼。这里年久失修,但一口大钟令人驻足,它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
为配合谈判,六七月间,志愿军在全线发起多次反击,取得很大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害怕志愿军乘胜前进,终于同意停战。得知谈判结束的消息时,全军振奋,我们记者团的人也都兴奋得跳了起来,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7月26日晚,也就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中朝方面的工作人员奇迹般地建起了一座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木结构大厅。
7月27日8点,我们记者团乘车到达板门店。双方正在简易平房里举行谈判,东边草地上停着一架直升机。我们转了一圈便出了大门。
美、英等国记者也同时到达。他们一下车,有的聊天,有的用报纸折成帽子遮阳。队伍中有两个特别记者:一个是英国共产党派来的阿兰·魏宁顿,一个是法国《人道报》的记者贝却迪。在谈判桌上谈到遣俘问题时,美方千方百计想知道被朝鲜人民军俘虏的美军师长威廉·迪安将军是否死了。迪安是美军二十四师师长,在组织队伍突围时被朝鲜人民军俘虏。他是朝鲜战场上唯一被俘的美国将军。
这天,阿兰·魏宁顿奉命向美方记者透露“迪安活着,身体很好”的信息,其中一个美国记者立即向他的报社发出了只有四个字的急电:“迪安活着。”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天天坐直升机来往于汶山与板门店之间。停战协定生效后,我们听说美军在板门店南边隐蔽了一支突击队。一旦哈里逊被扣留,突击队就马上来营救。
上午10点,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板门店大棚内签字。彭德怀司令员来到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并出席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即席讲话,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只要紧紧依靠中朝两国人民,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停战协定在签字12小时后生效。晚9点多,我们在高处向东南遥望。晚10点,板门店上空那两道探照灯光柱(表示谈判区)骤然熄灭。第二天,空中的两个船形的大气球也不见了。泄了气的气球像两块大帆布铺在板门店大棚外的草地上。三年战争真的停止了,和平来临了!
当年记者团的记者有的后来又去板门店参观,回来后告诉我,那座签字大厅连同当年谈判的会场已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场所。在朝鲜停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板门店仍作为停战委员会开会的场所。朝鲜停战后,朝鲜北南双方在这个直径大约为800米的“联合安全区”内,建起了24座建筑物。北侧建筑了“板门阁”“统一阁”,南侧建有“自由之家”“和平之家”,分别作为北、南双方联络机构所在地和对话场所。不少朝鲜北南双方的会谈也都曾在这里举行。“联合安全区”实际上横跨在南北军事分界线上,而军事停战委员会场内的那张谈判桌刚好位于这条线的正中位置。在军事分界线上,还建有7幢天蓝色的简易木板房,这是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厅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场所。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厅内,一条长桌位居正中,开会时双方代表各坐一侧。房子外面,朝鲜与美国、韩国警卫人员隔着一条5厘米高的水泥线——军事分界线相视而立,双方均不得越过一步。南北军事分界线全长241公里,共有1291个黄色的界标。向着韩国方向的界标上面用英文和韩文书写,而向着朝鲜一面的则用朝文和中文书写。根据规定,军事分界线两边各2000米为非军事区,以避免双方发生摩擦。
撰文揭露美军虐俘
停战协定生效后,开城人民一片欢腾。代表团和地方机关设宴相庆,文娱晚会接连不断,总政治部首派越剧团慰问公演,节目有《西厢记》 《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更活跃的还是我们记者团。记者团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到板门店采访交换战俘,一部分随停战委员会下边的观察组活动,另一部分下部队采访英雄事迹。我被安排去板门店采访交换战俘。
板门店冷清了两天,又热闹起来。大卡车来来往往,运送战俘。在现场可以明显看出双方政策的不同。“联合国军”的战俘个个红光满面,笑嘻嘻地回去了;中朝的被俘人员,无不面黄肌瘦。车到板门店,中朝被俘人员有的高唱革命歌曲,有的高呼反美口号。下了车,纷纷控诉美韩战俘营虐待俘虏的种种罪行。有人在气愤之下追打美军司机;还有人带着战俘营发霉的豆渣,向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控诉。
我和新华社的女记者谭家崐采访了许多从釜山战俘营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他们叙述了在1952年5月反对美方非法“甄别”的英勇斗争经过。他们曾因此遭到美军的屠杀,被打死、打伤的达200多人。美方原来把釜山战俘营中的我方被俘人员,宣布为经过“甄别”而“拒绝遣返”。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斗争完全揭露了美方的所谓“甄别”和“拒绝遣返”的骗局。
归来人员说,釜山战俘营中拘留的战俘都是病伤被俘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在巨济岛因为拒绝美方强迫扣留而被打伤的。他们为拒绝美方的“甄别”曾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正义斗争。
4月16日,美方战俘营当局用广播向战俘宣布要进行“甄别”,并派美军宪兵司令部警备科的人前来进行“个别谈话”。中朝被俘人员的回答是:“我们要回祖国,根本不需要‘甄别’!”第三收容所的被俘人员还升起了自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表示坚决要求返回祖国的决心。两小时后,一个美军上尉带了40多个美军人员以架着重机枪的装甲车为掩护,手执木棒冲进来夺旗,打死了一个护旗的人民军战俘,另一个志愿军战俘被打伤后在医院里死去。
第二天早晨,中朝被俘人员怀着沉痛而愤怒的心情举行了追悼大会,在死难人员的灵前宣誓:“誓死拒绝‘甄别’!”在第一、第二等收容所的帐篷上,也升起了中朝被俘人员用自己的鲜血染成的红旗。
从5月11日起,美方战俘营当局竟断绝供给第一、二、三收容所粮食,第三收容所的自来水管也被截断,当然更谈不到伤病人员应该得到的医药治疗。许多重伤员的伤口都腐烂起来,生了蛆;被俘人员都饿得心慌腿软,走路都会跌倒。但是,他们坚决要求遣返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双目失明的重伤员杨昌俊已饿得不能动弹,还用喑哑的声音喊道:“同志们,我如果死了,请把我的名字带回祖国!”
几天以后,美军当局开来几辆吉普车,上面装着大米饭、猪肉、罐头。他们无耻地在铁丝网外面向饥饿中的战俘说:“你们接受了甄别,就给你们吃饭!”战俘们愤怒地拒绝了这种引诱。
在这期间,第一收容所的中朝被俘人员因为四面都被敌人围住,受到的折磨最大。他们吃草,把破皮带、皮鞋用火烤了吃,最后不得不把手伸到铁丝网外拔草根吃。归来人员郝安生回忆说:“皮带虽然那么难吃,又苦,又臭,又涩,但为了回祖国,用牙咬着撕下一块就硬往下咽。”到5月18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饿得不能动弹的时候,美国人冲进来逐个问他们:“现在到哪里去呀?”他们每个人仍坚决地说:“回祖国!”
第二、三收容所的邻近还有别的收容所,那里的中朝被俘人员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出一部分,在夜里避开美军的探照灯光,越过铁丝网送来接济他们。
饥饿和折磨不能征服坚决要求遣返的我方病伤被俘人员,美军当局于是使用了暴力。5月20日清晨5时,美军一个多营在坦克掩护下,突然从釜山战俘营第三收容所的前门和后门冲了进去。一个美军上校坐在吉普车上用喇叭筒指挥屠杀。一瞬间,手榴弹、重机枪、六○炮都响起来了,毒气弹的臭气和浓烟弥漫着整个营场,燃烧弹的火焰四处蔓延。被饿了整整9天的中朝伤病被俘人员被迫抓起自己的拐杖、石块来自卫。
一个多钟头以后,许多我方被俘人员倒在血泊里了,许多原来残疾的战俘身上又增加了创伤,但他们高喊着:“不接受甄别!”“坚决回祖国!”双目失明的杨昌俊也躺在铺上喊:“反对美军大屠杀!”美方的种种暴行,丝毫也没有动摇我方被俘人员要求遣返祖国的坚决意志。
我和谭家崐把采访的这些事实写成了通讯《反“甄别”的斗争——记釜山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斗争》。新华社发通稿后,1953年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在三个多月的采访行程中,我撰写了10多篇稿件,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人民军队》等媒体上发表。
停战稳定了,炎热的夏天过去了,三八线上已有初秋的凉意。记者团工作了三个月,宣告结束,各大报的记者陆续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