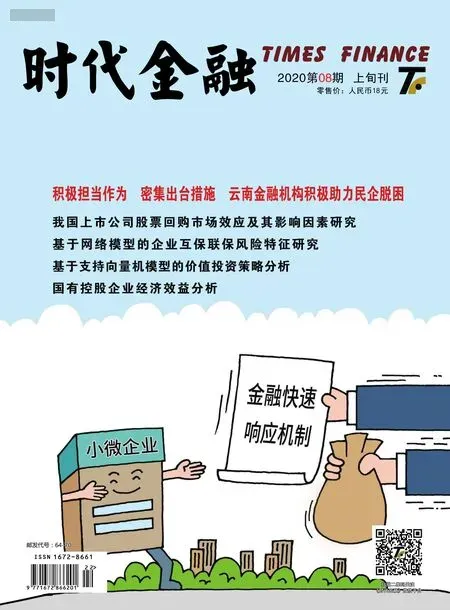数字解析
1万元
对于信用卡透支利息,国内大多数银行一直采用全额罚息。消费者刷卡消费1万元,哪怕还了9999元,就差1元逾期未还,也要按1万元计息。这一备受诟病的霸王条款,如今终于开始松动。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卡专业委员会的要求,从7月1日起,各成员银行要为客户提供信用卡“容差容时”服务。延迟还款不超过3天,未还金额在10元以内,都不再收取利息。
点评:信用卡消费贵在“信用”二字,持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清信用卡,银行给予适当的失信惩罚无可厚非。但“还款差1元按万元罚”的全额罚息,却有悖于基本法理。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消费者只有义务就自己未还款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已还款部分,消费者已经履行了信用义务,不存在违约责任,也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银行没有理由将罚息对象无限扩大到整个消费额度。
近年来,信用卡全额罚息引发的纠纷时见报端,社会舆论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却难以撼动这一不合理条款。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银行过度趋利避害。通过制定全额罚息政策、高额违约金标准,无限加重消费者的违约成本,从而尽可能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透支风险;其二,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我国《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了信用卡透支利息标准,但对于计息的本金是透支的全额还是未偿还的余额语焉不详。银行便运用自身话语权,单方面解释为“全额罚息”。
“容差容时”确实是站在消费者立场上考虑问题,体现了一定的人性化理念。但是这样的政策调整,只是一种小修小补,还未从根本上改变畸形的全额罚息制度。应该说,“容差容时”服务已经到来,取消全额罚息还在路上。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明确罚息的本金概念,从源头遏制银行的趋利避害。同时,引入听证制度,强化消费者议价权,抑制银行定价权,遵循权利对等、风险共担的原则制定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这样才能消除霸王条款的滋生土壤。

5小时
据《新京报》报道,湖南邵阳化工企业污水直排资江,政府下文2年无法关停。然而,此事经公益名人微博转发后,很快得到省环保厅官员响应,不到5小时,排污企业被停产整治。
点评:5小时微博 “秒杀”跑了2年的公文,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递状子没有用、拦轿喊冤显神效。早在2011年,邵阳市环保局就下发过通知,要求对企业实施全面整治,但这些企业仍在生产排污;今年7月2日,从上午11点多到下午3点多,邵阳市双清区化工厂污染问题经过媒体发布、公益人士转发、网友关注、环保厅官员介入、当地环保部门整治、微博回应等过程——5个小时内解决了两年也没能解决的环境问题。结果令人欢欣鼓舞,但过程和手段却令人百感交集。
污染问题要么没人查没人管,查了管了也没人落实,这就是中国基层环保的某种现状。公文跑了两年,抵不过微博上几个小时的来往,这事儿多少不能算是喜事。一者,它是基层环境执法孱弱的代言。你查你的,它排它的,环保局也不是神仙,要食人间烟火,要看人家眼色,地方政府如果睁眼闭眼,企业自然更为嚣张。道理不复杂,在排污链上,有地方GDP在陪绑,谁能当真硬气起来呢?这是中国基层污染久治不愈的最根本逻辑。二者,它是基层公共监督路径不畅的样本。2年的公文就算是以龟速前进,总还有其他民意通道,再不济,还有地方人大这个靠山。但为什么连“外人”都看不下去的事情,在邵阳就是久拖不决?常态的事件处理机制究竟梗阻在何处?
没有程序正义的目的正义终究是面目可疑的。公益人士的关注、湖南省环保厅官员的推动,以及微博上的民意造势,都是带有相当大偶然性的要素。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不力或不应,关停的事实就不会喜感地出现。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改变世界。但如果“微话语权”可以僭越传统事件处理机制而“一枝独秀”,那么,权力与监督机制一定出了问题。没人怀疑微博的传播效率,但如果公平正义必须要以“声势浩大”的姿态才能实现,秩序与规则的天平,还在水平线上吗?
303人
最近,香港大学公布了2013年内地招生情况,今年港大在全国高考人数连续5年下降的情况下,申请人数达到1.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港大最终录取了303人,远超过原定的250-300人规模。在录取的学生中,有16位全国各省市区的高考状元。
点评:有媒体保守估计,状元们出国留学的比例高达60%,这些曾经的高考状元学成归国的仅占少数,人才流失问题严重。
中国有句老话,叫“良禽择木而栖”。近年来,我国各地高考状元纷纷离开大陆、去香港甚至海外求学,就个人选择而言,当然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就社会现象来说,显然值得反思与警惕。此前有人说,“北大清华成了哈佛剑桥的培训班”,这话固然或有偏激,却也窥斑见豹。前不久《人民日报》用了差不多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中国顶尖人才的流失状况,称“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这组数据一石激起千层浪,戳痛了社会对高端人才流失的隐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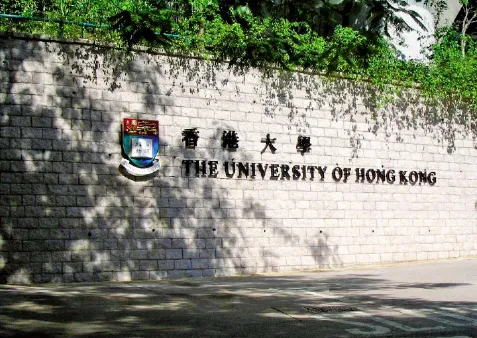
全国高考人数连年下降,港大2013年的内地招生却是“逆繁荣”,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样本。最耐人寻味的是——从2004年至2011年,北京高考文理科共产生了19名状元,其中11名最终选择在香港高校就读。仔细揣摩一下,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此前内地考生对港台、海外教育并不太了解,尤其是2000年政策放开之后,港台高校赴大陆“掐尖”,这也给了高考优等生更多的现实选择;二是港台或海外高校确实是内地高校的“强劲对手”,身强力壮、竞争力强;三是规则公平的力量。抛开社会保障与服务层面的差距不说,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也是不小的问题,高考舞弊、萝卜招聘、火箭提拔等事件,深深伤害了内地优等生“留下来”的信心。此外,不能不提的是,由于劳动力供需比失衡,用人单位对人才“高消费”的骄矜也是一时无解,“海归”镀金后身价飙升,无疑给留学背景打了鸡血。
正视问题,方能疏解症结。事实上,截至2011年底,全国所有省区市都编制出台了包括重视科技人才发展内容的人才发展规划。遗憾的是,人才还是“孔雀海外飞”,要逆转这一现状,恐怕还得做好相关的配套工作,如扎实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改善就业环境等。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人才环境”的改良。这种改良,不是只靠金钱能以改变的,必须辅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譬如很多致力于科研的高端留学人才更青睐国外开放、严谨的学术环境,以及不需要靠“跑项目”、山寨抄袭等手段来获得竞争机会。
1.3亿元
据媒体报道,北京邻近故宫的一套报价1.3亿元、面积400平方米的“学位房”引起了社会的热议。报道称,只要购买这套位于景山东街的四合院可以上“北京最牛的小学”。目前,这套四合院已经被移至线下管理。
点评:一套学位房,1.3亿元,这是什么概念?按照6月初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62677元,以此计算,要想买这套房需要一个双职工家庭奋斗1000年,而且还没算中介费、交易税。结论虽然有点荒唐,但这的确是现实。
如果留心观察,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在大多数城市,学位房都是房地产市场里的“白富美”,引来无数追求者。这套房子,折合单价约每平方米32.5万元,价格的确很高,但是放眼望去,附近的房子价格也不低,大多每平方米10多万元。以前很多人自嘲一年收入只能买个洗手间,现在看来,买个洗手间都是奢望。在广州,每年四月份都会出现一波学位房抢夺潮,一些学位房价格甚至三年涨了八成左右。即使在市场相对低迷时,学位房价格依然坚挺,甚至上扬。
从学位房的“逆市”中,可以看到“买房就是买资源”的“潜规则”,资源性购房需求,已经成为推动楼市的一双看不见的巨手。既然买房已经不是一个纯居住概念,相关的楼市调控政策也应该有所“调适”,从“就房论房”中走出来,多辅以一些调资源的措施。全国而言,一线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即使不能跨区域分配,亦应该向周围城市“摊薄”。具体到一个城市,可以把中心城区资源逐步向新兴区调拨。这样,方可能实现引导购买力从中心城市、中心城区撤离,为房价“削峰”的同时让大城市的规划布局更加合理。近几年,楼市调控对畸高房价屡攻不克,也与缺少对资源性因素的考量有关,不妨将“1.3亿元学位房”作为一个案例,剖析求策。

5400万元
日前,马伯庸发表博文让河北冀宝斋博物馆年代穿越、造型奇异的藏品引发关注,“青花人物纹罐”上写“炎帝制造”。据媒体报道,这个号称投资5400万元的村办博物馆不但是国家3A级景区,还是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级科普基地。
点评:这是一家很考验历史功夫的神品博物馆:这里不仅有“隋青花”、“魏青花”,还有款识“炎帝制造”的“青花人物纹罐”;此外是1.92米的汉代五彩瓷器,还有直径1.76米的“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大的古代瓷盘”……有人感叹“三观尽毁”,有人调侃“当笑话也看不下去”。如果说山寨货起码还能标注下“A版”还是“B版”,那么,这家博物馆却以历史文化正统的姿态,拿匪夷所思的“藏品”传承着瓷器文化。
农民办的博物馆,就像农民造的飞机、潜艇什么的,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往大处说也是“圆梦”,有限度地鼓励一下足矣。如果非要正儿八经地论证中国农民造出了“大秦歼星弩”、“大唐斩舰刀”……就显得有点不地道了。据介绍,这些宝贝是在二铺村当了50多年村支书的王宗泉所收藏的,此前曾多次陷入争议,有业内人士评价冀宝斋“就是个低仿假货集中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据馆主说,货都是各地送来的,也没花多少真金白银。这话让人瞠目,稀世罕有的历史遗存,就这么随便送送就凑成了传世博物馆,这让那些动辄上亿的藏品情何以堪?奇葩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谁在背后刻意制造这样的奇葩,谁又在制造奇葩的过程中渔翁得利?几个问题接踵而至:一者,这样的博物馆,轻飘飘地成了“国家3A级景区”,这不免让人怀疑,A级景区评定究竟有多“水”?二者,此地已成为“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级科普基地”,如果这样的基地将一直办下去,谁来承担对历史文化信口开河的责任?三者,这个博物馆所获得的“殊荣”,究竟多少次出现在地方的政绩报告里,又为哪些人的脸上争光添彩?
“穿越博物馆”的肥皂泡能吹得如此之大,不是一两个人为之编制“皇帝的新衣”,有人乐得织布赚钱、有人甘于添砖加瓦,这种相安无事的“平衡术”,究竟支撑了多少各取所需的潜规则?
500万人
根据目前国家发改委编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特大城市的标准“城市人口100万以上到200万”,有望被提升到“城市人口在500万以上”,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标准也会进行上调。
点评:如果按照旧的城市人口标准,不少地级城市已经变成特大城市;但如果上调了特大城市的人口标准,某些省可能没有一个特大城市。那么,很多地级城市提出的口号如 “进入特大城市行列”、“发展特大城市”等,就变得毫无意义。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各种城市标准都有可能上调,而且调整标准只有一个:人口总量。小城市标准从20万人以下调整到20万~50万人,中等城市标准从20万~50万人变为50万~100万人,大城市标准从50万~100万人提高到100万~500万人,超级大城市人口标准有望设定为1000万以上。
如果城市标准“升级”,显然有多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减少某些城市浮躁症,让那些一味追求“特大城市”称号的城市负责人回归理性;二是有利于引导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以控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三是让城市标准更适应发展需要,因为随着城镇化发展,某些城市标准已经明显过时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旧的城市规划法,还是最新的城市标准认定,都是通过“人口总量”来认定城市大小。以人口数量来认定城市大小有一定合理性,这是因为,人是城市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多城市规模相应就大,人口少城市规模自然就小。但认定城市大小不能只看人口总量,而要看综合指标,人口数量只是综合指标之一。如果只是以人口总量作为城市标准,标准似乎过于简单。最近,很多地方在描绘新型城镇化宏伟蓝图,诚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即使城市人口再多,恐怕也不能产生正能量,因为有产业支撑才能拉动就业、消费增长。所以,上调城市标准除了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产业规模,特别是上调城市标准要看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编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首先要编制城市公共服务规划,包括公共交通、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如果城市公共服务不能与人口总量相适应,就会带来很多“城市病”。上调城市人口标准的同时,城市相关制度更要升级。只有制度为城市保驾护航,城市的公共服务才能更公平更合理。
10分钟
据媒体报道,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自7月1日施行以来,淘宝上开始陆续有店家推出了“代看望老人” 系列服务,购买宝贝的形式是时间费用+物品成本+交通费用。一家店主贴出明确的收费标准:“10分钟=8元”。
点评:淘宝店做生意,寻求的是有偿服务,尤其是针对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后,一些家庭子女没时间常回家看望父母,便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这款亲情服务产品,属正当行为,无可厚非。对有些子女来说,由于工作繁忙,要真的做到常回家、常看看,也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购买淘宝“代看望老人”服务,也不失为一种补偿措施。
但于孝心来说,犹如某些地方亲人去世,花钱雇人代哭一样,把情感活动简单地异化为金钱交易的商业行为,这种“代看望老人”服务,对子女来说,安慰的是自我,却不是爸妈。毕竟老年人最大的愿望是子女“常回家看看”,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交流,得到儿女们的体贴与关怀,而不是找人看看、送点吃喝就能解决的。
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要“常回家看看”,是对做子女的履行法律责任的一种道义底线提示,提醒子女们再忙也不能忘了父母,忘了“常回家看看”,并非要给子女治罪,求的是一片真心真情。毕竟,儿女与父母之间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法律规定的抚养关系基础上的亲情关系,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代看望老人”服务虽然也是受儿女之托,其中也含有孝心成份,但老人收到的只是花钱雇来的程式化问候,未免虚情假意,听着好听,心里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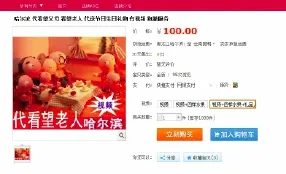
金钱可以买来服务,却淘不来亲情。对于淘宝店家推出的此项服务,大多数子女都不太认可,恰恰表明这项“代看望老人”服务缺乏亲情化,把“常回家看看”简单地演变成商业服务,也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蒙羞。对子女来说,看望父母可能存在“没时间”的问题,但“没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能总是“没时间”。只要孝心在,总会抽出一点时间挤出一点时间看望父母的。所以,不要苛刻地理解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要把看望父母的孝心传承下去,毕竟做子女的也有老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