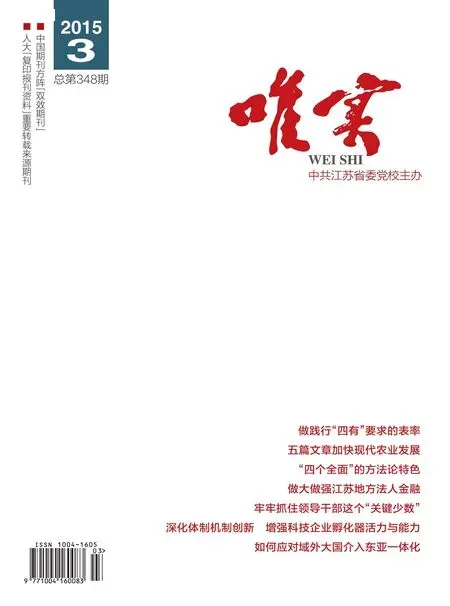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心态焦虑问题谈
卢 岚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教授,法学博士)
一
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打破了民众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低工资、广就业的福利计划。大批社会成员开始为家庭基本生活、为自己的前程、财富积累等现实问题表现出了极度焦虑不安、浮躁紧张的情绪。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压力下,国民的担忧、紧张、浮躁心理最终积成的社会焦虑现象,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和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现阶段的焦虑表现程度和波及范围是空前绝后的。说它空前,是因为从地域之广、人群之多而言。它涵盖了中国穷人为生计焦虑,想一夜致富;富人为安全焦虑,财产的来历心知肚明;官员怕东窗事发而向国外转移资金和家庭成员;年轻人为前途焦虑,老年人为医保、社保焦虑……本来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却给国人带来了生死攸关的抗争焦虑。据《中国青年报》一项社会调查(2134人参加)表明,焦虑已成为国民常态。34%的受访者认为经常焦虑,62.9%的人偶尔焦虑,仅0.8%的人从不焦虑。中华英才网对全国15个行业的1500名企事业职员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90%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社会焦虑是国民对个体命运的焦虑,怎样生活的焦虑,为何活着的焦虑。国民焦虑的这种普遍性势必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致使中国社会出现“裸官”、“裸商”和盲目出国寻安全的怪象,削弱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因此,构建良好的国民心态,是消除国民焦虑、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实现改革最终目标的重大保证。
二
经济转轨所引发的急剧社会变迁,是一个经济迅速“脱嵌”的过程,即经济发展摆脱一切社会规范,根据自身的要求重塑社会的过程。中国目前正进入全民焦虑时代,它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焦虑,而是社会焦虑;已不再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阵痛。而缓解焦虑首当其冲的是,了解社会焦虑的现状与生成的逻辑及其医治措施。
1.社会焦虑现状成因分析
第一,从经济维度上来说,分配危机使民众产生生存焦虑。一切为经济让道的发展模式已经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全面失衡。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财富的具体性、易衡量性导致人们极易直接攀比,攀比愈烈,中下层群体的失落感越强。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报道,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早在2009年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7(欧洲在0.24-0.36),远超国际警戒线0.4。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这意味着社会日益分裂为既得利益集团与草根民众。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具有垄断地位以及大企业等强势集团。由于收入分配的天平倾向既得利益集团,一部分人就被制度性地安排在社会底层。既得利益集团得益于改革开放,成了一定的规模、气候。在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的情况下,“只要是权力想做的,就是可以做到的。”换言之,权贵精英享尽一切人间的荣耀之后,毫不负责地将贫困丢给了底层民众。把构建“和谐”社会理解为“河蟹”社会,明目张胆地横行于中国交通、食品、医疗、司法等各个领域。攸关民生的毒奶粉、毒馒头、假药、资源垄断、贪污腐败、撒谎成习、操纵司法等乱象,挫伤了国人积极性、创造性,助长人们投机钻营。这种消极思想暗流趁机侵蚀社会机体,致使整个社会信任坍塌,使社会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的焦虑产生。诸如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有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不信任;职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等等。曾经受人尊敬的教师、医生、专家也频频跌破道德底线。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正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的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么杀熟又成为普通人群之间的信任危机难以破解的最好脚注。中国现在似乎不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是流行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第二,从文化维度上来说,文化危机、价值危机是导致国民滋生为何活着的焦虑。首先,社会快速变迁使价值规范无法成型。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成为价值冲突与失范的根源。文化的多元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生活“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孙立平语)。价值的多元化会导致人们政治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诸多困难,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焦虑与迷茫。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类对于道德、良知、灵魂的思考,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挤压、缩水。其次,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复杂性取决于价值主体的利益和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边形、差异性显著增加”(陈克敏语)。其实,“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当社会由于标准多样而失去标准时,社会的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兰久富语)。马克思曾感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缺少有智慧的人,但更缺少有信仰的人。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变革滞后,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价值观的正确、合理和科学固然重要,但传播的技巧也很重要。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的军文化语言和工程类术语的超长,运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和平年代,哪有那么多阵地、堡垒、主战场、攻坚战、夺取最后胜利?到处是工程,到处是硬梆梆的语言,哪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童世骏语)。

第三,从政治维度上来讲,政治危机导致国民怎样活着的危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亨廷顿,劳伦斯语)。换言之,“文化的沉沦也就意味着人的沉沦,而人的沉沦则直接意味着社会的沉沦”(郝宇青语)。就此而言,政治危机决定着国民生活的走向。当下政治危机包含政治态度危机与政治参与性危机。政治态度危机体现在公民对政府的公信力、公务员的信任度的下降。特别是权力的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极大地刺激了老百姓的现实感受,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其实,民众最为不满和怨愤的就是寻租、腐败、分配不公、侵害民众权利。政治参与危机在于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改革的旁观者,民众缺乏参与改革的渠道。在缺乏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下,自然难以保证权力公开透明,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日常监督机制,加之民众自身也缺乏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导致滥用权力时有发生。“要使公民重新担当其政治责任,关键又在于重新催化个体的公民意识,是指对自身在政治自身秩序的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连在一起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清楚地了解”(德里克语)。这样,才有利于民众从理性中感悟感性,从真理中捍卫常识,而不是去“打酱油”。总之,社会越政治化,公民对政治的关注越强。而民众对政治关注越强,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方针制定、改革成果的分配等的积极性与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实现主权在民的改革也就越易推进。
2.社会焦虑生成的逻辑
第一,人性的内涵与现实错综复杂的张力是社会焦虑生成的内在本质。本真状态人性,无论是本体构成还是现实表现都具有两面性:美善与丑恶、完美与残缺,廉洁与腐败并存。换言之,人既不是单一的天使,也不是纯粹的野兽,而是心中有天使的野兽之混合体。所谓野兽,是指基于客观存在状态而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天使则是指向意义建构状态升华,是通过主流价值牵引人向上的一种精神提升。本真状态的人性,既要摆脱本真状态的丑恶,同时还要对他的必要性给予尊重和依赖。换言之,既憧憬理想,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现实的状态,满足其物质需要,这就产生了逻辑有限性与价值理想局限性的张力。当人性中对物质的贪欲本能与现实的错综复杂之间的张力失衡并超度时,焦虑心态便产生了。
第二,理性的缺位与启蒙的稀薄是社会焦虑产生的逻辑深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启蒙教化的稀薄,导致民众缺乏理性。“在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全部历程时,除去社会转型、社会运动本身的制约外,就这一运动自身而言,不能不承认它有着过于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于急于求成。中国启蒙思想家不太注重思维方式自身的运用和革命,而是注重用国外理性思维的具体成果对民众直接灌输。“总想从国外现代文明中拿过几样现成的具体成果,在中国立即开花结果,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而过分地忽略了看来形态不那么具体、效果不那么显著的思维方式自身的变革”(姜义华语)。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导致缺乏理性,急于求成的短、平、快的行为方式。例如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批量生产”孝子;国家发改委某专家的所谓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了62%;宁波宣布将斥资5000万培养1400名“乔布斯”。这种政绩化的道德生产计划数字,折射出人们失去理性价值判断与实践行为,极易产生高期望值和人们的短期行为。一旦欲望落空,就会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会产生对社会不满心理,加重或放大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借机发泄迁怒于他人,马克斯·韦伯说,在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和动力的情况下,即使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条件也不能被有效地使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所以,中国启蒙任务没有完成,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启蒙工作。
另一方面,理性的空场导致民众思维方式的困境。由于启蒙的稀薄,理性的空场,在理性与价值失衡的现代社会中,一切非理性的情感、价值都是不可信的,自然导致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们沉浸在对于“现实即是合理”的幸福意识迷蒙中,忘记了批判精神,丧失了否定的勇气。历史一再证明,理性一旦缺位,认知、信仰一旦教条化,思想的鸟笼足以让愚昧荒唐的脚本上演。在从理性中感悟感性,从真理中捍卫常识。泾渭分明的崇高与粗鄙、高雅与庸俗、伟大与卑劣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价值没有标准”。相反,对严肃倒要质疑,在无厘头的搞笑和人性本能的匪气张扬中嘲笑理想、躲避崇高。马克思哲学在理性问题上的重要变革,就在于通过理性的考察还原出:理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依赖于社会生活;理性本身矛盾的加剧,理性与非理性的严重冲突,乃是特定条件下生活本身分裂的结果。社会分裂了,哪里还会有从容与淡定,民众不焦虑才怪。
三
大发展、大转型、大变革的当下,现代化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推向格式化和碎片化。而现代性的生存状态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的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的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进人的独立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孤立”(侯惠勤语)。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精神,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何使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有精神追求,弥合伦理道德理论与实践生态链的断裂,消弭精英与草根之间的裂痕,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应承担的责任。
1.公平与正义的落实:消解社会焦虑心态的内在根源
在价值多元化所引起的混乱与冲突中,最终源头仍是利益冲突。因此,对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整合,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之上。从制度设计和权力优化入手,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打破公共权力垄断,落实公平正义,倾听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在权力配置改革上,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对改革方针、改革过程、改革成果的分配及有效的政治参与。因为公权力的改革是通过人民民主实现主权在民的改革,所以,政府的每一个政令,精英的每一项决策,才会首先考虑的是对人民让利而不是自己得利。
第一,注重顶层设计、打破阶层之间的铁幕,促进公平正义落到实处。一是改革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智慧。因此,解放思想也包含解放思想者,给每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人以相同的权利,也是非常必要的。亨廷顿在比较改革者比革命者道路更艰难时说,改革者必然是两面作者,既要反对保守者,又要反对革命者;二是改革者不仅要比革命者更纯熟地驾驭社会势力,而且还必须更精确控制社会变化;三是选择改革的形势,决定优先顺序的问题,对于改革者比对于革命者更加艰巨。由此,他得出结论:“改革者必须具有革命这更高超的政治才能。改革成功之所以少有,恰恰是因为实行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天才极为难得。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都是一流的政治家,而成功的改革者却绝无例外。”
第二,加强对精英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官员逻辑的滥用反映出官员责任的滑坡、智慧的贫庸。当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即暴露了社会管理上的价值苍白,也体现了社会管理部门的慵懒和应付了事的不作为态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个体层面对民众(特别是精英群体)进行价值引导与自我建构,消除心理问题与不良情绪。促使精英群体形成改革大局理念,舍弃自身既得利益。凯恩斯曾说,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大卫·休谟也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所有事物,是有观念支配的理念战胜利益。通过对精英群体的教育,提高其整体道德水平,让他们学会反馈社会,反哺社会,树立以民为重的道德风尚,以弥合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鸿沟。否则,底层的沦陷将会加速整个社会的沦陷。
第三,确立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把群众作为改革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否则就会消解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淡化民本意识,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在实践中就难以落实,难以确立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地位,改革也就失去了基本动力。因此,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毛泽东语)。中国的质量和分量都在每一个民众身上。
2.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的统一:化解公民焦虑的现实路径
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巩固,不是话语霸权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在多元整合发展的过程。化解社会焦虑心态的现实路径在于引导公民自我生成、自我营造生活的价值、自我建构意义世界,而不是等待任何权威。
一方面,人是社会主体,制度是社会框架,而人的精神思想则是社会的灵魂核心所在。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和谐稳定亟需要法律,更需要人的精神思想境界的形塑。
另一方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民众自身素质。即便是功利主义也需要一个人品德的支撑。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理论变革,用专属于中国人的文化符号和独特的理论创制中华民族的痕迹与道德底色。
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搭建平台,用集体意识、集体良心宣传教化来建构社会信任。消解社会焦虑,培育积极国民心态。毕竟“那些从自己身上不断涌现出来的活性感受,是一个可以用我们的鲜血做图章来担保的真理。建设我们的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崔卫平语)。这是化解社会焦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