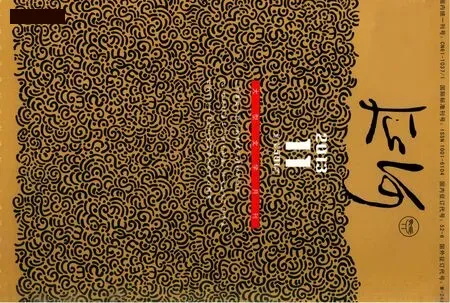走了几个地方
刘紫剑

丹 凤
一个人的名字好听了,虽然没有见,也有亲近的想法。地名亦然如此。丹凤就是个很好的地名,有一种女性健康、明朗的美,有传统的喜庆和华贵。
秦岭最美是商洛。丹凤在商洛腹地,应该也是个美的地方。虽然我去了,只是匆匆半天时间,走马观花,又是阴天,时不时飘点小雨,所看到的自然就打了折扣。
丹凤有山有水,一条丹江流经县城南侧,一座凤冠山坐定县城北面。“丹凤”其名,由是而来。
凤冠山是全城的最高处。关于这座山,贾平凹老师有一段文字:“没脉势蔓延,无山基相续,平坦地崛而矗起,长十里,宽半里,一道山峰,不分主次,锯齿般地裂开,远远望之宛若凤冠。”——这是他的家乡,笔下不免夸张。
秦岭是花岗岩山体,石多破碎,北坡险峻奇崛,南坡舒缓延绵。凤冠山作为秦岭南麓的一个小山峰,却有着北侧的山势,在四周连绵的和谐中,突兀一道嶙峋的山体,“南峰北相”,显得特别。山不高,相对落差300米左右,在山脚下可以看到山的最高处,修了一个小亭子。如“焰”之于明火,“味”之于美人,因为这个亭子,山就多了几分文化气息和人文风韵。
凤冠山的独特,还在于山体上挖有十二个洞窟。具体哪个朝代、何人开凿?我现场问了导游,回来查了资料,都语焉不详。十二个洞窟不规则地散布,南向居多,分供十二尊神。洞壁的周围,因神而异,还有形形色色的浮雕。这些雕塑看上去,就是现代的作品,比例协调,构图喜庆,画面热闹。
十二个神仙刚好一打,佛、道、儒都有,不在一个系统,级别不好定。如果放一起开会,按现在的官场礼仪,能把排座次的人急死。然而,香火是不同的,玉皇大帝、如来佛、财神爷这三位“神气”最旺。玉皇大帝是天庭的一把手,人们都知道现在办事,找副职有难度,于是直接烧香烧到位。如来佛呢,佛教讲究“因果报应”,现在的人们,好事情想得太多,亏心事做得太多,不论欲壑难填还是良心难安,反正逮住机会就在佛爷前表忠心。财神爷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国大地上,目前最火的就是这位“爷”。四大文明古国,据我所知,只有咱们在传统文化中把金钱供为神,所以,也应该算是“中国特色”吧。
我是先爬了山的,下山的时候开始飘雨。等到了山下,雨大了,起了雾。那雾平地而起,像开锅的蒸笼,翻滚着向上弥漫,不一会的功夫,就把凤冠山罩得严严实实,白茫茫一片了。我在看凤冠山的介绍时,对一句话不解:“遇雨则烟岚雾化”。看到这雾,豁然开朗。
在山上看城,有铁路、国道和高速公路,在丹凤横竖穿过,将县城划分成不规则的几大片。这些水泥和钢铁的巨龙,都是从秦岭山中钻过来的。人一旦做过手术,就泄了元气,即便好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山和人一样,这样横七竖八地穿堂而过,山的精气神也就散了。
在山上看水,一条浑浊泛白的带子,却是不敢小觑。丹江是汉江最长的支流,汉江又是长江最长的支流,若论起身份,丹江可算是长江“嫡出”的长子长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作用重要,历史上的丹江,是一条水上交通要道,始航在春秋战国之前,为朝廷“贡道”,是历代国都长安的物资补给线。明清时期,丹水暴涨,沙压滩平,船只往来无碍,航运最为鼎盛。
大水道必有大码头。因为这条水路的重要,在这冠山丹水之间,就有了一座享誉南北的水陆码头——龙驹寨。江、浙、湖、广等地的丝、盐、茶、米等物资,沿长江进入汉江后,逆丹江而上,靠船帮拉纤运送至此,拢船上岸转为陆运,改由驴驮骡载,人挑肩负,行销到陕、甘、晋省各地。西北的物资,反其道而行。龙驹寨就成了西北与东南商贸物资的集散地、水陆运输的交接点。
“龙驹寨”也是一个充满民间文化色彩、极富想象力的好名字,传说项羽的乌骓马就出自这里,又说在此产驹,寨子因之得名。还有说法是刘邦的坐骑,李自成的坐骑都与其有关。依我想来,李自成说比较靠谱,他是确曾将商洛山作为游击根据地,养精蓄锐,八进八出过的。刘项两位,花花世界还折腾不够,会到这山沟里来吗?
民国年间,陇海铁路建成后,商家弃水就陆运输货物,龙驹寨逐渐丧失了货运集散中心的地位。尽管如此,仍是方圆数十里地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的中心。现在是丹凤县治所在地。
龙驹寨昔日繁华鼎盛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百艇联樯,千蹄接踵”,为了给各行各业的弟兄们提供一个食宿、娱乐、聚会的地方,由各帮会自行筹资,修建了12座会馆。当时修建最好的就是船帮会馆,船工们从船上每件货物的运费中抽取三枚铜钱,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建成。
值得庆幸的是,历经近二百年的世事变迁,船帮会馆保存依然较好。一座青砖六柱五楼牌坊式建筑,是它的门楼,颇有江南水乡的情调,又不类于江南的小巧玲珑,居北向南,凭江而立。穿过门洞,转得身来,一个戏楼赫然呈现,重檐翘角,华丽明媚,高大雄伟,气势壮观。
船帮会馆是通俗的叫法,历史上的名称是“明王宫”和“平浪宫”,因会馆内除了戏楼,还有一座大殿,供奉了汉水水神,用以祈求神灵保佑风平浪静、船行安全。百姓又称之为“花庙”和“花戏楼”,一个“花”字,概括了这座兼具“南秀北雄”之誉古戏楼的风貌和特色。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砖作青色,木皆涂红,顶部镶嵌了五彩的琉璃和瓷片,显得古典而又喜庆。最令人赞叹的是,几乎每块木头上都布满了精细的镂空雕刻,技艺精巧细腻,内容庞杂丰富:大禹耕田、文王访贤、囊萤映雪、赤壁怀古等等,几十个画面,几百个人物,生动传神,活灵活现。
快两百年了,戏楼依然坚固耐用,听导游说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是龙驹寨传统的庙会,还有戏班在这上面演戏。这一点,真令我们现在的建筑专家和工程队惭愧。但大约不会惭愧吧,惭愧总还需有个良心在,而对不少的国人来讲,良心是最缺的东西。
陕南山水秀丽,民间说法阴气较重,女子多秀美,男子多阴柔。但我在丹凤没有见到几个耐看的女子。只是吃饭的时候,喝到了丹凤自酿的葡萄酒——这一点很让人吃惊——竟然在中国西北的大山深处,出产有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葡萄酒。一问之下,果然是西方传教士的产物,追溯起来,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听说在丹凤老街的两头,还矗立有两座舶来的教堂,也已向龙驹寨的山民们传播了一百多年的“福音”。

我是个味觉比较迟钝的人,于烟酒茶这些享受类的东西缺乏一般的辨别能力,也就是说,二锅头和茅台,金丝猴和软中华,除了香型不一样,我感觉都差不多,所以也就喝不出丹凤葡萄酒的妙处。只是看着硕大黧黑的橡木酒桶上百年前的标记,端起一杯刚从生产线上淌出的美酒,让那种温润饱满的暗红色液体在掌中盘旋,忽然想起那些价格昂贵、来历不明的“拉菲”们,我的心情放松而愉悦,没有理由不赞美丹凤的葡萄酒,没有理由不放怀畅饮,喝了总有一斤多吧,都有了醉意。酒至微醺处,花赏半开时,挺好。
离丹凤城不到十余里就是棣花镇,那是贾平凹的故里。在丹凤乃至商洛,这是一位正在被神话的人物,凤冠山的文昌洞里,塑有文昌帝君,手中捏着一支笔,笔锋所向,门口的介绍牌上说是指向贾平凹的故居。我顺着笔锋方向望,一色的苍茫秦岭。
二百年的船帮会馆,一百年的丹凤葡萄酒,六十年的贾平凹,一个养眼,一个养胃,一个养心,都是丹凤制造,可算得“丹凤三宝”了。
贾平凹去山东签名售书,唯独到了曲阜,只行祭拜而不问签售,因心有敬畏在。我亦心存敬畏,却不知高低地做这篇文字,简直就是孔夫子门前卖文章了。
镇安行
镇安离西安,走高速一百公里,说是一小时路程,但我们下午六点半出发,到达时,都已过晚上九点。
这天是处暑,暑气在西安城里依然横行霸道,没有一点躲藏的意思,更别说终止了——好像也就这两年的功夫,西安的夏天越来越像南方,不再是干爽的热,而是闷热,是湿热,是一团厚重的蒸汽裹着你,使人呼吸不畅,全身发痒。

镇安说是在秦岭的南坡,依我看,更像是在秦岭的腹地——在县城的高处四面望,群山连绵万里长。高速是穿越秦岭的,一条长蛇,无头无尾,在大山的肚子上钻来钻去。秦岭当然不高兴,下了高速,就让我们转弯子,后来去当地的木王,去塔云山,弯子就更厉害了,转得人晕,有的都吐出来。
夜色中的县城,红尘喧嚣,生机勃勃。路道一律狭窄,两边的商铺一家一家紧挨着,卖的货物却没有什么新奇,如同到了西安的小巷子,市声亲切而散淡。有躺椅放在路边,女人四仰八叉地躺着,忽然坐起来,拿眼警惕地盯我们的车,担心撞了她的货物。小狗,后面一个孩子忽然冲过马路,隔着车窗都能感受到追逐的快乐,只是可怜了司机,端着方向盘心有余悸地喘气。好不容易到了宽敞处,吓了一跳,人山人海啊,以为在集会。仔细看时,却是满满一广场的女人在跳舞,伴着欢快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一遍一遍重复着;每个人的空间很小,手脚都施展不开的样子,依然脸红脖子粗,个个汗湿了额头。后来发现不只是县城,即便路边的小村子,凡有空地,就有妇女在蹦跶。车上的人们都感叹:好呀,全民健体强身,果然和谐社会。
车子东扭西拐,在夜色中挤出县城,爬到一个山坡上,找到落脚点。后来我看贾平凹写镇安的文章,说是北山的膝盖上有个公园,也有个酒店,他在酒店里住过三天。第二天起早转了一圈,知道我也住在了这个酒店。
所谓“北山”,是贾平凹定义的,因为山在县城的北边。隔着一条县河,也有一座山,两山扭出个S形,县城就在这个弯子里蹲伏着。国家现在搞城镇化,城镇化如一场大雨,把人们从大山的皱褶里、从乡下的僻壤里,一个个冲出来,汇聚到城市,万川汇海,城市就在一天天长大。两边的山也就夹不住镇安,山下的楼房都快要长到酒店的高度了。
城市却是乏善可陈,火柴盒一样的楼房,外墙多贴了白的花的瓷片。能见度也不是很好,天的蓝、山的绿都在朦胧着,空气中淡淡的一层,不是雾也不是烟。我想着下场雨吧,雨后的镇安揭去面纱,也许会有别样的惊艳。
而镇安应该有它传统的老建筑,我印象中在什么地方见过:高的屋脊,大的进深,长的出檐,进门就是中堂,前有场院,后养禽畜。墙是粉白,瓦是黛黑,明亮、干净、简单,兼有苏杭的灵秀与皖南的柔美。什么地方?电视上,书本里,多年以前的游历中……
一个地域的文化,应该更多保留在建筑和饮食中。现在建筑已经被同化,只剩下吃了。吃得是农家乐,我捷足先登,和女性们坐在一起——我是越来越爱和女人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又能少喝酒又能多吃肉,光腊肉就吃了四片,油汪汪的,晶莹透亮,一片有半个巴掌大——爬山又累又饿的时候,我给当时在另一个桌上忙着喝酒的人们比划,和他们大方分享自己舌尖上的美味,听得一个个咬牙切齿。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地打嗝,打出浓郁的腊肉香。
酒是农家自酿的甘蔗酒,色泽淡黄,后味微甜。听说当地人一次可以喝个两三斤的,让人咋舌不已。我在酒上吃过不少亏,现在意兴阑珊,消沉了不少,但每每看到酒桌上勇猛的青年,都会在心里感叹,真有本人当年2B的风采啊。
同行中有个八零后的小姑娘,一路闲聊。说她奶奶家在秦岭南坡的柞水,她爷爷家在秦岭北麓的蓝田,小时候她两地常去,每次到了奶奶家,远在十里八乡的亲戚都会齐聚在一起招待,不管到那家,桌上排满了酒肉。到了蓝田,坡上的大爷家是苞谷稀饭和咸菜,饥肠辘辘到了坡下的二爷家,咸菜和苞谷稀饭。其实奶奶那边的亲戚都很穷,连房子都盖不起;而爷爷这边呢,有钱就盖房子,有钱就盖房子。这样说着,想一想,蓝田属秦,镇安归楚。秦人务实理智、内敛自俭,几近于抠门。楚人浪漫奔放、追奇逐新,但过于嗜尚衣食,大兴土木的楚灵王就是一个例子;另有吴越争霸,相传一个美女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一座大山,就这样形成了两处性格。
镇安在唐时称安业县。贾岛有一首诗《题安业县》: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僧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说的就是这里。前两句说山多且密,后两句说山险而美。通俗易懂,直白如话,我小时候背过,想象不出是怎样的一个地形地貌,现在四面看了,感叹也真是啊,贾老先生不愧是“推敲”的祖师爷呢。
现在各地都在发展旅游产业,镇安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木王森林公园和塔云山了。前者是自然景观,水路明媚,山路雄伟,确实无愧“秦岭最美是商洛”的宣传。后者是历史人文景观,为明朝万历年间建造的一处道观:小小的一间房子,架在高耸的山尖上,俯瞰万丈深渊,平视云雾缭绕,仰观天近云淡,颇为险峻和神奇。但包装有点过,新盖了好多零碎的建筑,牵强附会了一堆的历史名人和神话人物,不成体系,让人想起被浓妆艳抹过的法门寺和楼观台。导游也是临时凑合的,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伙子,满嘴跑火车,找不到逻辑关系,弄的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
回来的路上,当地的朋友推荐这里的苞谷,说都是笨苞谷,就是没有改良过的非转基因食品,纯粹的粗粮,原始的味道。朋友咬一口,感叹着筋道呀,这才是苞谷呢!现在城里的苞谷,还能叫苞谷吗!
我拿了一个啃,与平日所吃果然不同,不是香,而是硬,啃到腮帮子都木了,还咽不下去。就想:我所看到的镇安,交通如此便利,风俗如此雷同,还是以前的镇安嘛?又想:现在的人们,整天吃着改良过的食品和各种化学制品,呼吸着内容驳杂的空气,生活在各种辐射里,还是以前的人吗?这样琢磨着,就吃了一惊,不敢再想下去了。
樱花掩映下的青龙寺
清明前后的西安,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在坊间的口口相传中,青龙寺已成了观赏樱花的不二之选,于是携妻女到青龙寺看樱花。
沿着兴庆路一直走下去,过了南二环,行不到两站路,会发现西安城边少有的起伏,地势是愈来愈高。到最高处,在市井喧嚣的茶楼酒肆后面,隐隐透出一点古色斑斓的飞檐挑角,就是青龙寺了。
随着缓缓涌动的人潮挤进青龙寺,人头多过花色。不知是人在看花,还是樱花在笑看这些指指点点的红男绿女。
虽然,樱花是意料不到的惊艳。我是一个愚钝的人,很少能领略到花草的美。第一次吧,被青龙寺的樱花折服。
进得山门,你的眼睛就被樱花牢牢地抓住。在假山后,在殿宇旁,在修竹边,在流水处,那满树怒放的樱花,将小院渲染成五彩斑斓的花海。你几乎看不到树身,一棵树就是一个大的花团。走进了细看,大花团又由无数的小花朵缀成,一朵朵开得张扬恣肆、无所顾忌;娇嫩的叶子挤挤挨挨,一层一层地叠着,一层一层地拥着,每一片都在努力地张开,努力绽放它小小的生命。你禁不住起了亲昵的念头,近前去嗅,淡淡的幽香,是远山后一缕缥缈的呼唤,是蓝天上一抹悠远的浮云,若有若无的,而你能明显感觉到那娇羞的颤抖。

更为诧异的是樱花的花色,几乎一树樱花就是一种颜色。人世间最美的色彩都汇聚在了这里吧,白的是淡雅,粉的是浪漫,紫的是高贵,红的是热情,更多的花色,你无法用文字形容,大自然的美远超乎人类的认知和定义。尤其那种乳白底子上极轻极淡的绿,叫她嫩绿都说重了的,比静夜里春江的水都要柔的绿,比蓝天上满轮的月都要透的绿,仿佛花瓣上罩了一层薄薄的绿雾,不由你放轻了呼吸,只怕一不小心,就会被吹得支离破碎。
女儿早已是尖锐地叫着,一路奔跑一路欢呼。樱花应该是快乐的花吧,小小的花,小小的快乐。那么多的花,那么多的快乐。妻是精心妆扮了的,在花海中更见娇媚,“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并且陶醉,一如回到了少女时代的兴奋,在樱花间摆出各种曼妙的姿势,与这些短暂而灿烂的美合影。
说其短暂,是因为一朵樱花从蓓蕾初绽到零落为泥只有短短七天的时间,日本有民谚曰“樱花七日”。说其灿烂,是因为樱花的美不止于她盛开时的热烈,还在于她凋谢时的壮烈,迅捷、果断,“落樱”缤纷,宛如“花雨”一般。生和死,一样美得惊心动魄。
盛开的樱花是有分量的,压弯了那些瘦瘦的枝条,使得本来纤细而弯曲的小路更为逼仄。这样一条一条掩映在花丛中的小路,间以透出花间的一角红木楼阁和半片琉璃屋瓦,是极为古典的意境。
寺院里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这时候你才注意到,它们应该是这儿的主人吧。但对了美艳不可名状的樱花,都约好了宠着的,任由她一派烂漫、一派骄蛮地喧宾夺主。
其实,这样的红尘繁华不是青龙寺的本来面目。细算起来,樱花被植入这座避居闹市、独处一隅的寺院,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而在一千多年以前,青龙寺有着另外一种幽静、高远的景致。
在古长安最为辉煌的历史中,青龙寺是位于大唐都城中最高的一处,登临可以俯览整个长安城的乐游原。北对雕梁画栋、殿宇巍峨的皇家宫阙兴庆宫和大明宫,南望千峰堆翠、层峦叠嶂的关中屏障终南山,仰观长天空旷、流云飘飞,俯视林木葱郁、烟水明媚,京师胜景名迹,尽收眼底。因之吸引了众多的名流雅士汇聚于此,观赏吟咏。诗人朱庆馀因之留下了“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的句子;还有白居易的“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韩愈的“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晖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当然,最有名的一首,来自李商隐,他的《乐游原》无疑已成为唐诗中的经典,流传千古,妇孺皆知。
青龙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在雄心勃勃的隋文帝杨坚兴建大兴城(即唐长安城)时,为了超度那些由城中的陵园冢墓迁葬到郊野的亡灵,特意在城中延兴门内新昌坊的乐游原上,修了寺院,取名为灵感寺。又传说为了镇住意图摧毁长安的泸河小青龙,于唐景云二年(711),更名为青龙寺。后来几经兴废,直到北宋元祐元年(1086)以后,寺院废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才渐不为人知晓。
青龙寺的历史,简直就是对佛教“轮回”说的验证。因为有了前世的因缘,才有了今生的结果。
因缘来自于惠果和空海两位高僧。前者是唐代佛教诸多宗派之一的密宗教的大师,后者是东瀛渡海而来“入唐八家”之首的“学问僧”,入此寺拜在惠果门下受法求学,回国后创立了日本声名赫赫的真言宗的祖师。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青龙寺被日本奉为真言宗的祖庭和心目中的圣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遗址的基础上,由西安市和日本的一些佛教徒共同修建了这座小小的寺院,有在院落最高处三层木质架构的云峰阁,有四方佛塔造型的空海纪念碑,还有依照遗址考古完全恢复唐时形制的大雄宝殿,里面供奉了惠果和空海的木雕佛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樱花由日本的佛教徒带来,作为友好的使者,历经数年经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蔚为大观。
历史上的青龙寺最大时面积三百多亩,而现在的遗址只有二十多亩了。虽然小,但布局极为精巧,曲廊回合,小径通幽,绕过一株垂柳,你会发现一个小门;穿过几丛修竹,又会步入一个偏院。踏着咚咚作响仿佛有千年回音的楼梯,循着积满历史烟尘的扶手,我登上云峰阁顶,放眼望去,曾经是长安城中最高的一处景致啊,现在已然被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重重围裹,围裹住的,还有那一寺迷幻的花色和鼎沸的人声。大唐的风流雅致,追之不得,思之惘然。
就想,哪天樱花开过了,再来一次,好好看看这里,看看铅华褪尽的青龙寺——那个时候,她该会有别样的美吧。
兴衰荐福寺
荐福寺的路牌指向一条狭窄而笔直的小巷,两旁拥挤着低矮的平房和脏污的小店。行约数百米,一座敦实厚重的山门隐在小巷的深处,一色的青砖落地,顶部饰以精美的花卉砖雕和“福、寿”字样,飞檐挑脚,琉璃覆顶。山门题额上,仍保留有女皇武则天的御笔“敕赐荐福寺”。其书法采用“飞白体”,字体端庄大方,横平竖直,笔画有力。
进得山门,满目的苍翠扑面而来,立时将门外的喧嚣红尘屏蔽。踏着青青方砖铺就的甬道,两旁是高大茂密的古树,耳边是清冷淅沥的雨声。
雨中的荐福寺游人罕至,我一个人的脚步踏过空旷的寺院,走过千年的时光。
隋唐时,西来佛教如雨后春笋,遍地滋生。当时社会上层为其作古的亲友立寺,用以避厄祈福,已经成为风尚,以皇族为甚:隋文帝杨广为母孤独皇后立禅定寺,唐太宗为母太穆皇后立弘福寺,唐高宗李治为母文德皇后立大慈恩寺……,一时长安城中,佛塔林立。

荐福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皇后武则天急于为此前一年冬驾崩的唐高宗李治追祭亡灵,寄托哀思,选择了一个濒于废弃的皇家旧宅作为立寺之所,初名“大献福寺”。此前,这里曾先后居住过身为太子的晋王杨广(隋炀帝)和英王李显(唐中宗),建筑已有相当规模。
六年之后的天授元年(690年)——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是极其血腥的六年。武则天两废太子显和旦,诛杀皇族、大臣数百人,改唐为周——武则天亲自改名并题书“敕赐荐福寺”五字赐给寺院。一字之变,淡化了献福寺“为先皇帝献福”的专祭职能,而加强了武则天自喻“弥勒下生”的宗教政治意义。当时的荐福寺“占地三百亩,度僧三百余”,可见规模之大,而它最特殊之处在于一寺就供奉了三尊弥勒佛,可见武则天对该寺的器重。即使到了武宗灭佛的毁寺时代,武宗李炎(841-847年)仍明令保留“上都左街(即唐长安城中朱雀大街东)留慈恩、荐福,右街(朱雀大街西)留西明、庄严”而未触及。
宝刹总与名僧相伴。说到荐福寺,就不能不提到唐代的一位高僧:义净。现在的义净寂寂无闻,而在唐朝,他和大名鼎鼎的玄奘并称,也是一位西游印度取经的佛学家,并且是我国第一个选择从海路出游求法的僧人。公元671年11月,义净从广州乘波斯商船离开中国,经由苏门答腊抵达印度,仅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就留学十一年,先后经历30余国,25年后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金刚坐佛真容一尊、舍利三百粒。时年71岁的女皇武则天亲自出洛阳东门迎接,可见当时所受隆誉。

在荐福寺的藏经阁里,我读到了这位法门宗师在印度所做的“塔”形怀乡诗:
游,愁
赤县远,丹丝抽
鹙岭寒风驰,龙河激水流
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
已毕祗山本愿诚难遇,终望持经振锡望神州
一腔不畏艰辛万里求法弘佛、心怀故土思念祖国的赤子之情洋溢满壁。
义净于神龙二年(706)随唐中宗李显回到长安,居荐福寺译经,历时八年,直至圆寂,共译出佛学经卷67部。他与玄奘、不空号称中国佛界三大翻译家,也正因此,荐福寺与慈恩寺(玄奘)、兴善寺(不空)并称帝都“三大译场”。
当时的荐福寺内,亭台楼阁密布,广植奇花异草,曲径通幽,流水潺潺。虽贵为皇家寺院,但一直面向百姓开放,除了其特定的宗教含义外,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供市民消遣、休闲的生态园林和文化活动场所。诗人王维游玩后留下了“异花奇谐,群艳耀日,闻钟高阁,觐佛升堂”的句子,唐末进士徐夤在《忆荐福寺南院》写道“忆昔长安落第春,佛宫南院独游频”,唐人温庭筠曾在书中写有男女相爱时到荐福寺牵线传情的佳话,《南部新书》记载这里还是长安城中有名的戏场之一。唐宣宗(847-859年)有一次找万春公主,不见,询问侍者,答曰“在慈恩寺观戏场”,可见寺院之世俗迷人。
但荐福寺仍然没有保留下来。唐末天佑元年(904年),军阀朱温为了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自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开始建设、历经三百多年、壮丽繁华的帝都被彻底毁灭。荐福寺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之后的五代至金,连年战乱使得庙宇成为一片废墟。
今天所能看到的荐福寺,只是明正统八至十四年(1443-1449年),由藏传佛教法师勺思吉主持重修的部分建筑,其规模比唐时大为缩小。殿宇集中在与山门正对的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一路走来,慈氏阁、大雄宝殿、藏经楼、小雁塔、白衣阁等。
慈氏是梵文“弥勒”的意思,即佛教中的未来佛,常被塑造成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欢喜样子,也就是武则天为自己大造舆论的所谓“真身”。可惜阁门紧闭,不向游人开放,只能怅然而退。
大雄宝殿只留了一张释迦牟尼的画像,其余均被改为书画卖场。因为雨天,游客稀少,仅有的几个书画商昏昏欲睡,对我的闯入不屑一顾。
慈氏阁与大雄宝殿之间用围廊圈起。在其东围廊外,一个其貌不扬的小院子里别有洞天,密密麻麻的栽竖着几百根拴马桩和上马石,应该是寺院或有识之士从关中各地收集而来。桩、石均为青石雕刻,上马石较多相似,两级台阶,高低错落;拴马桩上蹲伏着形态不一的人、狮、猴,顶部均被抚摸得光滑圆润,雨点落在上面,弹起冰冷的水花。一个个凝固的生命,大张着双眼,似乎在寻找知音,诉说那一个个湮灭在历史中的烟云往事。
再往后走,绕过一丛青翠茂密的竹林、几柱老干虬结的唐槐,细密秋雨笼罩下,历经1300年风雨的小雁塔,赫然涌出,宝相庄严。
苍茫小雁塔
与众生汇聚、车水马龙的大雁塔相比,相距4000多米的小雁塔如同一个婉约内秀的处子,深居闹市闺中,自成寂寞风景。
今天,我们不知道公元652年,玄奘取经归来在京城长安营建慈恩寺塔(即大雁塔)时,当时还在济南一个小寺庙里苦心修炼的义净,这位年方17岁的小和尚是否感受到了“浮图高耸,万法归一”的佛门盛况,进而倍受鼓舞、暗自激励?我们只知道公元707年,也就是义净回长安的第二年、武则天去世的第三年、设立荐福寺后的第二十三年,正是在义净与当时的荐福寺住持、佛门律宗大师道岸共同奏请下,朝廷诏准建造荐福寺浮图(即小雁塔)。义净和道岸参与设计、亲自督造,年秋末开工,历时两年,一尊秀丽舒畅的密檐式宝塔惊世亮相。
小雁塔的出身迥异于其他佛塔。朝廷虽然答应建设,但这笔钱从哪儿来?皇帝李显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皇后振臂一呼,号召后宫嫔妃及宫娥、修女捐钱修塔。因荐福寺本是皇家庙产,又是武后开基,更重要的是当时参与集资的数万宫女,绝大多数地位地下孤苦无依,这些青春勃发的生命熬不过寂寞无聊的宫中岁月,只能寄希望于“建塔图报”轮回转世的佛教信仰。
塔作为一种建筑,起源于早期印度佛教,最初只是僧侣们死后葬身之所,多单层,低小。东汉时,塔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与中国特色的楼阁式建筑相融合,愈建愈高大,成为一种象征性和精神性的建筑和标志。
之所以被称为“雁塔”,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宗教的,蕴含着牺牲的禅意:印度早期佛教分为大乘、小乘两宗,大乘戒肉而小乘不戒。一天,有长期未进食的小乘僧众,看见头上飞过一群大雁,一僧长叹:“我等无食,菩萨可知?”话音未落,头雁退回来,自折羽翅,坠殒僧前。众僧大为吃惊,以为此雁定是菩萨化身,舍身布施,于是建塔葬雁,并从此戒食肉。“雁塔”由是得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这个故事。其二是世俗的,充满了红尘的喜悦:唐中期,新科进士汇聚到长安城南郊的曲江池宴饮欢游,之后到附近的慈恩塔下题名留念,并勒石为习;因其名字排列有序,“妙有行列,宛若雁阵”,喻为“雁塔题名”。因慈恩寺浮图与荐福寺浮图相较,规模较大,故称为“大雁塔”,后者,也就被称为“小雁塔”。
作为唐朝留存在长安城中最完整的两个建筑之一,小雁塔保留着几乎原汁原味的初建时形制:外部轮廓略呈梭形,塔身中部最粗,往上依次收缩,造型挺拔优美舒展俊俏,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通体全砖结构,做工简洁洗练朴实无华。
小雁塔建在一个高约三米、方方正正的塔基之上,爬上十余级台阶,即可进入塔内。塔内中空,有木质的楼板和楼梯,此外空空荡荡。沿着扶梯盘旋而上,层层叠压的青砖触手可及,一块青砖仿佛一位宫女浓缩的人生。我尽量把脚步放得一轻再轻,生怕压痛了这些苦命的女子。越往上爬,楼层越矮,楼梯越窄,我几乎是在弓腰屈膝顶礼膜拜了。为谁——被幽禁在高墙深院内的宫女?求经弘佛的义净法师?千古传唱的大唐盛世?忽然,细雨扑面,暮色呈现,却已经上到最高一层了。
在我国存世的佛塔中,小雁塔是唯一可以登顶的一尊。原因说来也简单:小雁塔没有塔顶。
这看似柔美秀气的小雁塔,其实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经历了大小76次地震,其中造成严重毁坏的有两次:1487年8月10日,临潼的六级大震把小雁塔从上至下震裂一条大缝;1556年元月23日,华县的八级强震使得塔顶崩塌坠毁,使得十五层的宝塔剩余今天所能看到的十三层。
在大自然的威力和造化下,小雁塔却留下了神奇的传说:在地震中三次开裂,又在另外三次地震中复合,《长安县志》记载了“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比合之者。”当时人们不得其解,只能归于佛祖的神力。建国后修复小雁塔时,才发现了“神合”的奥秘:唐时的工匠们,在最初建造小雁塔时,就考虑到了长安自古多震的地质特点,将塔基用夯土建成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均匀分散,小雁塔就像个“不倒翁”一样,从公元709年建成迄今,整整一千三百年,任你地动山摇,我自巍然屹立。

站在这无顶的小雁塔上四望:合拢的暮色、残破的外形、悠扬的钟声共同营造了千年宝塔苍茫的意境。
秋雨如泪,连绵不绝,我更愿意相信是那些淹没在繁华文明虚幻信仰之后的唐朝女子,用她们悲惨的人生和坚定的信念护佑着这份残缺的美。
小雁塔闻名遐迩,除了她自身的传奇和美丽,还因为她和她身下的一口巨钟构成了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雁塔晨钟。
“关中八景”名气很大,但这个提法由来模糊,我们无法知晓最早指哪八景?由谁提出?我们只知道最后对这“八景”予以明确的是清康熙年间的关中文人朱集义。
最早提到小雁塔钟声的是唐代诗人韩泓,他在《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中写到:“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描写了在迷蒙的暮霭中寺院空旷幽静,钟声悠悠回响的景色。
千年之后的公元1680年,秋天的一个拂晓,朱集义来到小雁塔。天际明月迟迟未落,大地一片混沌蛮荒,忽然钟声响起,浑厚洪亮的钟声划破寂静,惊醒残留的梦境,晨霜笼罩下的千年名刹宝塔,充满了无限的神秘和苍茫。朱集义于是挥笔留下了“噌吰初破晓来霜,落月迟迟满大荒。枕上一声残梦醒,千秋胜迹总苍茫”的诗句。

在陕西的文化史上,朱集义算不上一个名人,历史资料极其稀少。他一生中最大的成绩好像就是围绕这“八景”分别作了八首七绝,绘了八幅图画,当时有石匠把它们集中篆刻。这通《关中八景图》的石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现存于西安碑林。
“晨钟暮鼓”凡寺皆有,何以唯独小雁塔的晨钟能够跻身于“关中八景”。原因在于小雁塔的钟身巨大,钟声洪亮,“声闻数十里”,堪称陕西梵钟之最。
“雁塔晨钟”的实物依然吊置在荐福寺的钟楼内,只是作为文物,仅供观摩,不让敲击。遗憾的是我连观摩的福分也没有,钟楼大门紧锁,我只能从门缝中窥视,一瞻“晨钟”真容。
光线昏暗的钟楼内,硕大的钟体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空间,上面铭文模糊,灰尘遍布。在钟身正下方,有一个大坑。其实这个坑,正是小雁塔“晨钟”声响音远的关键所在,坑口正对钟口,击钟时一部分声音从此坑通过地下传送,人若伏于地,似闻声从地出,深沉浑厚。
据载,此钟铸于南宋时代金章宗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钟身通高3.55米,口径2.45米,口沿圆周7.65米,重八千公斤。最早悬挂在陕西武功靠近渭河边的崇教寺内,因渭河发水,冲毁寺庙,大钟沉于河床泥沙之下。康熙年间,有村妇在河边洗衣,用木杵捣衣,忽“声自石出”,响闻数里,妇惊走。众人报官,遂于河石下发现巨钟,移置荐福寺。
清末,此钟已被神化。传说有信徒将心愿写在黄裱纸上,祷告之后贴于钟壁,然后以杵击钟,所许之愿可还;有或思念远方亲人,击钟时默念亲人姓名,无论千里万里,均可感闻钟声,或回程,或回音,告慰亲情。直到民国末年,钟已残,楼已毁,而钟壁上,依然贴满了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黄裱纸。设想一下:在那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时代,这样的一张纸上,蕴含了一个怎样辛酸的故事?寄托了一个怎样渺茫的希望?
1926年,这口钟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刘镇华驻军在荐福寺,攻打西安城,需要军火补充。当时寺院废弛,晨钟裸露,有人就打起了主意,建议毁钟造军械。刘镇华即命手下以捆雷炸钟,没有成功,却给晨钟留下了一道长约七米的裂痕。也有传闻,此裂痕为战时流弹所袭。
1993年,钟体伤痕被焊接复原。当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晨钟再次被敲响时,却让人们大失所望:钟声沉闷混沌,远不如传闻中的“如闻神明之音”。也许,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沧桑,钟也累了。
远外忽有钟声响起。我循着钟声走去,在小雁塔的东南侧,一口乌黑锃亮的大钟露天悬挂在四根金色柱子搭成的粗壮木架上,四周彩旗环绕,花团簇拥。诚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只是一口后来铸造的仿制铁钟,供游客敲击祈福。
我用双手推动沉重的木杵,让那悠扬的钟声破穿秋雨,直抵遥远的故乡,护佑我年迈的双亲平安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