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第一剪”韦纯葆
文/陈清泉

韦纯葆在剪辑室观看样片
新中国电影的剪辑师们,十分推崇上影韦纯葆和北影傅正义这两位剪辑大师,将他们并称为“南韦北傅”。1980年,这两位大师发起成立了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傅任会长,韦任副会长,一时传为佳话。
韦纯葆192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39年,他13岁时经姐夫陈翼青介绍到新华影业公司当学徒——学习剪接(今称剪辑,但一字之差说明当时将这一工艺当作纯技术工种,而新中国的电影界对这一行当正名为剪辑,表明这一工种包含了艺术创作的成分)。屈指算来,到2005年完全离开剪辑台,他在电影剪辑这个岗位上勤奋工作了66个年头,见证了中国电影剪辑技(艺)术的进步和发展。说他是新中国剪辑界的元老,称他为上影的“第一把剪刀”是当之无愧的。
在新华影业公司的六年,是他勤学苦练基本功的六年。说是学习剪接,但剪接与洗印车间合在一起上班,分工并没有那么明确,剪接、洗片、印片、放映……等都要干,吃住也在厂中。姐夫陈翼青是一位剪接、摄影、制片、剧务、导演等都拿得起来的多面手,经常手把手地教他掌握剪接技巧,加上徐亮、许明等五六位师傅的言传身教,到1945年应云卫导演在国泰影业公司拍摄《忆江南》时,韦纯葆已和师傅们一起剪接这部影片了。
1946年,对于韦纯葆来说是他个人从业史上最重要的年代之一。这一年,他独立担负了杨小仲导演的《莫负少年头》的剪辑工作,他将从陈翼青、许明、徐亮等大师们那里学来的剪辑技巧,全部运用到这部影片的剪辑之中,获得了他的师傅们和杨小仲导演的赞许,鼓舞了他全身心投入电影剪辑事业的信心。在上海解放前的短短四年中,他为文华、国泰、益华、上实等多家公司剪辑了《大地春回》《浮生六记》《残冬》《春归何处》《马路英雄》《小城之春》等二十多部影片。
1947年夏,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认为:《生死恨》这台京剧以主人公韩玉娘的不幸遭遇揭示了反侵略的主题,是《抗金兵》的姊妹篇。在与费穆导演商议后,决定将这台宣扬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搬上银幕。
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但当时只有16毫米的彩色底片,而声音却是35毫米的胶片,造成了声带与画面不同步,也给剪辑工作带来难题。
韦纯葆应召来到费穆家中,与费导一起剪片子。那时35毫米的放声机是要用手摇的,声音当然不均匀。而且光学声带是不能剪断的,只好每个声音都要用手工办法对准画面上的口型并做上记号,可以说是用上绣花的功夫,花了六个多月时间,才把这部片子剪好。然后将16毫米的拷贝送到美国去加工做成35毫米的拷贝,否则是不可能在上海和全国放映的。韦纯葆原名韦顺宝,由于要在片头字幕上挂名,而费穆先生觉得这个名字“太旧”,向他提出改成“纯葆”,并且指出:“纯葆两个字符合你的性格”。从此,韦顺宝成了韦纯葆,一直使用至今。韦纯葆在谈及此事时依然十分感动。
《小城之春》是他和费穆合作的第一部戏,韦纯葆说:“费穆是位大导演,人很文雅,很有水平,他第一次教我剪片时很放手、很细致、很有耐心。”这三个“很”字道出了韦纯葆对费穆很高的评价。因为,费穆在拍摄时就从不同的机位拍了好几条片子,选择余地大,他从导演选择的片子中揣摩与观察导演的意图与艺术见解。在这次跟着费穆剪片的过程中,他不仅领略到费穆导演十分缜密的艺术构思,而且还常常从费穆的指点中知道了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剪,另一个镜头又为什么那样剪;以及胶片怎么对接、怎么掐时间,缺了点什么时应怎样补救,等等,十分具体而包含着丰富的经验。通过《小城之春》,韦纯葆在剪辑技艺上突飞猛进,开始向这门艺术的高地进军,终于在积累了大量经验后成为中国电影剪辑界的领军人物,这是与他在解放后的一段经历有关的。

《小城之春》海报
解放后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了剪辑科,韦纯葆奉命去翻译片组,在组长陈叙一(后长期担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一职)领导下从事翻译片的剪辑。十分用功的韦纯葆利用“摇”(检查)片子的时机,了解到许多苏联电影的镜头怎么衔接,一场戏镜头又怎么组合、如何转换。他把片子颠过来倒过去地反复看,悟出其中道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从翻译片中学到很多东西,在后来的剪辑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是我妻子陈婵的舅父,在我调进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之前,他已经是厂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和技术科副科长。在我进入电影界后漫长的三十个年头中,我们虽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工作,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确实受到他的支持和影响。
我进入天马后接的第一部戏是戏曲艺术片——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作为该片的场记,在影片制作完成后要写出一个“完成片剧本”。
这个本子在混合录音时已经写好并进行过初步校对,但为了量每个镜头的长度和检查剧本是否绝对准确,我必须进剪辑间“摇片子”,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量好尺寸(胶片以呎作计算长度的标准,不足一呎时则按胶片上的每个画面为一格加以计量),同时检查并纠正剧本初稿,连演员的动作、台词落在几号镜头上也要写得明明白白,如演员甲在15号和16号镜头中说了一句“你怎么没到我家来,让我等了半天”,15号镜头为中景,他向对方说“你怎么没到我……”16号镜头为近景,他继续说“我家来,让我等了半天”,就得分两个镜头把哪句话、哪个字落在哪一号镜头上标清楚。
完成片剧本既要标明从1至若干号的镜头序号,还要标明这个镜头是远景,还是全景或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等,更要写清楚人物在画面中的地位,他们的对话、动作,以及地位的变动和镜头在对话的哪个字开始作推拉或摇移的运动及运动的停止,还要写上鸡鸣、犬吠、开门、打枪等效果声所在的位置以及音乐的起讫,等等。
有一天,我正在量镜头尺寸时感到身后来了个人,我转脸一看原来是韦纯葆,便叫了声“娘舅!”他答应后对我说:“完成的台本今后要附在每一个拷贝里面,会到达每一个放映单位、放映人员手中,让他们了解画面内容、长度等等,所以准确性最重要。”这话我的同事也是入门老师张秀芳曾经对我说过,他又这样提醒我,让我更加认真、细致地去完成这影片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在我后来的几部戏中,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撰写的本子,与影片没有丝毫出入,曾得到过张骏祥导演的表扬。
他还对我说:“量尺寸虽然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但你应该知道,电影蒙太奇的产生和实现,是在剪辑台上完成的。如果你趁此机会通过剪辑好的完成片,去琢磨一下导演在镜头组接上的创作意图,了解一下这场戏的‘蒙太奇’构思,就可以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得到启示。”
他的这些话使我想起了他的一句名言:“剪辑工作应该有‘两栖性’,它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它的艺术性比技术性还要重要。”
他的这些话,使我对场记工作的认识进一步升华。进厂时,齐闻韶副厂长找我谈话时,曾经说到场记与导演的关系以及这一岗位对于初进电影厂的人是个极好了解电影创作规律的机会。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摄制组,我十分注意导演与各艺术创作部门的活动,力图将种种艺术实践活动储入我的记忆并细细地品味和化为自己的心得。比如:我曾经详细地记下了这个摄制组七十多个特技镜头的拍摄过程,弄清楚了孙悟空在银幕中“上天入地”“千变万化”的艺术效果是怎么达到的。在做完成片剧本的韦纯葆对我的谈话,推动着我在后来的几部影片中以海绵吸水的方式,贪婪地允吸着摄制组所有的活动成果——从每一个制作阶段、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不同创作部门和创作人员的活动中及谈话里吸取养分并从中获得了疗饥解渴的快感。应该说,他的“两栖论”让我引申到场记工作上来,启发我认识到:场记,也是一种技术与艺术“两栖”的岗位——如果你把场记看作只是导演的事务性、技术性方面的助手,那么你的工作就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如果你接受了“两栖论”,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工作所包含的艺术成分,那你就有可能把这个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去认识、去吸取艺术营养,从而在实践中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由于在场记工作中的积累,我后来在上影文学部担任编辑工作时,便可以从导演及其他创作部门的角度、从画面效果来评判剧本的高低优劣,并要求作者在创作剧本时要有镜头感。粉碎“四人帮”后,为了重建制片生产的新秩序,文化部派人来沪起草不同部门、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任职要求时,厂里派我去参加起草。正由于我在场记工作中对各个部门不同工种岗位有较深的了解,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经讨论后形成条款撰写了100余种岗位任职要求并经文化部颁布施行。后来,我调往厂部负责经济工作时,对厂内不同行当应抓住什么环节来实现更好的效益提出要求,并对摄制预算进行审核和指出哪些地方可以削减、哪些地方应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在那四部戏中通过场记这一岗位打下的基础,而韦纯葆的“两栖性”的观点对我的启发是我热爱场记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韦纯葆是“两栖论”的创造者,也是“两栖论”的实践者,他与谢晋的合作,让他在技术与艺术这两块天地中自由地飞翔,获得许多令人满意的业绩。
那是1953年的事了,他参加了陈西禾导演的《妇女代表》摄制组,而谢晋则担任该片的副导演,于是他们相识了。这时,谢晋才三十岁,而韦纯葆还要小谢晋四岁,当年才二十六岁。两位对新中国电影事业怀有美丽憧憬的年轻人在艺术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使他们常常坐在一起探讨艺术创作上碰到的许多问题。韦纯葆深切地感受到,谢晋的独到之处是他往往从导演的角度,将剪辑师的工作提升到参与导演创作的高度,使韦纯葆产生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处理剪辑工作的激情。
隔了几年,他俩又在《女篮五号》一片中相遇,这时谢晋已是独立拍片的导演了。他要求韦纯葆多看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影片,剖析这些影片的镜头组接技巧,将那些堪称传世之作的剪辑精华拿来丰富自己的技艺。于是,韦纯葆不仅用心地观摩谢晋推荐给他的影片,而且自己还找来了好莱坞拍的体育片《出卖灵肉的人》——这是一部以拳击手为主人公的影片,著名华人摄影师黄宗霑为了在画面上创造动感,他脚蹬着溜冰鞋跟着运动员“满场飞”,摄影机与演员及场内观众的互动所创造出来的画面效果大大提高了影片的感染力,曾在国际电影界引起轰动。
他将这部影片看了好几遍,然后又坐在剪辑台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解剖,研究用这种特殊拍摄方法所形成的节奏感,并在吸收这部美国体育片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女篮五号》的剪辑阐述,并在摄制组谈了他的看片体会。
谢晋读了这份阐述以后,赞扬韦纯葆的种种设想十分新颖,认为他对未来的影片应该怎样结构的意见对实现导演构思可以产生独特的作用。谢晋还认为:这份剪辑阐述中的许多很有见解的想法,对其他创作部门也有参考价值。
全剧有四场球赛,韦纯葆建议:在拍摄球赛现场使用两台摄影机,一台手提小型“埃姆”摄影机可以从不同地位、不同角度拍观众。实拍时,韦纯葆坐在观众席的观众演员中,根据不同情节招呼摄影师拍摄哪一部分观众。这些东偷拍一个、西偷拍一个的镜头组接起来以后,果然产生了奇特的效果——现场感和动感特别强,竟然与黄宗霑拍摄的场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谢晋的合作,韦纯葆的剪辑技巧上了一个新台阶,人们评价说:《女篮五号》剪得干净流畅,使主题更为鲜明、人物形象更为动人,这要归功于导演懂得剪辑、剪辑参与了导演的创作。这进一步证明了他的“两栖论”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在此后的剪辑生涯中,他剪辑的《为了和平》《山间铃响马帮来》《布谷鸟又叫了》《三毛学生意》等影片都获得了成功,并形成了他的剪辑风格——节奏明快而流畅,为圈内人所称道。
他的经验在剪辑师中广泛流传,他曾经将这些经验归纳为:一个优秀的剪辑师,除了熟练掌握剪辑基本功外,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他自己就读过大量文学著作,每参加一个摄制组,总要反复研读电影文学剧本和导演分镜头剧本,分析和理解导演的艺术创作构思,提出自己的剪辑方案。他说:剪辑只有“进了戏”,才能根据该剧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影片样式及导演风格进行剪辑。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完全融入各个艺术创作部门的成果之中,使剪辑成为综合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

《女篮5号》海报
有时,导演的创作意图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未能实现,又失去了补拍镜头的机会,因而让人感到“遗憾”,谢晋导演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就包括这种遗憾。遇到这类事,韦纯葆会想方设法利用剪辑尽可能地来弥补。他在《红色娘子军》的剪辑中就有一些生动的事例。
在洪常青英勇就义那场戏里,战士们十分伤感,痛哭失声。这是一场十分动人的戏,但审查者却认为“情绪低沉”,通不过,重拍了几次还是未能通过。谢晋还想重拍,他舍不得这组可以将吴琼花在洪常青就义时两人心灵互通、情感交流的动人场面。韦纯葆认为:怎么样重拍也难以让审查者去除成见,不如在剪刀上想想办法,下下功夫。
于是,韦纯葆将拍了好几次的片子集中起来,选择了那些可以表现得昂扬一些的镜头,重新加以组接。于是,一边是洪常青在熊熊烈火中英勇就义,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并传到另一个山头娘子军们和琼花的耳畔,吴琼花与战友们将泪水化为一腔复仇的怒火,将仇恨变成了摧毁旧世界的坚强决心。烈士与战友们的心在几个镜头的跳跃中紧紧连结在一起。审查者们满意了,谢晋的意图也达到了。

韦纯葆与秦怡
其实,洪常青就义的所在与娘子军的驻地并不相连,吴琼花们是看不到洪常青,也听不到他呼喊的口号的。几个镜头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观众与剧中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也就不会从空间是否允许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反而会承认这种剧中人心灵上的互通,可以打破生活中的时空限制形成电影中的时空关系的。这一组镜头确实是大手笔,是剪辑创造的艺术上的辉煌!
1971年,他从“五七干校”调回上海。1973年由天马、海燕合并后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并建立了技术办公室,著名摄影师黄绍芬担任了技办主任,韦纯葆则成了他的助手担任了常务副主任一职。这时的技办要管理摄影、录音、剪辑、化妆等部门以及照明车间、水电车间和洗印车间的建造。
洗印车间,是许多摄影师梦寐以求的技术设施,有了它,拍好的片子很快可以冲洗出来,让摄制组及早看到样片,大大缩短了等待样片的时间,有利于摄影棚的周转和提高利用率。韦纯葆受命负责车间的建造,从此又肩负了基本建设工作,包括修建职工宿舍等等。而厂里技术保障方面的业务包括器材调拨、人员配备、设备更新、经费管理、业务培训……都需要他协助黄绍芬去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和推广。他在使出浑身解数的同时,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来应付繁忙的工作。
我调进厂部工作后,与他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频繁了。初进入厂的领导岗位,许多事我都摸不到门,但我明显地感到他是怎样地为我“补台”的。
例如:技术部门每年都要制定一个十分周密的设备更新计划和一份年度经费预算,这通常是要由分管厂长亲自参与其事,我当然不明白这个程序。
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吧,他跑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清泉,我们技术部门要制定一个明年的更新计划,要花一点钱的。过去杨师愈(副厂长)过问这件事,现在你要参加。”这就提醒了我,让我不敢大意。于是,我去找了技办的负责人黄绍芬、苗振宇和柳和纲(具体负责这方面的技办工作人员)及韦纯葆一起商量了大的原则。在他们制定出预算和计划后又进行了仔细的磋商,使我避免了被动,及时地将计划预算提交厂领导讨论并作出决定,保证了第二年技术部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这次反复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对各技术部门、各个工种的状况和各种技术标准了如指掌。正因为他如此熟悉技术部门的各项业务,他经手制定的计划和预算反映了实际需要与可能,在厂里经济状况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分步骤地解决了问题成堆的现象。
当时,许多三十年代的、十分笨重的摄影机尚在使用,而较为轻便的阿莱摄影机只有那么两三台,其他器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大家抢着用好设备、新设备的情况下,我的这位娘舅真的成了解决器材使用方面纷争的“老娘舅”了。为了逐步解决这种状况,他与黄绍芬、苗振宇等人一起,提出一个分三四年逐步进行设备更新的设想,经我与他们仔细研究后上报并获得了批准。
从1982年到1984年的三年间,上影厂将原先使用的、不便携带的录音机,全部更换成可以肩背的半导体元件组装的便携式录音机,更换了大部分摄影机,将三号摄影棚改建为新录音棚并配备了全套新设备,新建的洗印车间已从论证进入到设计阶段,不久就开始施工,新的特技摄影棚也正在建造中……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条件,为上影厂每年生产十九部影片创造了优良的条件,在形成这种技术保障条件的过程中,人们都能看到忙碌的韦纯葆的身影。
就在如此繁忙的工作状态下,韦纯葆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忙里偷闲地活跃在剪辑台上。在那些由他独立剪辑或帮助他人完成剪辑任务的影片中,《泉水叮咚》与《青春万岁》是应该记录在电影剪辑史上的佳作。
《泉水叮咚》是青年女导演石晓华首次担纲执导的大型故事片,而摄影、美工等部门的主要创作人员也都是中青年同志,他们有理想、有干劲,但经验不足,拍的素材有不少枝蔓。厂长徐桑楚等厂领导看样片后,一方面肯定了这些年轻人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指出了上述不足,决定将韦纯葆请来协助原剪辑,解决样片存在的结构松散导致戏剧情节不能充分展开、许多好戏淹没在无关紧要的场景中等存在的问题。
韦纯葆与导演石晓华会同厂里请来协助石晓华工作、曾经当过石晓华老师、又是艺术上很有成就的女导演颜碧丽一起反复观看了初剪的样片,研究并制定了几个剪辑方案。在导演敲定了方案后,韦纯葆大胆地改动了结构,砍掉了许多枝枝蔓蔓,围绕着导演刻意追求的情和趣、尤其是儿童们的童趣,将有些情节做了调动,在重场戏的铺垫和渲染上下了大功夫,终于将所有“有戏”的地方剪了出来,将原来片长达一百六十分钟的样片剪成了完全符合片长要求的九十分钟的完成片。这部儿童片在公映之后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获得了1982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金鸡奖”特别奖、新时期十年电影奖处女作导演荣誉奖,以及意大利吉福尼国际电影儿童节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第三届印度国际青年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像奖、葡萄牙第五届托马尔国际青年电影节儿童演员特别奖、伊朗第十五届国际教育电影节教育类影片比赛铜奖。了解情况的人都说:这个奖,那个奖,还应该给韦纯葆一个剪辑奖。
还有一位年轻女导演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她就是黄蜀芹。

《泉水叮咚》剧照

《青春万岁》海报
作家张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万岁》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学生的理想和追求,剧中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的活动把人们带进了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剧本充溢着激情,人物的立体感很强。因而从文学部到厂部都看好这个本子,有人说:“这部好戏不能搞砸,一定要交给经验丰富的老导演来拍。”
但是,厂党委一班人却不这么想,在厂长徐桑楚领导下已作出培养青年人、尤其是女导演的计划,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青年女导演黄蜀芹来执导。
这时的张弦已经成功地创作了好几个剧本,并且都已摄制完成了,他深知导演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对“初出茅庐”的黄蜀芹能否拍好他的“得意之作”多少有些疑虑。于是,他找到了黄蜀芹,悄悄地问她:“这么一部大片子,你有多少把握?”黄蜀芹答道:“因为有摄影师单联国和老剪辑师韦纯葆参加,我有把握把它拍好。”几句话掷地有声,张弦放下了心。
《青春万岁》是黄蜀芹的“处女作”,她当然十分倚靠单联国和韦纯葆。在进入分镜头后,她特别请求韦纯葆好好看分镜头本,希望“老韦”能对她加以指点。而韦纯葆在下组以后,便认真地、反复地读了文学本和分镜头本,比较这两个本子的异同,特别注意黄蜀芹对剧本的改动之处,琢磨导演的创作意图,又通过与导演当面交换意见,进一步弄清了导演的艺术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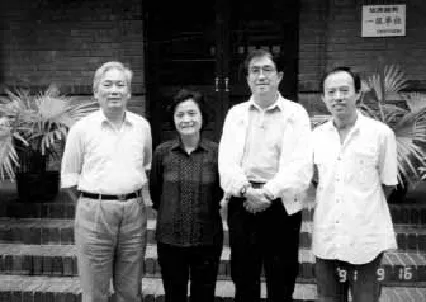
韦纯葆(左一)与谢晋(右二)等人合影
拍摄阶段结束以后,便是韦纯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通过他这把“好剪刀”,解决了结构上松散,加强了场与场连接后形成的张弛关系,在动静结合上作了不少文章。于是,他制定的剪辑《青春之歌》的几大原则,即通过删、加、移位等技术手段达到主题更加鲜明、人物面目更加清晰、情感交流更加充分和准确、节奏处理更加流畅,并且突出了人物的内在情绪。这样的结果,作者十分高兴、导演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并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到了晚年,他仍然没有放弃剪刀,参加了许多电影和电视片的剪辑工作。
从剪底片开始到剪光学声带再进入到磁性声带,他都能“与时俱进”地攻克技术难关,在学习中掌握了新工艺。但电视片与电影剪辑不同之处是,电视片是在编辑机上完成的。
电视剧制作者原先普遍认为:电视片的完成是直接由原磁底“拷贝”出来,即由原底复制到另一条磁带上的。如果片子已经接到后面再去改动前面的片子,那就要推倒重来,工程浩大,所以完成片只能剪(编)一次。
韦纯葆认为:这样的工艺会留下太多的遗憾。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他根据电影剪辑工艺,提议多翻一条原底,在保留第一原底的同时,拿第二条磁片去反复剪辑,然后在第二条原底“完稿”(编辑成功)后,照着样子剪出完成片来,这就不会损害原底了——就这么简单,但在韦纯葆提出这个方案之前谁也没有这样想。于是,这种工艺已为电视界普遍采用。人们评价这件革新时说:“生姜还是老的辣!”
韦纯葆这把“剪刀”是把“宝刀”,已经为电影和电视事业服务了六十多年。最近,他已不再上剪辑台和坐在编辑机旁了,但人们依然怀念这把宝刀,他在剪辑这个“双栖”技艺上的魅力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未衰退。
他一生所创造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剪辑界的地位。在编纂《电影艺术辞典》时,他担任了编委和剪辑部分的主编,在中国电影剪辑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会长。
他的余热仍然散发在电影剪辑事业的热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