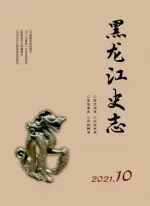西北边疆危机与清代新疆政治中心的转移
丁立军
(伊犁师范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清朝统一新疆,建立了以军府制为主导,郡县制、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为辅的多元化行政管理体制,长期维持了对新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但是,十九世纪阿古柏入侵新疆和沙俄侵占伊犁造成的西北边疆危机使清政府在整个新疆的统治危机空前加剧。规复新疆后,旧制荡然无存。1884年,新疆建省,既采取了与内地划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同时新疆政治中心转移到乌鲁木齐。
一、十九世纪中期新疆的动荡
1864年新疆农民大起义形成了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和田五个中心,新疆各地陷入封建割据。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仅限于东疆的哈密、巴里坤,北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至塔城一线,苟延残喘。这种混乱局面为阿古柏和沙俄军队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1864年8月,占据喀什噶尔的柯尔克孜部落首领司迪克,请求浩罕让大和卓的后裔返回喀什噶尔,企图利用其声望来号召当地的维吾尔居民,维护统治。中亚浩罕时刻觊觎天山南部,乘此机会,派阿古柏挟大和卓曾孙布素鲁克进入喀什噶尔。阿古柏占据回城后开始四出侵略,占领南疆七城并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之后,又率兵进犯吐鲁番、乌鲁木齐,“尽掠其遗货,搜刮汉、回民人金帛转输南路,而驱其丁壮踞守乌垣各城,以为屏蔽”。[1]至1873年,除镇西、哈密、奇台、古城、济木萨尔等城被清军或汉族地主武装拒守,俄国占伊犁外,阿古柏侵占了新疆大部。“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决定依靠军队的力量”[2]的阿古柏政权,靠六万多入侵军对占领区内的各族人民实行野蛮残暴的奴役和敲骨吸髓的剥削。各族人民的正项税收包括“农业税,牧业及商业税,捐税,棉田、果园及苜蓿税,农业附加税,遗产税,草税”等,还有摊派的赋税和劳役,75%以上的劳动成果被阿古柏以各种税收巧取豪夺。沉重的负担……毁得(各族人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这种蛮横的反动措施,遭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如1867年吐鲁番人民反对新税法的起义和1872年乌鲁木齐人民反抗阿古柏的起义。
阿古柏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横征暴敛致使已遭受起义和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衰败不堪,各族人民纷纷沦为奴隶。同时,阿古柏的入侵使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体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在客观上为清政府重构其在新疆的统治体制提供了契机,也为新疆政治中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十八世纪初,俄国开始实施“南下政策”,从西伯利亚自北向南侵略中亚,并不断蚕食新疆西北的大片领土。同时进行经济侵略,1851年,强迫清朝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在我国新疆地方设立领事、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和建立贸易圈等特权,不仅“在商业关系上,而且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成为深入中亚西亚继续进攻活动的强有力的动机”。[3]这个条约的签订从陆上打开了中国西北大门,是沙俄以鲸吞中国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了把侵占的中国领土合法化,沙俄几次要求同中国签订西部边界条约,均被清政府拒绝,俄军开始占据“符合俄国意图的国界线”[4]的许多中国领土。1864年,沙俄利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强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其中包括占伊犁地区4/5的伊犁西路大部分地区,伊犁仅存九城及周围防营驻扎、屯田区。巴布科夫供认:“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有属于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我国领域之内”。[5]沙俄并不满足现状,又阴谋“窃取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而后已”。[6]俄国把侵占伊犁全境视为吞并我国新疆、侵略西北的重要步骤,侵略者认为“伊犁就其位置来说,是一个现存的十分坚固的堡垒,因此,从军事上看,我们必须占领伊犁”,因为伊犁“若以之属俄,则可予俄国边防以相当保证,而使中国受军事上之威胁”。[7]新疆农民大起义爆发前,就曾多次派兵侵入伊犁西部,抢劫牲畜,烧毁村庄。新疆农民大起义后,1871年,沙俄占领了伊犁。侵占伊犁等地后,沙俄假惺惺地向清政府表示只是代为收复伊犁,并无久占之意,一等清政府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当即归还中国。为防止中国人民反抗,沙俄在伊犁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对各族人民逼令指定地区居住,不准迁移;在各地遍设站台,派兵把守,严厉禁止各族人民相互来往。沙俄向各族人民按灶派捐,定居人口征户口税,游牧人口索帐篷税,满、汉、蒙古、锡伯等民族均摊派大批银两。对沙俄的经济掠夺,左宗棠指出,“俄人挟伊犁为重者,贪每岁横征数十万(两)之利”。[8]
沙俄在伊犁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使清朝的西北边疆危机达到顶峰,对新疆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治上,使新疆政治中心伊犁成为抵御沙俄进行战略防卫的前线;经济上,沙俄的掠夺使“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民用繁富”[9]的伊犁,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城池残破。往昔繁荣的伊犁就此衰败了。
二、清代伊犁的兴衰
清代的伊犁地区指伊犁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以霍尔果斯河为界,伊犁分为东、西两路。伊犁的形势是甲西域之地,天山北部因东、南、北三面群山环绕,西部地势稍微开阔,是内外势力出入的重要通道,伊犁就处在这咽喉要道之上。据有此地,不仅东、南、北三面不易受到外敌的攻击,还可以东迫焉耆,西进中亚,南逾天山穆素尔大坂。
1759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后,鉴于伊犁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加强西北地区的边防安全考虑,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犁将军驻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惠远城所在的地方,基本上是伊犁河谷中山水环绕的中心,交通便利。从惠远城向东北行二百余里到达赛里木淖尔,从这里穿过察哈尔驻守的卡伦就可以向东至精河以及乌鲁木齐等地;从惠远城南渡伊犁河,一方面可以达南部乌什,另一方面还能够至喀什噶尔。为拱卫惠远城,伊犁河的北岸陆续修建了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春、塔尔奇等八座卫星城,分别驻扎军队,统称为“伊犁九城”。同时,清政府在伊犁河南岸建有八堡和蒙古营地,从东向西排成一条以惠远城为中心的防卫圈。为进一步达到控驭四境的军事目标,清政府先后调集满洲、蒙古八旗,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到伊犁戍边,目的就是为了强化伊犁将军对全疆的驾驭作用。这样做有三层含意:一是新疆甫定,南北两路都有再生事乱的可能。如后人所说:“督抚必皆住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10]二是新疆之外,还有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及沙俄等各种势力,伊犁驻军既防范新疆内部又防守外患。三是伊犁当时处于全疆中心的位置,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相互支持、制约。可见,清朝统一新疆后,将政治中心设在伊犁是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伊犁成为全疆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伊犁河两岸土壤肥沃,矿藏繁多,冬暖夏凉,宜农宜牧,被誉为“塞外江南”。这里是中国西部边疆的一块宝地,利于发展工农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清政府把戍边与农业生产结合,实行了军屯、民屯、回屯及旗屯等多种形式,屯田所获“谷石极丰”,以至于仓库中储存的粮食、陈陈相因,驻防在伊犁的绿营和满洲官兵的生活有了保证,还吸引了从内地来的汉民。1782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向朝廷报告,伊犁仓内存粮五十万石,以致红腐霉烂,因而一度不得不将兵屯的数量由原来的二十五屯减至十五屯。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伊犁九城建成后,经过多年的经营,惠远城“官兵既众,商旅云集,关外巍然一重镇矣”,[11]“成为中亚农牧工商集中的重要商城,百货云集,市场繁华”,[12]自古“伊犁是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因而城内外寺庙林立”。伊犁之地十数年以来,民庶物阜,有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成为新疆第一大城市。
1864年,新疆农民大起义迅速燃遍新疆各地,1866年,伊犁起义军先后攻陷伊犁九城,成立伊犁“苏丹”政权。惠远城被攻占后,伊犁将军明绪自尽,标志着清朝统治新疆军府制度的结束。沙俄乘机悍然出兵入侵,对伊犁军事占领长达十年之久。原本富饶的伊犁地区,经沙俄盘踞、劫持之后,面目全非。仅就城市来说,伊犁将军所在惠远城“西南两面城垣均已被水冲坏,城内仓库、官厅、兵房荡然无存”,巴彦岱、霍尔果斯“城垣坍塌尤甚”,绥定、塔勒奇、瞻德“城楼女墙均已损坏城垣亦多坍塌之处”,熙春、广仁“城垣楼橹坍塌不堪”。著名的伊犁九城,大半成了废墟。至于农村,“伊犁旧设屯田颇多,现皆一片荒芜,鞠为茂草,桥梁渠道年久失修”。[13]在沙俄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历经百年政治风云的新疆军政、经济、文化中心惠远城被糟踏成一座废墟。
1875年,新疆收复后,经过艰苦谈判,1881年1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满目疮痍的伊犁回到祖国的怀抱。根据条约,伊犁维吾尔等族十万人被迁入俄国,回屯从此销声匿迹,伊犁地区的农业遭到严重损害;《伊犁条约》及其签订的子界约,使沙俄割占中国领土达七万多平方公里。中国西北边疆,由沙必乃达巴汗西北鄂毕河上游地区,经巴尔喀什湖沿岸至西部天山南缘、葱岭西麓一线,向东向南退后了约882—63千米,内缩至由沙必乃达巴汗向南沿唐努山西段向西南,经穆斯岛山、东塔尔巴哈台山、喀拉达坂、阿拉套山,向南至汗腾格里山,再顺西南天山至葱岭北缘一线。[14]四方汇总之地的伊犁,“自分界以来中外之势若处一堂,其地旷野平原,无关山险要可守,一旦有事,而孤悬远塞,征挽兵响,累月不能即至,而彼之铁轨朝发夕至,利钝迟速不可以道里相计,名曰收复,实空城也”。[15]从战略地位来看,伊犁已不再是新疆的中心地带,而是兵临城下、唇亡齿寒的边城,丧失了作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作用。新疆建省后,伊犁的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保留伊犁将军,但职权大为缩小,改称为“伊犁驻防将军”,仅负责伊塔地区的军事和边防。
三、结语
同治年间的大动乱,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秩序“荡然无存”。俄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疆都抱有极大的野心,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更集中、更严密的统治体制,才能保证新疆长治久安,才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1884年,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的建议,在新疆设行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十九世纪末,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新疆省会的选择考虑的是政治影响、商业和交通的需要,军事防御的意义则微不足道。刘锦棠指出“军府之于行省虽均取地方扼要,据其形势便于策应,然比诸营室,行省如堂奥,故多在腹地;军府如门户故多在口隘。新疆大势南北分歧,总以乌鲁木齐为堂奥……如将来行省议定扼要建置,当以乌鲁木齐为最”,[16]他认为乌鲁木齐处于南北疆的交通枢纽线上,可以居一地而控南北,主张把省城设在乌鲁木齐。从此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伊犁转移到乌鲁木齐。“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为了发展当地的社会生产,清政府采取移民垦荒、发展交通、兴修水利、统一货币、兴办工矿业等措施,使乌鲁木齐成为一个“因商而兴”的新兴城市,成为区内的核心城镇,带动了区域内其他城镇的复兴和繁荣。
西北边疆危机,新疆设行省,政治中心从伊犁移至乌鲁木齐,清政府成功地实现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制度一体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清政府开始放弃“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治边政策,实施将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行政制度一体化的政策。说明清政府改变了只注重边疆局势稳定而不重视边地开发的传统观念,开始考虑“移垦设治”、“开浚利源”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现实政治形势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献参考:
[1]钦定平定七省方略[M].陕甘新卷301.北京中国书店,1985:5.
[2]库罗帕特金著,凌颂纯等译.喀什噶利亚[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159.
[3][4][5]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42.253.470.
[6][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O]卷27.卷89.北京:中华书局. 1979:34.10.
[7]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M].昆明:云南崇文印书馆,1946:146.
[9]新疆图志[O]卷29.实业一·商.1923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10]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M].杭州:古籍书店影印,1985:159.
[11]魏长洪.伊犁九城的兴衰[J].新疆社会科学,1987,(1).
[12]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M]第二卷.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432.
[13]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光绪朝)第26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29.
[14]张权.新疆行政区域的变迁[J].新疆地方史,2006,(2).
[15]袁大化.新疆图志(卷1).1923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16]刘襄勤公奏稿[O]卷3.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21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