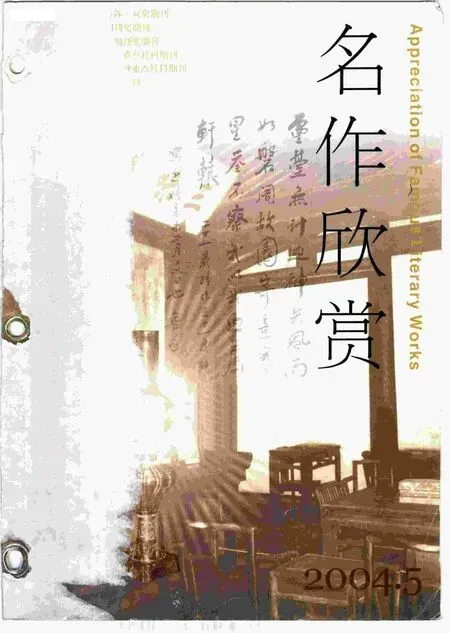时间话语与中国古代诗人的悲剧意识
⊙王利平[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 211188]
在中国古代诗人的审美视野中,时间不是一个中性、客观的抽象存在,而是一个灌注了主体生命意识的美学观照对象。时间通过“回忆”这一心理路径,显露出独立的审美价值,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它已然是诗人的心灵明镜。时间开始作为相对于诗人的客体,进入考察、省思的视野。于是,它带来了诗人心灵上一系列的审美反应,形成了中国式的鲜明的时间话语与悲剧精神。
一、距离:当下与过去的落差
记忆总是包藏和承载着已经过去的存在,回忆就是将这个曾存在的过去时间放置于现在。过去时间已经被诗人视为一个“对象”,诗人成为站立于过去时间之外的旁观者和欣赏者,一改诗人从前沉浸其中的粘合状态而发生了某种“陌生化”和“间离”,而进入到一种审美观照,“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①
其一,落差感。诗人常徘徊于过去世界与当下世界之间反复参照、体认,就产生了生命体验的纵深化。他们常常以一年前—一年后、往昔—今朝、少年—老年这样的时间跨度,对照出无限多的对立项:昔日繁华、富贵、位极人尊、喧闹、热烈、享乐、奢华至极,而今萧瑟、荒凉、地位卑下、凄清、寂寥、穷困、潦倒至极。这种生命的畅达、豪迈、伸展体验和当下生命的逼仄、阴衰、萎缩体验,各自被诗人渲染、强化到极点,在诗人的心中便形成了强烈的乃至“致命”的反差,以及心灵上激烈的撕裂疼痛。他们首先发现了某种美好的沦落或丧失: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陶渊明《杂诗》其五)
继而,往昔繁华与今朝冷寂惨烈对比,造成了主体带着疼痛的失落感,主体在繁华零落后产生了枯槁空洞的人生体验。
其二,梦幻感。过去时间同当下时间之间虽然存在着必然的、不可割裂的联系,但在诗人主观心灵上却仿佛隔绝了线索各自孤立起来。诗人由于过分地凝视“距离”的两端(即过去和现在),忽视了中间联结因素的存在,这使他们感觉到中间是空白的,时间由过去骤然跳跃至当下,两个时间维度之间仿佛失去了关联。反映在诗歌中,这就是诗人的人生梦幻感,一切皆无可解释,充满神秘,人生便如一场莫名其妙的“梦”:“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赵佶《眼儿媚》)我们可以看出,描述今昔巨大反差的诗人多是亡国之君或遭遇人生变数的诗人。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人生行程由明亮豁然骤然沉降至昏暗死亡的底色,以变故事件为交界仿佛突然断裂,而且让诗人毫无心理准备,甚至还来不及接受和思考。人生若梦,醒觉前和醒觉后完全相反,前后两段生命历程的直转急下使诗人仓皇慌乱而找不到联结。
其三,创伤感。在过去时间与当下时间的对照中,一些转折性的重大事件还在诗人的心灵上产生了深刻的创伤感。“心理性的创伤,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创伤的记忆,就像进入身体中的异物一样,必须把它继续看做仍起作用的动因。”②我们对事件的记忆难以耐住自然遗忘,一切记忆都要屈服于这一磨灭过程,但创伤记忆却例外地以惊人的鲜明程度和情感强度顽固地存在下来,对诗人构成强大的心理压迫。在创伤事件中,诗人全部注意力将集中于此并被它所引发的情感控制,进而“通过其情绪的消极过滤器对日常生活事件进行编码(以及提取),从而在他们全部生活经验的表面之上笼罩一层灰暗的抑郁情调”③。他们将把这种短暂却最为深刻的记忆扩展至整个人生,形成强烈的挫败感、毁灭感及生命虚无的彻悟。具体到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如李煜的《破阵子》:“……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诗中的情感是创伤记忆发生后的冷却和沉淀,从而保持了一种“心理距离”。创伤记忆在此亦成为一个审美对象,诗人借助对这一对象的艺术观照和隐喻处理,书写创伤记忆沉淀成的生命“痛感”,暂时缓解积压在心灵上的“受压情感”,以话语的形式对创伤进行洗涤、冲泻与抵销。
二、迟暮之年:“定局”的悲哀
在中国诗歌中,有许多进入老年的诗人在回忆生命历程中试图总结一生,我们称为“结语”,比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诉衷情》),等等。这些“结语”反映了老之将至、死亡靠近、远景缩短的精神疲倦、体力衰退和衰败感。仔细考察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对整个过去时间的回忆生成了一种极具诗意化但又是主观疼痛的张力。人生已成“定局”,生命这项工程已趋竣工,诗人对前路将不能有所作为,生命流露出可悲的“尽头”“收尾”的意绪。
其一,功业未建与人生虚无
儒家贤哲很早就意识到了人“必死”的命运和生命的短暂性,并不像基督教传统为人指出死后来世的归所,儒家截断了这条“再生”之途。死亡必然激荡着文人的生命意识,于是转向了以“精神不朽”作为“永生”的方式,以此超越缠绕主体的死亡恐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岁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宋代张载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这就是儒家的“不朽期待”:以无限的精神空间开拓有限的生命时间,使自己的生命以“精神”的形式在历史长河中久远地延留。而对于一个富于主体意识,有着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人来说,“不朽”便是要建立功业。
诗人以居高临下的俯瞰角度宏观视察个人往事,以深沉成熟的眼光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再审视,获得了难得的高度和深度。岁月流逝,却没有达成生命中建功立业的不朽期待。一方面,岁月流逝了;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诗人发现这段生命却成了毫无价值的一段,流失得毫无意义,从而引发了诗人对自身价值的全面否定。他们在昨日理想和今天实况的对比中,看到了巨大差距,甚至被总结为“一事无成”。
在诗中,诗人“面对着死亡,一切自私的盘算和无谓的纠纷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劳心费神的,因而对周围世界、对自己本人的评价仿佛也扩大了范围”④。科恩还认为,随着年龄而变化的不是自我评价的水平,而是自我评价的价值等级和标准。诗人暮年的价值评定是着眼于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要义,但回顾时却发现珍贵的生命竟然流向了“空无”,其流逝毫无价值。正所谓:
万事云烟飘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初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辛弃疾《西江月》)
诗歌的悲剧意蕴由此生发开来,这是一种震慑人心的生命虚无意识,将导致诗人空活一生的惨烈痛感。
其二,价值体系的动摇与人生迷茫
钱穆先生说:“因为中国古人看人生,不专从其赋得的生命看,而进一步从所赋得的生命之内在本质及其应有可能看。”⑤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过去的生命状态展开理性探索,重新审察生命的“已然”,对照生命的“应然”时,于是秉持一生的价值标杆发生了致命的动摇。
许多具有生命自觉性的诗人秉承老庄玄学,晚年立足于死亡意识,展开了对“功名荣华”这些所谓人生追求目标的猛烈抨击和彻底消解:“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红楼梦·好了歌》)显然,当诗人追问生命中何为终极价值时,“功名富贵”“建功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这些传统价值叙述遭到了深刻质疑和坚决抛掷,从而,几十年生命历程中的价值选择在诗人哲理反思时遭到了否定:
昔年十四五,志向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 今自嗤。(阮籍《咏怀》十五)
诗作是一个典型的回忆-反省结构,展现出传统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轨迹。诗人先是回忆少年时代即志向于儒家经典,并以儒家人生楷模颜回、闵损为精神偶像,其人生取向显然是儒家“三立”的不朽道路入世有为。但以开窗见坟墓蔽野为转折点彻底地否定了原有价值选择,以“自嗤”嘲笑过去生命的徒劳付出。精神偶像从“颜闵”更换为“羡门子”,标志着新的生命价值观念的确立,即蔑视身外之物,结束几十年的迷途式的生存理念,回归存在本身(此身)。这条精神路径就是走向隐逸和山水,神游于天地万物,取消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挟制,达到绝对的自由。
三、宿命:一种深切的无常感
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中,宿命是其最重要的生命观念之一。
其一,无意志的压抑感。钱穆说,命首先从天道之下人的“自性自行”开始,“自性自行,是一绝大的自由,同时也是一绝大的束缚。人类一切束缚皆可求解放,只有自性自行的那一种最大的自由,它在束缚人,人不该向它求解放。中国古人则指说此一种再无从解放者曰‘命’”⑥,也即“天命”。古人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都由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即“道”来操持,任何人必将被它挟持入一个命运的轨道。这股冥冥中的神力是不可违抗的——即使违抗,主体也无法寻到违抗的具体实在的对象——人在它面前生来便孱弱而无知。
宿命论使诗人与最终命运面对时,常常有一种无意志的压抑。正如朱光潜先生讨论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时揭示的:
他的头上随时有无可抵抗的力量在威胁着他的生存,像悬岩巨石,随时可能倒塌下来把他压为齑粉。他既没有力量抗拒这种状态,也没有智慧理解他。……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⑦
诗人不是哲学家,并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纯粹理性、逻辑的分析,只把一切归于玄妙。南宋词人辛弃疾老来看取平生遭际,从年少时的“名利奔驰”,到暮年时的愁病,只觉得命运的神秘莫测与无可掌握:“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西江月》)诗人陶渊明站在现在一点上回顾过去时,就顺任了天命:“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神释》)他因为“委运”,反而摆脱了无意志的压抑感,获得了精神的解放,获得了心灵的大宁静和人生的大自由。
其二,深切的无常感。诗人进行生命反思时,“不仅从自己一面之努力与奋斗进程看,还从其奋进历程之沿途遭遇及四围环境看”。当诗人不凝视宿命的终点而凝视生命行进的过程时,会产生深深的生命无常感。一是纵然生命是一幅被制定完备的卷轴,但作为无助而无知的个体无法领悟天命在己身上施行的规则。对于自己来说,无法把握自身未可预知的行程。二是回顾自己的生命过程时,诗人往往只是凭借直感,并不运用哲学家的纯粹理性思辨在各个事件中建立一种必然的链条,不容易寻到线索性质的因果联系。因而他会感觉到,人生仿佛皆是一场场偶然的混乱连缀,全是不知来由的偶然事件。他更会惊诧自己是如何被抛入深渊,堕入当前这样一场难以解脱的困境。诗人的困惑不解和命定论结合,让他回眸生命中过去某点到现在的里程时,省略诸多因素迅速由始点到达终点。这种瞬间的完成性,让诗人体验到世间变化是如此难以预料,而找不到生命发展到现状的因缘。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李煜《乌夜啼》)钱锺书先生对此种意绪有过精辟的描述:
前尘回首,怅触万端,顾当年行乐之时,即已觉世事无常,抟沙转烛,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登场而预有下场之感,热闹中早含萧索矣。⑧
可以看出,诗人的命运无常感是从一系列对照中飘逸出来的。一切仿佛还鲜活地存活在昨天,而今天竟遽然沦落:从昨天的繁荣喧闹瞬间跌入今天的零落萧条,从昨天的壮志少年瞬间跌入今天的垂暮老朽,从昨天的功业辉煌瞬间跌入今天的冷落寂寥等等,仿佛这一切只是宿命而已。这场巨变震荡着诗人敏感的心灵,而且,由于从此情境到彼情境对照是如此强烈而迅猛,这使诗人感觉人生便如“黄粱一梦”。“梦”成为诗人归结一生、概括无常感的最主要的词汇。人生无常,也不过是“梦一场”,氤氲出中国古典诗歌浓烈的沧桑感和凝重风格。
四、面对宏阔历史:生命有限的苍凉
历史是一个悠长的“过去时间”,也就是曾经发生了的现实,曾经是一幅鲜活的画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生动的历史感性形式都化为宁静的记忆。
其一,兴亡更迭的苍凉感。数千年过后,历史曾有的声音、色彩,历史曾有的人的呼吸、动作,都被时间磨灭或掩藏,最终化作一种“博大厚重的宁静”。这宁静将使诗人猛然惊醒,既而追忆、反省历史的那场喧嚣:“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刘禹锡《金陵怀古》)历史的频繁兴废更替里,沉淀在诗人心中的是对昌隆治世的深切怀念,对血腥动荡的惊慌,对颓然败落的同情,对风云变幻无序的无常感,这些复杂情感综合为一种失意与苍凉。面对金陵的兴亡故事,李白同样传递了一种历史面前的苍凉意绪:“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
其二,被历史淘洗的空无感。在诗人看来,历史是一条绵延的河流,不能追溯它的始点,一直绵延至诗人的“此在”,并时刻欲将现在转化成历史。于是诗人在历史河流面前思量两类人。一是已经逝去的被存档在历史中的个体,他们占据历史绵延的“一点”,他们的命运被时间的洪流淹没、湮灭。无论生前曾经多么显赫辉煌还是贫困潦倒,无论生前位极人尊还是万人足下,都被历史“淘洗”,而只归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正如《浮士德》中所说的:“我们坐在金字塔前,阅尽诸民族的兴亡;战争、和平、洪水泛滥——都像若无其事一般。”另一类人是也处在绵延时间河流中的自己。诗人心中感到自身同样是历史与将来之间的“一点”,一个“瞬间”,同时也必将如同前人一样被时间扫除。于是,相隔久远岁月的心灵开始对接、对话、理解、互诉。时间宿命的相通,使得诗人与古人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历史悲凉: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此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青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温庭筠《过陈琳墓》)
其三,生命有限的悲情。发现己身亦将被无情“淘洗”或被历史收编之后,诗人开始省察己身的现世生存。功业未成而时间催人老去,时不我待,生命终点即将来临。苏轼因而赞美周公瑾而伤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人被困陷在自然的那种既定的机械运转中,他们逃脱不了盛衰荣枯这种自然的循环往复的变化。”⑨诗人伫立“现在”回顾历史,就产生了个体生命有限而历史之流无限的悲情感知。相对于邈远的历史,个体生命只能是倏忽“一瞬”,有限性的个体“暂存”于人世。历史的不可返回,未来的不可预知,将个体打入精神了无寄处的恐慌和难以言明的巨大孤独中。一句话,历史将把一切变为过去,历史便是一种残酷的吞噬力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陈子昂就将这种复杂幽曲的历史情绪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了。
①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② 布洛伊尔、弗洛伊德:《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绪言》,见《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页。
③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高申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④ [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一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佟景韩等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44页。
⑤⑥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页,第33页。
⑦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⑧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8页。
⑨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