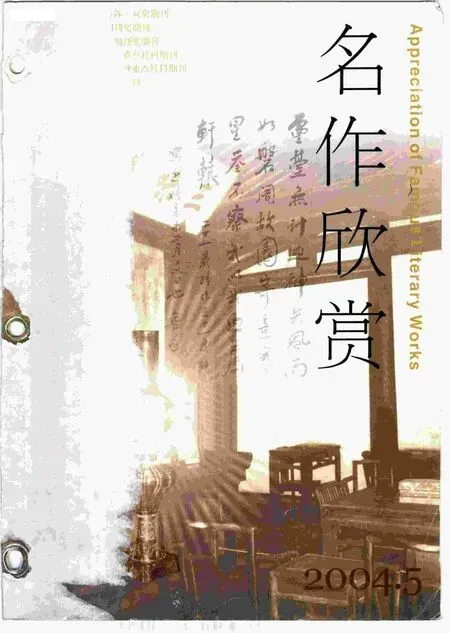奇迹的降临——论伊丽莎白·毕晓普
⊙黄丹萍[中山大学, 广州 510275]
作 者:黄丹萍,中山大学文学硕士,曾就职于驻外领馆,发表随笔与诗歌于《明报月刊》《香港文学》《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上,诗歌翻译作品发表于《中西诗歌》及美国《新大陆》等诗刊。
一、灵动的鱼
足够的水,这本应盛着空气的桶变成了冒气泡的桶,水泡沸腾着、闪烁着,一边还滋滋响着,我觉得。隐隐约约地我知道这些泡泡是要用来装饰的,为了某种庆典。
和《鱼》得缘于一个梦一样,另一首同样采撷于梦境的诗是《在渔房》,在这首诗中,诗人描写回到童年熟悉的海边,静静看着海水的流动,凝望着这片“轻轻地,心不在焉地浮游在石头上”的海,漫过礁石,然后淹没整个世界。诗中所述风景大多是诗人返乡后所见,不过有许多诗行都是梦中所得,老渔夫便是来自于梦境,毕晓普用这个在暮色中独自坐着织网的老人,让整首诗浸润在一片银白色的光泽中。老人一边在海边等待鲱鱼船进港,一边修补着渔网。刮掉无数美丽的鱼鳞的老渔夫仿佛真的存在着,可他身上又隐隐约约有一层似真似幻的色彩。
这是在这样的色彩描述中,毕晓普从观察慢慢地走入事物。某种程度上,毕晓普的诗和美国画家爱德华·霍伯(Edward Hopper)是接近的,他们的诗与画都没有熙攘的人群,却惯于呈现事物,打开自然的窗户,比如早晨的清冷,深夜的路灯等,这都是美国艺术细腻、充满哲思的一面。
读毕晓普的诗,偶尔会感觉像她刚刚说完一个奇妙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往往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她尤为他人称誉的是观察,她望着一条鱼,一只矶鹬,就仿佛像年轻的恋人望着春天的花蕾,像黝黑的西班牙人弹着吉他。
万物都有灵性,关键在于你如何唤醒它,对那些寻常的事物,一条鱼,一只突然出现的动物,一幅地图,月亮,
在《纽约客》的编辑霍尔德·莫斯(Howard Moss)来到巴西的时候,毕晓普带他去了里约的蕨类植物园,那是她常去散步的地方。毕晓普总是可以迅速而准确地叫出各种奇特动人的鸟儿的名字,面对那些动植物,她成了一个好奇的孩子。他们散着步,还在植物园里一起诵读了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的诗歌。
还有一次,毕晓普和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一起逛动物园,两人在一头大象面前徘徊。毕晓普指着它新奇地说:“瞧,它的皮肤像青蛙。”玛丽安·摩尔当即说:“这个比喻不错,我能用它吗?”毕晓普点头同意,后来它果然出现在玛丽安·摩尔的诗《群猴》中。
读毕晓普的诗,如同听流水在说话。她笔下的动物、植物、微细的描写都是流动的,是一只猫或者一朵玫瑰,拥有灵性,缓缓绽放,属于草木虫鱼的不规则的美。它自有其呼吸,是活生生的物体,可以感触到肌肉、皮肤、眼睛和温度。那条放在船边的《鱼》,“遍体鳞伤而又庄严自若”,面对诗人注视的眼光,他也只是“稍微动了一下,却毫不回应我的目光”。鱼的自尊与庄严不由得让人对自然力量产生敬畏之情。在这首诗中,诗人用“他”而不是“它”来称呼这条鱼。这并非拟人化,而是在毕晓普的眼中,这条鱼和人并无二致。
关于这条鱼,1937年毕晓普曾在日记中记录下一个梦,她后来还说,这是她一辈子最喜欢的梦:
这条鱼可真大,约摸有三尺长,鳞片如同金属薄片,闪着美丽的玫瑰红色泽。我自己在梦里则显得略微小些,我们在水中相遇……澄澈,透着光(很像是翡翠,也像烈日下白桦树的叶片)。这条鱼很亲切,说乐意带我到鱼群中区,不过,我们得快点才能赶上鱼群。它游在前面,隔一会儿就用大大的眼睛回头看我,看我是否跟了上去。我自在地在水里游着,又似乎没有做出任何滑翔的动作。它的嘴里衔着一个全新的镀金的桶(我甚至像看到红底蓝字的纸质商标还在前头粘着)。它正要送一桶空气给其他的鱼儿——因而才凑巧碰见我。我往桶里一看——里面有了空气,还有色彩。毕晓普正是那个呼唤者。诗中描写的事物寻常之至,使一首诗截然不同的是诗人表达的方式、观察的角度、思考的深度以及语言是否像叶子一般自然地生长出来。
毕晓普用那双奇思异想的画家的眼睛去观察,这带给她无穷的乐趣。她遵循的是一种诗人的逻辑和感觉,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审视日常事物,从而使它们获得一种全新的生命力,既将这种最奇特的感觉传达了出去,同时又显得庄严、平静、温柔,如同她在《麋鹿》一诗中出现的那只如奇迹降临的麋鹿。
奇迹,是为相信奇迹的人而降临的。对毕晓普来说,一首诗首先应该具备的便是惊奇。题材和用来表达的语言都应该让诗人自己觉得惊奇。当你觉得惊奇,便是因为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奇妙的活生生的东西。
二、专注的矶鹬
精妙,毕晓普依靠的是一种“物对物观察”的冷静的距离感,她的眼光总是“比历史学家的还要精妙”。一生漂泊的毕晓普的创作,就是为这个可能的世界绘制地图,以其深情的关注,观察一件物事,直至它的内在的核层层显露。在不动声色的描绘中,能察觉她敏感的智慧和深厚的激情。她总是对周遭的世界保持着最新鲜的好奇。这种好奇,可以是一只麋鹿,可以是一只犰狳,甚至一个加油站,她从中看到一些奇妙的活生生的东西,并对之充满了兴趣和敬意。她享受观察,在那些平凡的事物里看到了整个世界,在一只麋鹿的气味里她触摸到永恒的回忆。
不管是奇特还是庸常的事物,毕晓普总能用最不寻常的语言表达出来。希尼对此曾说:“毕晓普有那种能将事实提升为一种崭新的修辞效果的古老天才。”在《麋鹿》这首诗里,毕晓普讲述了一路上发生的事情,那仿佛是一次谁都曾经历过的旅途,除了最后那只神秘降临的麋鹿。她用浅白简洁的文字去书写复杂或神秘,这是一种艺术的自律,这也是毕晓普让人着迷的地方,让感情涌动在冰山下,只把那八分之一显现。
毕晓普的诗大多都是沉静的,她从气质和理智上都倾向于离群索居,在文坛上并不活跃,写诗的风格也和当时的流行相去甚远。诗作的数量极少,并且长期旅居国外,与各种诗歌流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毕晓普在写给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诗中曾说,她向来幻想可以当一个看守灯塔的人。毕晓普所想象的看守灯塔的人可不是“整天坐在那儿,除了擦灯、修剪灯芯、在一丁点儿大的园子里耙耙弄弄之外”别无他事的人,她期待一种彻底的孤独。在海上的灯塔里,没有人去打扰她的阅读或者静思。
无论孤独与否,她始终力图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用客观冷静的调子来审视周围的世界。这种平静、不露声色的叙述风格并非为了使读者震惊,而是如同布莱克(WilliamBlake)诗中所写的,她自有这样一双眼睛:“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梁宗岱译)她在这些寻常事物中看见了永恒。在致梅·史文森(May Swenson)的信中,毕晓普说道:“我自认为我最好的诗歌是那些看起来非常客观的诗,有时我希望我对其他事物都能如此客观,一旦我试图非常个人化时,就不那么成功……”
当然,很多时候她是成功的,虽然有些人批评她“诗里一点也没有哲学”,“只不过是一个擅长描写的诗人”,“像鳗鱼一样冰冷,有些甚至让人读之却步”……对于这些批评她从不辩驳,只是在一次访谈里说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对你而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毕晓普拒绝把生活理论化、格式化,她的诗纯粹,有着自身的韵律。正如洛威尔所说,她是“一个使庸常事物变得美好的完美的缪斯”。
毕晓普的诗歌通常开始于观察,一种生物,一处风景或者其他细小的切入点,于她都会有独到的发现,她用一种沉默的笔触获得了自然这把“可变的钥匙”。她的观察,似乎能将聚焦到事物的灵魂之内。就像史蒂文斯的一首诗的名字:《不是关于事物的理念而是事物本身》,她关注的就是摆放在面前的“物”。她将人与物的眷恋在细微之处表现出来,让人得以欣赏在平常的事物中被忽略的美。如《在渔房》中描写老渔夫:
他的汗衫和拇指上有一些小亮片。
他刮掉无数的鱼鳞,最美丽的部分,
用一把又黑又旧的刀子,
刀刃几乎磨钝。
诗人詹姆斯·梅利尔(James Merrill)曾如此评论毕晓普:“描写与叙述同时并行的方法,很明显的,让毕晓普在诗人中别树一帜:其他诗人认为微不足道或与主题不相干的细节,她能一一娓娓道来。透过她的诗行,读者不只沉湎在所描绘的景致中,也分享了她的心路历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故事,一小段历史。”
进入事物,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写道:“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它所隐藏于其中的对象——或称之为感觉,因为对象是通过感觉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很可能不再与之相遇。因此,我们一生中有许多时间可能就此永远不复再现。因为,这样的对象是如此微不足道,在世界上又不知它在何处,它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路上,机会又是那样难得一见!”
三、沉默的麋鹿
毕晓普的诗作如水般清新澄澈,却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那些文字看似随手拈来,其实多数费时多年,连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也《随笔》中特地写了一首诗:“你是否仍将诗句挂在空中,十年也不完美。”
对毕晓普来说,灵感如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说是“每日练习的酬劳”,比如她的《麋鹿》一诗便历时十六年。对毕晓普来说,一首诗从在脑海里诞生直至下笔,可以从十分钟或者长达四十年。她曾说过,她所拥有的少数值得称许的美德,便是耐心,无止尽的耐心。
在《追忆玛丽安·摩尔》文中她自述:“只有写得更好,更用心,不在乎别人怎么想,除非自己已经竭尽所能,否则不尝试发表,不管费时多少年——甚至永不发表。”
毕晓普写得慢而且克制,她的全集中诗歌也不过一百多首。对一首诗,它或许很久之前已在自我的世界里生根、默默潜藏,要有足够的耐心慢慢等待它们显露。生命中曾经发生的某一件事,比如亲人的离去,也许要等到又一场同样的大雪漫天落下来,潜伏的疼痛感才会以沉重的声音把人淹没。那种沉默是如此凝重,仿佛拥有了某种生命的质感,像是一幅油画,每个厚重的色块在那里闪烁着光芒,散发出直抵骨头的釉光。
含蓄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这是毕晓普诗中的启示。希尼曾在《舌头的管辖》中称赞她是最缄默和文雅的诗人,说她通常把自己局限于一种调子,而不会去干扰陌生人在一座海滨酒店用早餐时那种谨慎的低声谈话。有这么一则小故事,一位爱斯基摩老妇人唱着短小的歌谣,当人们问起她,为何部落中的歌谣都如此短小时,她简单地回答:“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毕晓普身上便有这样一种动人的沉默。
毕晓普的童年布满阴霾。在她十个月大的时候,身患阵发性抑郁症的父亲病逝,母亲开始屡屡因精神崩溃而住在精神病院中。毕晓普从小辗转流离于外婆与祖父母处。毕晓普一生在痛苦中不断挣扎,却坚决反对夸张、虚饰和过分的情感宣泄,她认为观察和精确是最难的。作品节制,对于童年的不幸,她曾在给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的信中坦言:“尽管我拥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哀伤得几乎可以收进教科书,但不要以为我沉溺其中。”
回忆是毕晓普诗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她的《六节诗》《麋鹿》《水澳》以及《在渔房》等都是和家乡的人与事有相关。《在渔房》中与老人的对话更是让人心里像蒙上一层暮色的忧伤。这种淡然的忧伤也浮现在《麋鹿》中,诗人在半睡半醒中梦见童年时的外祖父母,他们说着村里发生的种种不幸与悲伤:
死亡,死亡和疾病;
那一年他再婚;
那一年(有些事)发生了。
她死于分娩。
那一年失去了儿子
当纵帆船沉没时。
那些不幸似乎预示着她的一生都将在孤独和被放逐的生命中度过。而在诗中最后外祖父母对那些提及的苦难,却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是啊,生活就像那样。我们知道的(还有死亡)”,似乎生命旅途中一切的意外都可以当做有惊无险的插曲默然接受,意外的遭遇甚至因此化作邂逅永恒的契机。
毕晓普诗歌中的美,不是精巧,也不是痛苦与自白,而是像惊鸿一瞥的飞鸟,潺潺的流水,或者暗夜里草丛中的萤火虫那样蓦然显现,却给人无尽的回味,那种余味就像看着一直风筝在天空上悠悠地飘荡着。
在毕晓普给玛丽安·摩尔的信中,曾经描述在沙滩上放风筝的场景。她说清晨时会有海鸥飞到风筝上方,好奇地看着,有时在夜晚,那些红胸脯的家燕还试图停栖在风筝线上。毕晓普还说,那种从大海上空往下张望的感觉,肯定很奇妙。
[1]Bishop,Elizabeth,One Art letters.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94.
[2]Bishop,Elizabeth,The Complete Poems,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3.
[3]Camille Roman,Elizabeth Bishop's World War II-Cold War View,Palgrave Macmillan,2001.
[4]Lloyd Schwartz,Elizabeth Bishop and Her Art,New York:The UniversityofMichigan Press,1983.
[5]Miller,Brett C.Elizabeth Bishop:Life and the Memory of It.Berkeley:UofCalifornia P,1993.
[6]Bishop,Elizabeth,Elizabeth Bishop Poems,Prose and Letters,NewYork:LibraryofAmerica,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