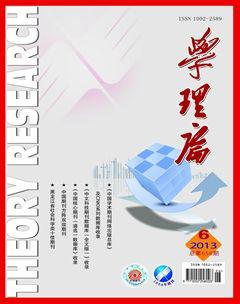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人的价值观演变
李娜
摘 要: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人的发展问题不可回避,而价值观作为人的思想观念中的一个方面,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实践证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人的价值观转变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观;演变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89-02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即客体的性质特征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正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效用的看法、观点。在人的发展历程中,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过程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变革和转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深入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受此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也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那么,转型时期人的价值观到底发生哪些变化?归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一、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演变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有着深厚的权力意志支撑着。国家动荡不安、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和文化落后,人的个性受到严重束缚。因此,人们价值观念主要是追求统一与稳定、道德与伦理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划归到一个标准上来,这就使人的交往范围受到很大局限,丧失了表达自己内心意愿和思想自由的权利。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转型已经开始,社会发展开始趋向正常化、多样化,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也向多元化趋势迈进。
现在,我国经济上正经历着从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社会转变,政治上开始由国家政治集权向建立在人的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社会转变,人的发展方面开始由“以物的依赖型社会”向以“人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经历着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人的价值观的转变是最主要的,它影响着人们的追求和趋向,决定着人的发展历史进程。正是基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些转型和变化,人们对于自身需要和利益的追求使得价值观念多元化、多样化,已经由国家垄断、市场消极调节的国家本位思想转变为商品自由流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念,由传统的中国核心文化价值体系转变为融合、包容性吸收外来文化中国的优秀成分,由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传统思想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主义、权力主义已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人民本位”或“人民主体化”。“当然,在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中,并不否定主导价值取向的存在,即以一种价值取向为主导,以其他价值取向为补充。因此,多样化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统领的。不能离开主导价值取向而单纯地主张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也不能以强调主导价值取向为由,否定多样化价值取向的现实,继续坚持单一化价值取向。”[1]
二、从注重集体利益到尊重人的个性演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前,人们是把集体主义作为价值主体的,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或者国家利益,人的自由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国家利益,“一大二公”的观念十分盛行,人们从事生产、教育、文化、艺术等活动都以集体或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这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本位——轻个体重整体”思想所影响,人们的地位自始至终得不到有效改善,严重忽视了人的个性自由和个性张扬。客观来讲这是违背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如果说整体利益是共性、一般性,那么人作为最主要的社会力量就是“细胞”、“微动力”。因此,从社会发展历程看来,一味地强调整体,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是不能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
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已经蓬勃发展,现代西方文化已深入到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和长期以来的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整体主义受到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的冲击。表现在价值观上,开始由集体转向个体,注重个人的发展,重视人的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的尊严;开始全方位地创造条件,使人的需要和追求不断得到满足,不断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但是,这种思想的转变容易产生消极作用。社会转型是社会的大变革和大转变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也表现出无目的性、盲目性,极易受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例如现阶段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社会道德观念缺乏核心主导等等,都集中反映了西方价值观传入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重视个体价值将会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方面产生倾斜,不惜一切代价满足个人而损害集体和国家利益。这就需要以正确的价值思想和核心理念予以引导,引导人们在坚持整体利益的同时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从传统的重义轻利到义和利相互并重的演变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主体经济上表现为重农抑商,因此,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即为重义轻利,义与利的问题就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些传统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合理,符合中国人的价值习惯和文化观念,它重视人的思想世界,崇尚人与社会的道德理想,对于抵制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物质利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体系的不断确立,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逐渐表现出很严重的缺陷。它将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不道德”、“不正统”、没有人生追求。事实上,这是带有典型的“左”的义利观色彩。相比较而言,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逐渐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价值取向提倡人们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财富,不断满足自身生活所需,不断实现自身价值,政治上要求民主、平等和自由,经济上要求实现个人私有财产合法化等等。这种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走向极端就变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新时期新阶段,面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大转变,中西价值观念之间必然相互撞击与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不可能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为这是促进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也要求人们重视社会道义和集体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人们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下追求自身价值,不断满足自身物质文化需要,又要求人们以大局为重,以社会、国家和人民总体利益为先决条件;既不能过分采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也不能忽视重利轻义的西方价值理念;既要重视人的自身个性张扬,又要尊重社会道德公义,将义与利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使义与利的现代价值观更加合理,更加科学,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繁荣复兴的目标价值所在。
四、从因循守旧的消极观念到开放进取的价值观演变
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都显得极其微小,因循守旧就取自传统文化中的不求上进、自给自足、故步自封的价值观念。
《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永不放弃追求、不懈努力、不懈奋斗的思想品格,并且一直激励着中国人不断前进,不断奋发向上。这与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反差很大。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封建的血缘家族制。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本位是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的体制,它限制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限制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以保全家族地位。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之间只能延续,只能遵从前人的经验与意愿,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能违背老祖宗意愿。这种思想根源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因循守旧的价值观,可见,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号召之下,人们在破除迷信,取缔传统消极思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这只能是祛除因循守旧的思想。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思想价值,采用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就需要探索,那么这就需要革故鼎新,就需要人的价值观开始由一元变为多元。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进入使得中国人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于新事物和新观念的理解也变得多样化,现代科技和经济的不断进步又使得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愈来愈深入,人们在各个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方式,中国已经步入开放国家的行列,人们的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任何一种思想的束缚,而是跟随者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更新观念,人们的价值体系也不断完善和进步。
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是思想观念的不断革故鼎新和不断进取。现代化的中国人正在扬弃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包容和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西方价值思想,正在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以自身合理的价值理念影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以自身优秀的价值成果推动世界和谐,实现世界大同。
参考文献:
[1]张友谊.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嬗变[J].岭南学刊,2006,(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