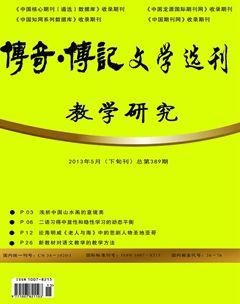浅析春柳社对话剧艺术性的追求
张欣杰
【摘 要】春柳社作为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始终都有着对话剧艺术性的坚持。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春柳社话剧活动的三个阶段,然后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春柳社追求话剧的艺术性,分别是严格的剧本制、十分注重表演艺术以及多悲剧而少喜剧。春柳社在鱼目混杂的文明新戏中坚持了对话剧艺术性的追求,只是在最终难以维持时先堕落后解散,但是其追求艺术性的脚步是难以磨灭的。
【关键词】春柳社 剧本 表演艺术 悲剧
在中国文艺的殿堂中,无论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音乐、美术、舞蹈,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话剧这门综合艺术相对来说则年幼的多,它从西方传到中国仅有一百年的时间。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话剧是李叔同和曾孝谷创办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春柳社是个综合性的艺术团体,设有诗文、绘画、音乐、演艺等部门,而以话剧为其主要活动,它对中国话剧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春柳社于1906年由曾孝谷、李叔同等在东京发起,主要成员是留日学生(欧阳予倩在观看了《茶花女》之后加入该社)。他们受到日本兴盛“新派剧”的感召,得到了日本著名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等人的指导和帮助,再加上其成员对这种能够逼真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型戏剧艺术的真诚热爱,使得其话剧创作和表演从一开始就严谨认真而充满激情。春柳社从兴起到结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东京的活动:春柳社在东京共举行了五次演出,有《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热血》、《鸣不平》、《生相怜》、《画家及其妹》,其中以《黑奴吁天录》和《热血》最为成功。《热血》由于涉及到革命问题,给革命青年带来了很大鼓舞,所以受到清廷驻日使馆停止官费留学的威胁,春柳社在东京的活动因此沉寂了下来。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轰动给国内的戏剧改革带来了很大影响,使得原来国内只是在传统戏曲的框架、程序和表演模式上运用模拟现实的方法来表现现实生活的戏剧改革发生了极大改观,许多新的话剧社纷纷成立,如春阳社、进化团等。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胜利后,春柳同仁回国,由陆镜若领导的以新剧同志会的名义在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杭州、湖南、汉口等南方各地演出,很受群众欢迎;1913年秋,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支持春柳社的许多同仁被杀,春柳同仁被迫解散,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活动。这一阶段新剧同志会也积累了不少剧目,如《家庭恩怨记》、《猛回头》、《社会钟》等。第三阶段:春柳同仁回到上海,在陆镜若、欧阳予倩等的组织下创办了职业性的春柳剧场,并保持其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话剧艺术,得到观众的认可,然而由于保留剧目有限,仓促创造的新剧又相对粗糙,无法应对每日演出,其他剧社为赢得卖座率而满足小市民低劣的喜好,故意在演出中制造噱头,春柳社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进行效仿,但还是难以支持下去。这个中国最早的剧社最终以1915年9月陆镜若的去世而告终。
话剧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种类来说,经过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创作、出演,可以相对获得较大的社会反响,又在一定程度上有艺术的纯粹性要求,可操作性很强,更能实现青年学生关注现实、追求艺术理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并得到社会承认的愿望。二十世纪初,中国由于自身的落后和列强的欺压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屈辱年代,激情澎湃的觉醒青年更容易感觉到人生的幻灭和迷茫,春柳社于1906年在留日学生中成立,是不难理解的。欧阳予倩先生说“虽然春柳同仁从日本回国后成立新剧同志会,到处跑码头,以各种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名义演出,但是春柳的宗旨和作风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在上海的时候还挂出春柳剧场的招牌,并引以为豪。 “在这里最明显的“宗旨和作风”就是对话剧艺术忠诚严谨的态度和作风。春柳社从日本新派剧发展而来,但没有完全拘泥于新派戏。新派戏中穿插了很多中长篇即兴的政治演说,而春柳社则发挥了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长,穿插了很多他们擅长的舞蹈和乐器演奏表演等。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几乎贯穿了春柳社话剧活动的始终,只是在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放弃艺术性。笔者将从下面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春柳社对话剧艺术的追求:
一 严格的剧本制
在话剧初创期,几乎所有国内成立的剧社还在沿用京戏和地方戏等旧戏曲的排戏方法,只靠一张提纲(即幕表)就把情节编排一下,分场分角色,有时注上按照情节非说不可的台词,再详细一点的就是写上演员上下场的次序。排戏时把大家聚拢到一起来分配好角色,说一说故事情节和上下场次序,编导的责任就都尽了,演出几乎全靠演员的即兴发挥。幕表戏的好处则是可以迅速的反映现实,如进化团早期为及时配合时政进行宣传而演出的剧目,都是临时写幕表的。在演出时还有一位“言论派老生”专门发表政论演说,扮演者应时宜地临时编制台词进行革命宣传。靠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演出不错的戏,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大多数剧社为了盈利而使用幕表不断推出新戏,很容易使戏剧沦为插科打诨之类的下流笑料。事实上,当时上海的连台新戏多半是靠离奇的情节、噱头和机关布景卖钱,戏的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有艺术价值、是否能发挥演员的长处,从来就不。而春柳社从一开始就严格的遵守剧本制。从他们正式公演的第一个戏《黑奴吁天录》开始,就有完整的剧本,“这个戏有完整的剧本,对话都是固定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才上演”。剧本也没有完全依照小说,从头到尾没有涉及原著中的宗教思想,结尾也把原书中的解放黑奴改为黑奴杀死几个奴贩逃走了,更适合中国人喜爱以战斗的胜利而告终的心理。剧中还有许多唱歌、跳舞等穿插,虽然不尽合理,但体现了中国最初剧本作者的主动创造精神。以后,春柳社在各个时期也都是自己创作剧本,如陆镜若创作或编译的《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猛回头》,马绛士改编的《不如归》,欧阳予倩创作的《泼妇》、《回家以后》等。在话剧初创时期,这些剧本难免有其幼稚之处,但却显示了先驱者对待话剧艺术严肃认真的独立创造精神。在上海时期虽然十分艰难,但翻译剧和自己新编的剧都有。春柳戏有剧本是人人都知道的,有剧本台词不致散漫,动作也有规矩。所以,众所周知春柳戏整齐、认真、严谨艺术性高,来看的很多都是回头客。可是到了后期,春柳剧场的保留剧目有限,编写剧本和排演的速度不可能满足观众每天观看新剧目的要求,眼看着剧场经营一天不如一天,卖座十分惨淡。为了维持剧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使用“幕表”编戏,演剧从此越来越粗糙,春柳也慢慢垮掉了。
二 十分注重表演艺术
话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成功与否的很大因素不仅仅在于思想性方面,还在于能否给人艺术审美的感受,能否吸引观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的表演是否精彩。所以它不仅要求剧本杰出,而且对演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中国古典戏曲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见精湛的表演技能对演员的重要性。而话剧艺术刚刚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大多数剧社不注重演员在表演技能上的提高和完善,而更注重在舞台上插科打诨,甚至以出丑来引起观众发笑。有社会责任感的剧社,如进化团在前期虽上演了许多反抗暴政宣传革命的剧目,但是因为过分注重话剧的政治效应,对话剧的表演艺术也没有足够重视。为了及时配合革命宣传而匆匆忙忙写了一张幕表,根本来不及排戏,演员根据各自性格的不同总是分别扮演同一类型的角色,也形成了固定的表演模式。这样的戏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并不是严谨创作话剧的正确方法。春柳社同仁大多是真诚的热爱演剧事业,并有一定的艺术根底,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表演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分别拜求过专门的戏剧艺术家为师,如欧阳予倩、马绛士等曾向日本著名戏剧家学习过;陆镜若则师承藤泽浅二郎,并与松井须磨子等著名演员一起切磋琢磨表演艺术。陆镜若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还一度被春柳社拒之门外,经过刻苦练成普通话后才许入社。欧阳予倩经常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练哭练笑,一练就是半天。李叔同,“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供自己研究……”这些早期话剧艺术家对表演艺术的追求达到了近乎痴迷的境界,所以才有了在台上的精彩表演。欧阳予倩回忆自己在《热血》中扮演杜斯卡的情景(杜斯卡看到自己的未婚夫露兰画了美丽的伯爵夫人的速写),“对着那张速写,我的呼吸短促,胸口起伏,声音也变了”。曾孝谷在《黑奴吁天记》中扮演黑奴妻意里赛,掌握了哭声的妙绝:“在对话中逐渐增加情感,自然的变成哭声,然后再哭下去,这种地方,每次都博得了极热烈的喝彩”。类似这样细腻精湛的例子还有很多。后期春柳剧场在上海的演出,也以表演的整齐细腻而著称,名誉最好,但是不能满足看客所要求的过分滑稽和意外的惊奇,眼看不能维持生存。在这种“曲高和寡”的情况下不得不步人家的后尘,春柳剧场失去了端庄严肃的面孔,而呈现出解体的现象。
三 多悲剧而少喜剧
众所周知,西方以悲剧为真正的艺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奠定了悲剧的高贵地位。悲剧以高于常人的神或英雄为主人公,他们由于犯了过失而毁灭或牺牲,给我们一种崇高的感情,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喜剧则讽刺低于常人的人,是一种轻松的调剂。好的喜剧作品讽刺人生丑态,如戈里的《钦差大臣》;而悲剧能体现出全人类的命运,唤起观众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如《俄狄浦斯王》。在中国话剧初创期,喜剧的讽刺因素也有,但是大多是插科打诨的逗笑戏,目的是迎合小市民轻松消遣的愿望,提高卖座率。春柳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悲剧而少喜剧,从东京时的《茶花女》、《黑奴吁天记》、《热血》,到新剧同志会时期的《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猛回头》、《运动力》,再到上海春柳剧场时依然保持这个传统,六七个主要的戏全是悲剧,就是后来临时凑的戏当中,也多半是以悲惨的结局终场。《运动力》以湖南省议会竞选议员为背景,揭露革命新贵们的腐败状况;《社会钟》的结尾是哥哥杀死妹妹;《猛回头》的结尾是妹妹杀死哥哥。其实春柳社以悲惨的结局结尾,或者在剧中穿插很多悲惨情节的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而只是相对其它剧社卖噱头挣钱的闹剧来说,比较严肃地反映了许多现实问题而已。剧作者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想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想让观众看过戏之后或对社会认识的更清楚,或对人生有所感悟,这种初衷造成了剧中多悲惨的故事情节。剧本中仍有许多粗糙幼稚的成分,但作者对待话剧虔诚的态度本身就是可敬的。春柳的演员不大会演不严肃的喜剧,喜剧在春柳剧场只能算是临时凑数的。而中国观众对悲剧很不习惯,一般观众都愿看过戏后轻松愉快,而不愿带着沉重的心情出戏院。春柳最终难以为继也是因为看悲剧的人越来越少,而增加喜剧的分量之后又不如其他剧社更会制造笑料,鹿不为鹿马不为马,最终走向破裂。
理想和吃饭问题的对峙,以及诸多的社会原因使得春柳剧场解散,但是春柳同仁对话剧艺术的理想永远也不会消失。春柳剧场有次演出《茶花女》时天下大雨,场内只坐着三位观众,他们本想给观众退票,但观众说有心看戏的就是知己,为知己演戏不在观看的人有多少。他们听到这话热血沸腾,到后台认认真真的化妆换衣,比平时演出更加卖力,可见他们对艺术的态度真是达到了忘我的程度。眼看剧社难以坚持下去,许多演员纷纷离开春柳,而领导者陆镜若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却还要同欧阳予倩等少数成员继续坚持下去,最终活活劳累而死,春柳终于崩溃了。春柳社在动荡的历史时期艰难的维持了近九年之久,虽然有得有失,但是其在剧本、表演等方面对话剧艺术性的坚持,为中国话剧带来了良好的开端,后来的许多优秀话剧都是从春柳社话剧中吸收营养的。
参考文献
[1]柏彬.中国话剧史稿[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2]黄会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3]回忆春柳.欧阳予倩论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4]谈幕表戏.欧阳予倩论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5]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
[6]陈丁沙.欧阳予倩艺术生平,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第一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7]陈丁沙.春柳社史记,中国话剧史料集(第一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8]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1)
[9]欧阳予倩.欧阳予倩代表作[M].葛聪敏编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0]欧阳予倩.欧阳予倩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