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塞得进房子吗?
2013-08-06 09:23小康谈乐炎
小康 2013年10期
《小康》记者 谈乐炎
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儿时读这句诗时我有点不明白——当年艾青为何在智利的海岬上,给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一句中国式绕口令。
地球塞得进房子吗?
如果不能,诗人为何写的如此笃定?这种质疑有矫情之嫌。
我想这不仅仅是个文字游戏。
再次看到这句诗,是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本书里——当原国民党将领文强再次推开文史专员办公室时,他已经步入耄耋之年,阳光与尘土交融那一刻,文强读懂了老朋友艾青。
战俘,这是文强毕生的标签,正如《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作者黄济人接受我采访的开场白:“我是战败者后裔。”
很长时间里,国民党战俘这个群体被人唾弃和遗忘,而这种遗忘,正是很多战败者所期望,倔强如牛、至死交错不交罪的黄维面对黄济人的采访要求,始终牙关紧闭:“你要撕开我们这些战败者的伤疤,我不能接受。”
这个一个复杂的群体,尽管他们已经与“胜利者”冰释前嫌,从此新生,然而“战败者”这个角色深根于他们内心,挥之不去。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文强最喜欢别人对他这样一句评语:“秋水文章,性灵普通,一个善良的老人。”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世纪老人”,这和战争无关。而曾经的“特务头子”沈醉,在上半生就已经“机关算尽”,下半生他将所有气力都花在儿女情长里。当然那位固执的黄维老先生,余生仍旧痴迷与“永动机”发明,我想他在做这件事情时一定没有纠缠于“失败者”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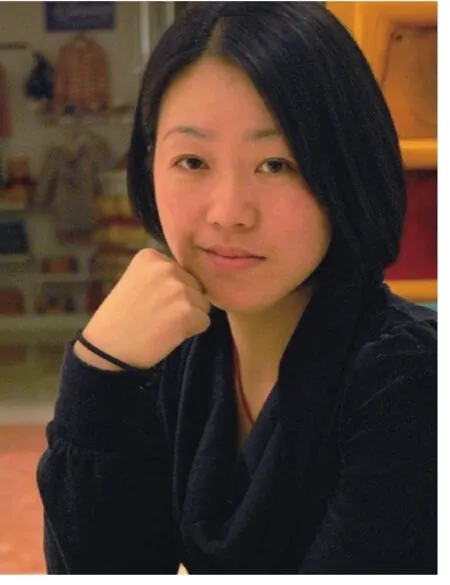
或许他们心里最终明白,自己只是一棵棋子而已,一部历史大戏里的无名之角。
唯有历史这个地球,深深住在你我心房。
你是胜利归来的人
还是战败了逃亡的人
都不是,都不是。
——艾青《在智利的海岬上》
猜你喜欢
金桥(2021年6期)2021-07-23
科学大观园(2020年4期)2020-03-30
爱你·健康读本(2019年3期)2019-06-11
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18年4期)2018-06-21
唐山文学(2016年11期)2016-03-20
共产党员(辽宁)(2010年15期)2010-09-20
军事历史(2002年2期)2002-08-21
军事历史(2001年6期)2001-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