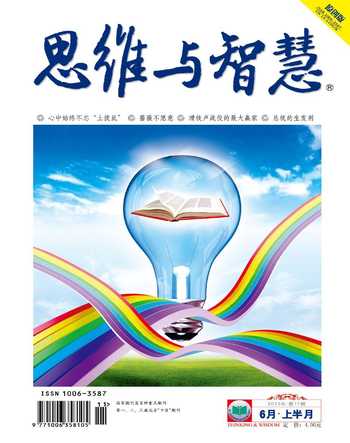麦田里的生日
马亚伟
南风起,小麦泛黄,我的生日也到了。父亲早早把镰刀收拾出来,磨刀霍霍。镰刀的刀锋在我眼前一晃,雪亮亮地刺眼。我的生日,已经被父亲忘得一干二净。我扯了扯母亲的衣角,等着母亲提一下。母亲小声地嘟囔了一句,父亲也像没听见一样。在他看来,生日没什么大不了的,和土地长庄稼一样自然,过生日实在是多此一举。
父亲起的很早,我在睡梦中听到他收拾农具的声音,“叮叮当当”响过一阵后,我被揪出被窝。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不情愿地穿好衣服,跟着父母下地割麦。
火辣辣的太阳瞬间就把麦子上的晨露蒸发干了。父亲拿出镰刀,小心地用食指蹭一下刀锋。然后,父亲弯腰割麦,麦子在父亲手中服服帖帖倒下。我的镰刀要小一些,是父亲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弓下身子,我还不能像父亲一样,一镰刀下去,“唰”的一声,麦子乖巧地应声倒下,躺倒一大片。我是笨拙的,小心地一把一把割着,把割下的麦子放在小小的臂弯间。
我开始感到累,不停看地头,那么漫长,仿佛这辈子都到不了头。有蝴蝶蜻蜓飞过,我想去追。或者,就地躺倒在松软软的麦子上,看蓝天白云。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我低着头,汗水,雨一样纷飞。我不敢停下来,父亲把我甩在后面,我要追着他的脚印一步一移。
金黄的麦田,油画一样安静。只有一家人割麦的“唰唰”声,不同节奏,此起彼伏。我的生日,淹没在这无边的麦田里,淹没在这不间断的“唰唰”声里。
突然,父亲喊我的名字,我一惊,难道是父亲想起了什么?原来,父亲是让我回家拿一块“磨石”,他的镰刀割倒了大片大片的麦子,钝了。我在路上不敢耽搁,小跑着回家。
谁能想到,我到家,竟然鬼使神差地睡着了。人累的时候,连梦都没有。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背后上重重挨了一巴掌,我一个激灵跳起来。我不知道是惊恐,还是委屈,呆望着父亲,咬着嘴唇,使劲忍住眼泪,一言不发。父亲怒目圆睁,吼声如雷:“让你回来拿东西,活还没干完,跑回来睡起了大觉!”又一巴掌,落到背上。我委屈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我的生日,像一只逃窜的小兽,急匆匆,惶惶然。我的童年,从此笼罩在父亲的严酷中。我的生日,再也没有被提及。
岁月倥偬,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与父亲的隔膜,都被时光冲淡。父亲老了,脾气也温和了许多。我结婚的时候,借钱在城里买了房子。父亲把我叫回家,抖抖地递给我一个6万元的存折——这是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父亲挥洒在土地里的汗水都凝在里面,沉甸甸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很久以来,父亲把爱深埋起来,以忽略和冷漠的方式呈现。父亲吃苦耐劳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孩子留下点财产。他认为这是无比重要的责任,所以,人一意孤行地删繁就简,直奔自己的目的。想到这里,忽然觉得,父爱像一盏黑暗隧道里陡然亮起来的灯,让人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其实,父亲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儿女。这种爱,忽略了过程,忽略了表达,直接把他认为最正确的结果给了出来。
(编辑 一昕)
-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心中始终不忘“土拨鼠”
- 后得与厚德
- 位置
- 强悍的心灵
- 半
- 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着一个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