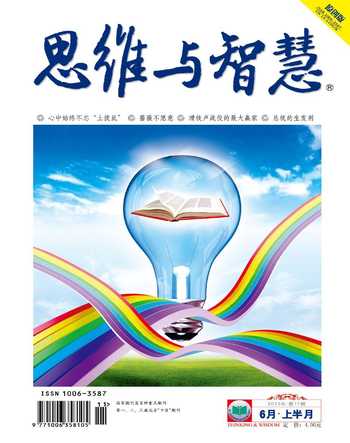蔷薇不愿意
凉月满天
“佩带花环的阿波罗,向亚伯拉罕的聋耳边吟唱,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着蔷薇。”
好诗。
可是一只猛虎嗅蔷薇,你晓得人家蔷薇乐意不乐意。
好比我们赏花,撅着屁股,凑得近近的,鼻子都要杵进花心里了,眼睫毛都要把娇嫩的花瓣扎出一排洞眼。
又或者伸出柔荑,轻轻掐下一朵花来——
对人来说,这叫风雅。
对花来说,这是个什么玩意!这么怪,大脚板把地板跺得咚咚响,吓破了偶们的小心脏;鼻子长得像白毛象,还伸进来乱嗅乱拱,鼻毛都能数得清,呕——
眼睛上还长一排铁刷子,喂,别凑这么近!
啊!一朵好姐妹被这只怪物用长满体毛的爪子把脖子拧断啦,把尸体还给戴到它自己的头上,呜哇哇——
瞧。
我们眼里的蚂蚁,多么微乎其微,对于一朵花也是一只扛着大铡刀的恶狼,它们钻进它的花芯,噬咬它的花瓣,或者不顾它是疼还是痒,径自排着队浩浩荡荡爬过它的身体。它也不能动,所以只能既恐惧又恶心。
一头猛虎细嗅蔷薇,从老虎的角度,也许它的心里有朦朦胧胧的一点什么感觉,但是不耐细追寻,一追寻就消失了;从人的角度,这是诗意的,值得赞叹和铭记,带着禅味。而从一朵蔷薇的角度呢?这家伙那么大的嘴巴,会不会吃了它?这家伙整天吃肉,口气好臭,要熏得它背过气去。我们眼中所见的无比违和又无比和谐的一幕,宇宙间漂亮的一景,如果从蔷薇的眼中看出去,是可怕的灭顶之灾。
还有,你知道一棵树拔出来,再重新栽回土里去,为什么会叶片发蔫,好长时间恢复不了元气?
不是因为损伤了根脉。据说,把树从土里拔出来,露出根,那是和人类的被剥光了衣服裸奔一个等级的行为,把你扒得光溜溜的,让人看个饱,然后再给你解开,穿上衣裳,让你继续生活,不羞死才怪。
当然,当春风拂面,百花挤挤挨挨,香气萦绕,天顶一片湛蓝,太阳发着金光,或是细雨淅沥而下,这些花啊树啊是多么地惬意。好像一切都围着它起舞,一切都为它谋篇布局,阳光是为它照耀,青草是为它生长,蜂蝶是为它营营绕绕,流水潺潺,其实是为它奏响的爱的鸣琴……
对一朵花来说,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它发生,我们是它生命中的恶棍,它的生命中还有那么多、那么多专为它存在的喜悦。它才是世界的中心。
每朵花都是世界的中心。
每只猫、每只狗、每只蚊、每只蝇。
一块石头也是世界的中心。
谁说石头没有生命的?你问问量子物理学家,它在和它的周围的环境,质换着怎样的粒子,而它的内里,是又有着多么活跃的粒子的运动。对于它来说,即使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举动也像是在快放电影,就那样滑稽地飞速地前进、倒退、说话,嘴巴动起来快得无与伦比,一切都滑稽得不行。而它们睡一觉醒来,我们早已经成了灰尘。
我们就算站在它的旁边,一动不动几十年、上百年,对于它们来说,也不过就是我们的身边,有一只蚂蚁偶尔停留了片刻。至于片刻之后,蚂蚁是生是死,我们不关心,而我们的生与死,石头也不会关心。
所以,你的眼里看出去的,不是世界的中心,那只不过是你的世界。我们看一个疯子傻呵呵地满街乱跑,可是对于这个快乐的疯子来说,我们才是表情木然、心思呆滞的疯子。
我们不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也不认识自己。
当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慈禧西逃,随身两个丫头一边吃苦受罪伏侍主子,一边说闲话,说到当初看戏看到的陈圆圆的故事,城破被俘,六宫的人被赶着迎接新主子,“九殿咚咚鸣战鼓,万朵花迎一只虎”。
老虎是开心了,那一万朵花开不开心?
当然这话跟老虎说不通,因为老虎不识字,人形的老虎也是莽夫、粗汉。可是我们识字。所以我们不要搞这种让花恶心的事。
当你想要亵玩一朵花的时候,也要先想想它开心不开心。
所以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地去歌咏一头猛虎细嗅蔷薇,因为蔷薇不愿意。
(编辑 慕容吟)
-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心中始终不忘“土拨鼠”
- 后得与厚德
- 位置
- 强悍的心灵
- 半
- 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着一个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