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作家风云录
文/马信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反映上海工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由小说、诗歌开始,后发展到电影、戏剧,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颇有才华的工人作家。在这风云际会中,工人作家这个群体的崛起和辉煌,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瞩目的一页。这个曾影响全国的海上文坛“黄金期”的产生,显然与上海这座特有的大工业城市有关,更是党在这个时期推行的新文艺政策的结果。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对于一个城市的传统和文脉得以传承,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应该仍有意义。
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陆俊超等工人作家,是当时活跃在海上文坛的耀眼明星,也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其中最有成就的胡万春因病已经过早地离世,而费礼文、唐克新、陆俊超等也已是逾八十的老人。当记者日前找到他们,回首往事,说起这段已经逝去的岁月,老人们依然怀有激动和眷恋之情。
难忘工人创作进入的黄金期
让我们的视野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上海工人文学创作曾经的火红年代。
新中国诞生后,一批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拿起笔杆,用自己喜爱的文学体裁记录、描绘、探索上海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这一派文学是上海当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最具上海城市特点的文学之一。
1952年,上海第二钢铁厂工人胡万春的第一篇小说《修好轧钢车》在《文汇报》副刊上发表,接着他又写出了其自传体小说《骨肉》和小说《青春》。
1953年,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费礼文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兄弟俩》,在同年5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接着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一年》《两个技术员》。
与此同时,上海第六棉纺织厂工人唐克新将小说处女作《车间里的春天》寄给了《解放日报》,几乎没有修改就刊登出来。不久,他又发表了近3万字的小说《古小菊和她的姐妹》。
稍晚起步的海员陆俊超,将他的处女作《海洋的主人》投寄给了《萌芽》杂志,小说为中国海洋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当《萌芽》主编哈华审看稿子后,当即决定发表。而后,陆俊超的小说《国际友谊号》和《九级风暴》相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当工人写小说势头正旺时,诗歌这种短小精悍的文学体裁也成为了工人们的最爱。从民歌吟诵到写诗作歌,上海培养工人诗人和推广诗歌活动的两大基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沪东工人文化宫热闹非凡。白天,工人们在炉前炼钢,在车间织布,晚上,他们带着火热的生活感情来到“市宫”和“东宫”尽情抒发。
国棉十九厂工人李根宝的诗《烟囱》就是从这儿传开的:“高高伸向白云边,青烟缕缕绕蓝天。哪棵大树有你高?哪根天竹有你甜?你是一只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你是一支大毛笔,描画祖国好春天。”
上海电话局的仇学宝参加了伊尔18型飞机试飞后,写下《飞翔在上海高空》:“黄浦江是一条镀金玉带,满城的宝石花在闪光,烟囱像晚雾笼罩的森林,新楼像绿色稿笺上的诗行。脚手架像长城连绵不绝,新工业区在发展成长,啊,飞跃前进的城市,啊,万马奔腾的故乡。”
达丰印染厂工人郑成义的诗《布上鲜花朵朵开》在当时广为流传,还被谱成了歌曲,歌词这样写道:“布上鲜花朵朵开,鲜花永远开不败,鲜花本是我们栽,机器一开就春天来。嗨,嗨,嗨!我们的劳动多光彩,多把幸福的花儿栽。”
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人谢其规紧紧抓住劳动的特征写的《翻砂》诗,语言干脆有力,音节琅琅上口:“黑脸、黑袄、黑手翻黑砂,修修、刮刮,墁刀飞上飞下。张师傅把砂比作花,墁刀整枝修芽杈;修出千台汽轮机,明珠挂满荒山洼。”
沪东船厂工人居有松的《火工谣》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劳动场景和高昂的热情:“火工战斗船台下,手上乙炔开蓝花,榔头擂起震天鼓,再硬的钢板也听话。太阳西沉满天霞,火工抬头笑哈哈:我的衣裳汗未干,你倒偷偷溜回家。”
“工人写工人”的文学作品,在上海高潮迭起,为此,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1954年和1955年,先后编选出版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选集》一、二集,收有二十名工人作者写的近五十篇作品。与此同时,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选有很多上海工人作者作品的《工人文艺创作选集》。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这次会议对推动文学创作特别是青年和工人创作起了积极作用。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毛炳甫、樊福庚、郑成义、徐锦珊、金云等8位工人作者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大会。费礼文还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根据会议精神,为加强对青年和工人文学创作的领导、培养和辅导,会后,作协上海分会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建立起专门组织,还创办了以发表工农兵和青年作者作品为主的刊物《萌芽》。从那以后直至六十年代初,上海工人创作进入了“黄金期”,涌现出一批工人作者、作家,写出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品。
其中,进步较大的是胡万春,他被推荐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之后,接连写出《内部问题》《特殊性格的人》等多篇作品,出版了《谁是奇迹的创造者》《红光普照大地》等小说集;费礼文写出了《晨》《不落的太阳》等中短篇,出版了第三本小说集《早春》;唐克新写了《沙桂英》等新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种子》等;海员陆俊超继出版了中短篇小说《九级风暴》后,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幸福的港湾》。
围绕上海工人创作的发展,许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此进行分析和评述,他们既热情肯定其中一些可取之处,也中肯指出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如罗荪写的《上海十年工人创作的光辉成就》,魏金枝写的《上海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巨大收获》,是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文章。同时,北京《文艺报》对上海工人的文学创作也十分重视,据统计,“十七年”期间,共发表专题报道、评论达36次。
新文艺政策让“工人拿起笔”
那么,上海为何能成为全国工人文学创作的重镇?又是什么原因,能涌现出众多的工人作者和文坛明星?与费礼文、唐克新、陆俊超等老作家探研这些问题时,他们一致表示,这不是他们先知先觉或聪明所致,这是上海这个城市赋予了他们的幸福使命,是党在这个时期推行新文艺政策而结出的硕果。
上海是我国特有的大工业基地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自清末李鸿章苦心经营洋务运动以来,在上海这个大本营中,他开设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不仅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也培育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1843年的开埠也使上海较早沐浴西风美雨,促进了上海工业的发达。其中英商和日资开设的纺织厂就奠定了上海纺织业的中心地位,外商投资的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等现代化企业也都提升了上海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据统计,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工人数量迅速增长,1920年工人人数为56.3万人,1939年增加到60万人以上,1949年达到100万人,而仅仅过了两年,即增加到141.38万人。
作为大工业基地,工人生活成为上海人民生活的很大组成部分,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火热的生活本身就为工人题材创作提供了条件,而此时我们特有的文艺政策使得这样的创作如沐春风,如虎添翼。有着庞大的工人队伍,不仅使群众性创作有了雄厚的基础,也为逐渐形成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群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多次在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提出,要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文艺大军。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队伍。”邓小平也说过:“要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建立业余群众文艺的新据点,培养工人农民出身的文学写作者。”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也说:“你们是从工农兵群众中来的,你们又会劳动又会创作,拿起枪来是战士,拿起笔来也是战士。你们既是生产的队伍,打仗的队伍,也是创作的队伍。这么一支队伍,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出现,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贺的大事。”
因此培养工农作家成为当时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而普及性的扫盲运动为此打下了基础。到1965年,全国共扫盲9571.3万人,职工中的文盲基本扫除。由于文化程度的提高,直接刺激了一部分工人群众的创作热情,他们纷纷拿起笔写心中的感受,写身边发生的一点一滴,而此时,我们的报刊杂志、电台中的记者编辑纷纷放下架子,为培养工人作者大开绿灯。其实,中国作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考虑过如何组织和培养工农作者的问题。时任领导的邵荃麟提出的措施就是:先让工农作者在生产单位的小型活动中崭露头角,然后再由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把其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
上海文学组织在培养工人作者的工作中成为重要角色。上海工人创作队伍的培养基本上就是按照中国作协提出的那个思路运作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作者活动场所之一——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文学组织热情浇灌创作之花
胡万春生前曾参加过本刊组织的创作笔会,他多次与记者谈及他的成长史。说到上海工人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他告诉说,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他们的文化基础很低,都只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基本都是从参加学习班,从反映真人真事的小通讯、小故事开始,中间经过文学期刊,或电台,或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培训、辅导,后来才做小说家、诗人或编剧。他深有体会地说,上海工人创作队伍的成长和壮大,离不开上海的工会和文学组织所起的积极作用。
早在1953年,上海市总工会就委托《劳动报》组织工人作者学习班,请作家协会的专家辅导。《解放日报》也办起了工人通讯员学习班,很多作家担任辅导员,其中包括胡风、柯蓝、叶以群、靳以、魏金枝、菡子、王若望、赵自、阿章、唐铁海、茹志鹃等。
《上海文学》的前身《文艺月报》,创刊不久,就开辟了“习作”专栏,主要发表工人作者的文章。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后,为更好地发表工人等群众作者的作品,上海决定办一份青年文学刊物,起名《萌芽》,从第二期起,该刊就开辟“文学青年笔谈会”园地,并首先发表了电话局工人福庚的诗歌创作经验介绍,以及编辑刘金撰写的讲评文章。编辑赵自写了不少诗稿随想,对工人的创作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推动并适应群众文艺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上海对文学刊物作了重要调整,把市一级文艺期刊《萌芽》《群众文艺》及《街头文艺》和《工人习作》合并起来,从1958年9月起改版为《萌芽》半月刊。新《萌芽》除定期发表短小生动的指导性专论、述评和典型经验介绍外,又开辟“文艺笔谈”、“友谊书斋”、“作品分析”、“文艺信箱”等专栏,大力辅导群众创作。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发挥了重要的辅导作用。早在1952年,电台就成立了“工人文学协作小组”,坚持两周一次的文艺学习和写作讨论活动。开始的时候,学员只能写一些简单的通讯报道和快板唱词,后来经过专业作家和电台编辑的具体帮助,逐渐掌握了写作生活小故事和速写等文体,创作出一批较好的短篇小说。
上海各级工会组织是浇灌工人创作之花的园丁。最著名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成了培养工人作者的大学校。1950年9月,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题写的横匾“工人的学校和乐园”挂在了大厅。自此,这里成为工人学习创作和接受辅导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位于上海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大杨浦”建造了沪东工人文化宫,以及后来各区建立的工人俱乐部,在培养工人创作队伍中,做着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为了从实践中更好地培养工人作者,上海还采取了选拔工人作者到文学期刊担任编辑的培养方法。其中胡万春先后去过《劳动报》和《解放日报》;唐克新、仇学宝、郑成义和王宁宇到了《萌芽》;费礼文、殷锡泉到《劳动报》,费礼文后又调入《上海文学》;张英、孟凡夏调到《解放日报》;陈琼英调到《支部生活》;樊福庚调往浙江省作协工作。经过历炼,他们后来都分别成了作家和编辑。
正是在这样的重视和培育下,上海的工人创作队伍逐渐壮大。这支队伍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参加了电台《劳动报》或《群众文艺》等编辑部举办的创作学习班,他们都发表了数篇作品,但还不太出名,人数大概有两三百人。第二层次是在上海及全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较多文学作品、已经小有名气的工人作者,人数约有50人,其中包括沪东船厂的居有松,上海电话局的仇学宝、福庚,国棉十九厂的李根宝,上海分马力电机厂的张英,达丰印染厂的郑成义,华东开关厂的周嘉俊,上海钢铁结构厂的毛炳甫,新民机器厂的谢其规,上海电机厂的胡宝华,上海汽轮机厂的俞志辉,俞培荣,亚细亚钢铁厂的丁承羽,上海申新六厂的宁宇,上钢一厂的王金源,国棉二十一厂的徐锦珊,新亚电工机械厂的楼颂耀,上海铁路局的朱珊珊、陈继光,上海航道局的张士敏,以及金云、徐俊杰、肖木、高金荣、谷亨利、水渭亭、孟凡夏、钱士权等等。第三层次是很有名气,已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被收入作家传略的工人作家,如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陆俊超等。这个时期上海工人作家发表作品之多,获奖之多,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胡万春的《骨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得了世界优秀短篇小说奖。费礼文和唐克新的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日、俄语和世界语,并被介绍到许多国家。


胡万春:从写真人真事开始
胡万春,1929年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解放前,他家庭贫穷,母亲给人家当老妈子,他只是在耶稣教堂里免费念了两年多的《马太福音》,一天到晚唱着“哈里哈里哈里罗耶”,建国后才开始学文化,1951年开始给报纸写短小通讯,并试探着写一些特写与小说。
胡万春曾回忆说,“1951年,有一天,我在陕西北路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两本破旧的书,这就是高尔基的《童年》和《人间》。我翻了下就喜欢上了它们,买了下来。每当我工作完毕,我就一个口袋里放一本字典,另一个口袋里放一本高尔基的书,随时翻字典,随时读作品。尽管在这种困难下阅读,但我还是深深地被高尔基的作品吸引住了。当我读完《童年》,开始读《人间》时,不知怎么的,我的脑子里像电影似地映出了我童年时代的情景。我想,高尔基也只念过很少的书,能将自己惨痛的童年生活写出来,告诉别人,这该多么好。就是这样,高尔基的作品不仅教育了我,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而且还启发了我对文学发生兴趣,并从而去认识生活、理解生活。”

胡万春

胡万春作品

胡万春作品
然而真正拿起笔来写作依然困难重重。胡万春当上通讯员后,第一篇稿子是用嘴巴讲,记者帮助记下来的,结果稿子登出来是他的名字。他说:“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我还是开心煞了!厂里的师傅讲,‘喔唷,小胡啊,你做秀才了!’我讲,‘断命秀才!’但心里确实高兴。后来就自己拿起笔来写了。错字别字一大堆,当然退稿也一大堆,总共有200多篇。”但正是这200多篇后,他的字也写端正了,文化也提高了。1952年,他写出了3000字的特写《修好轧钢车》,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了出来。胡万春说:“我就是从写真人真事开始的。”
胡万春17岁进钢铁厂当工人,他熟悉炼钢过程,了解并热爱钢铁工人,他把最多的心血放在了钢铁工业这个题材上,所以胡万春写得最好、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就是不久后写成的中篇小说《特殊性格的人》,小说中的主人公王刚,人物生动,性格鲜明,是胡万春精心刻画的一个钢铁工人的形象。
1955年,他的自传体小说《骨肉》获得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世界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春》、《爱情的开始》、《谁是奇迹的创造者》、《过年》、《红光普照大地》、《特殊性格的人》。论文集《我怎样学习创作的》。
与此同时,胡万春积极参与电影和话剧创作,著有电影剧本《钢铁世家》和《家庭问题》;先后与黄佐临等人合作编写了话剧《激流勇进》和《一家人》,这两个剧本都曾获得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创作奖。1964年他来到越南抗美战争前线,回国后创作了中篇小说《铁拳》,获越南政府奖。他的作品被选进多种文学选本和语文教科书。
但胡万春再纯朴,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制约,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不公正的评价的影响,胡万春也在小说中把技术人员或技术干部,设计成“对立面”,造成人物模式的概念化。比如《发生在钢铁厂的事》《一个女炼钢工人》里,将技术员设计为思想保守,而缺少文化的工人反为先进,大力歌颂不当技术员而当工人。
同时,他在有些作品中将艰苦劳动万能化,有些作品甚至违背了科学精神,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接班”主题的概念化。小说《家庭问题》(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就很具代表性。小说中的福民从技校毕业进厂当技术员,可福民父亲硬逼儿子当工人,否则他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大少爷和小开,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就这样把一个家庭问题政治化。接班的命题,是作者当时在“阶级斗争”思想影响下在文学上自觉和不自觉的表现。
正因这样,文革后,胡万春审视自己,他把描写的中心从工人转移到了技术人员。如发表于1980年的《寂寞中的安慰》,小说讲述了一个从大学毕业生成为轧钢机械设计专家的故事,尽情歌颂国家建设需要科学技术的主题。1982年,他发表的《烘云托月》,主人公王双喜虽仅是一个小组长,但为让科研人员得到重用,巧妙地利用外宾来征服具有洋奴思想的厂领导。这是一篇具有歌颂和讽刺双重主题的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对国人思想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也为胡万春开辟了创作的新天地。他写作的题材已不局限于工人和工厂,而把触角指向社会,伸向老上海。曾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小说《蛙女》《情魔》《女贼》等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前两者被拍成电视剧后,深受观众的欢迎。
可惜这位工人作家不满70岁就因病去世。否则,在锐意改革、深入开放的今天,他一定会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作品。
费礼文:从《老兄弟俩》开始《成长》
费礼文,1929年生。解放前只读了3年书,14岁当童工,1945年后到上海做临时工。建国后进上海中和机器厂当工人。1950年转到吴淞机器厂(后来的上海柴油机厂)先后做铣工和滚工。费礼文说到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回忆起那段从“不敢”到“敢”的路程,依然激动不已:

费礼文电影剧本《钢人铁马》

费礼文

费礼文作品
“1952年,我因积极参加职工夜校学文化并取得一点成绩,被评为上海五金工会系统的学习模范,夜校老师要我写篇获奖后感想,发表在厂部食堂门口大黑板报上。未料想,我写的这篇以解放前后学文化的苦与甜为内容的短文,竟引起当时在厂里参加民主改革的《劳动报》记者唐铁海、杨振龙等人的关注,他们和厂工会领导找到了我,说我那篇短文写得有真情实感,有点写作潜力,因此鼓励和动员我担任报社通讯员,给报刊写稿。一开始我遭到12次退稿的挫折,但在报刊编辑、工人群众的帮助支持下,我写的稿子终于在报上刊出,而且越登越多。接着,我参加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组《劳动报》这一组的学习。开始是旁听,我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兄弟俩》,就是在我当‘旁听生’时写的。稿子投寄给《文艺月报》,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跨进巨鹿路作协的大门,见到当时编辑部负责人之一的老作家魏金枝和小说组编辑、女作家罗洪、欧阳翠,经过他们热情帮助,这篇习作很快在该刊1953年五月号上发表。从那以后,我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而它们都经过魏金枝的亲自审阅和指点。”
1955年,费礼文的早期小说代表作《一年》发表于《解放日报》颇得好评后,1956年被调往上海《劳动报》当记者、编辑。不久,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成长》。1959年调到《上海文学》任编辑。1960年成为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期间写有《不落的太阳》等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出版短篇小说集《金色的雄鹰》,中短篇小说集《早春》和《竞赛没有结束》等。大都是描写工厂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工人们的心声和对未来的追求。
接着,他参与了电影剧本的创作,相继发表了《钢人铁马》《船厂追踪》《他们在成长》《风流人物数今朝》(根据自己小说《王林鹤的故事》改编,与艾明之合作),话剧《一家人》(与胡万春等合著)。
费礼文说,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中,一直得到老作家的关怀和培养,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评论,如欧阳文彬写的《费礼文的“钢人铁马”》《致费礼文同志》,晓立(李子云)写的《费礼文短篇创作的新收获》等等,他们从点到面地剖析了当时创作的得与失,对自己帮助极大。
作为从产业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工人作者,费礼文感慨地说,尽管那段时期,不少作品还很稚嫩,但毕竟反映了过去很少见到的工人生活,使得整个社会文学画廊中或多或少增添了普通工人和劳动者的人物形象。
但他毫不讳言,由于当时受到“左”或“右”思想影响,使有些作品变成了某项政策的图解。费礼文谈起过去的教训还带有激动。他说,比如我在创作电影剧本《激流》时,当时正是庐山会议后所谓“反右倾”时期,为了完成这一“主题”,就根据事先画好的框框,到生活中去搜集素材,尔后根据“政策”要求来编故事、安排人物。尽管当时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不少因“反右倾”造成的种种恶果,以及许多浮夸、虚假的东西,但是我却怕违反“政策”而把它当作“非主流”、“非本质”丢在一旁。结果是,剧本写得似乎离“政策要求”越来越近,而它所反映的却是离真实生活越来越远。尽管这个剧本后来还是拍成电影发行了,但是这种只是为了图解某项“政策”和“中心任务”的作品,又怎么能打动观众的心?只能是过眼黄花而已。
他还说,又比如我在写一篇反映工人搞技术革新小说时,开始写得还较为生动,但等到我按“政策”框框去衡量它时,又开始害怕起来,感到这儿不符合先进典型标准,那儿有损人物形象,于是先对它一遍一遍地“磨平”,把原先尚能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些生动情节,都当作“犯忌”东西“磨”掉,然后,再脱离生活实际地对人物进行“拔高”,向所谓“高大英雄形象”靠拢,不断加大他的“英雄行为”和“豪言壮语”,直至顾不得吃顾不得睡,没有家庭生活,更不许谈情说爱等等,你想,这样的人物还能真实可信生动感人吗?
费礼文是真诚的。不过他还欣喜地告诉我,今年正逢他创作生涯60年,上海作协为他编选的四本文集(约百万字)将出版,为正视这段历史,他“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自己的作品。
唐克新:纺织厂里写“女神”
唐克新,1928年生。他只读过2年的书,12岁当童工,建国后进了上海国棉六厂。比起其他几位工人作者,唐克新的起点是比较高的。虽然他受的教育并不多,但是却接触了大量民间文学,他有一定的文艺素养和艺术积累。不过,唐克新心里很清楚,光有过去的一点东西,光有旺盛的创作力是不够的。

唐克新

唐克新1963年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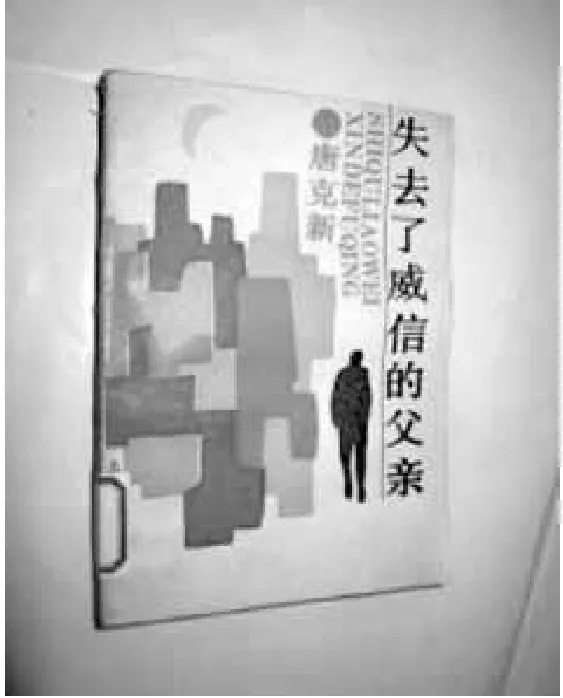
唐克新作品
1952年,唐克新参加了电台的工人学习班,每周都赶去听课。文艺组的编辑陈榭和王友枚经常组织大家讨论、分析作品。他勤动脑筋,细心揣摩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各有什么优劣之处。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一定要深入生活,发现生活中的本质东西,并且要写自己熟悉、理解的生活。
唐克新对新旧工厂的变化十分敏感,他几乎是在一个夜晚就写出了处女作《车间里的春天》,讲的是要安装冷风机,使车间温度降下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文章寄给了《解放日报》,编辑没有怎么改,就登出来了。由此,唐克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唐克新熟悉纺织厂,了解纺织女工,自打这篇作品后,他的笔触有了转变,专注于写人物,特别是纺织女工,写他心目中的“女神”。纺织女工们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劳动岗位上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创举,他要用作品展示的,就是她们的美丽心灵。
《萌芽》编辑、老作家欧阳文彬在《文艺报》撰文评价唐克新,说他在写作过程中肯动脑筋、越来越重视工人劳动的热情的由来,又注重对人物本质力量的发掘,他创作的速度不算快,把很多时间都化在了提炼思想上。小说《种子》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种子》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写了一位女工王小妹,从一个人们眼里的“累赘”,而无声无息地成了挡车的高手。作者采用心理线索和行为线索交相推进的手法,让读者心悦诚服。作者喻意,王小妹就像一颗种子,且是先天条件极差的种子,结果却结出硕果。把这种经验在全体工人中推广开去,使整个社会都“硕果累累”。这是何等美景。
1960年,唐克新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主人》。小说的主角仍然是纺织女工,不同的是她是一个行将退休的老女工。她不甘心做机器和生产工具的奴隶,于是摆脱了“只是为了做生活方便”的朴素想法,而投入到改造旧技术和发明新工具中,完成了“从工厂的主人到社会的主人”的升华中。这是作者靠着对生活的熟悉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
1962年,唐克新发表了影响最大,争议也是最大的中篇小说《沙桂英》。年轻的挡车工沙桂英以连续10个月不出次布的优异成绩跨入了工厂的先进行列。然而,她可爱吗?小说正是以一个大大的悬念为读者揭开了她美丽的面纱。接着,在工区落后、调车争论和恋爱风波等多回合中,面对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的关系,工人阶级的责任等尖锐问题,沙桂英作出抉择。这样一个新人物使作品获得相当的深度。但当时有人却认为,作者把人物写得不高,作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邵顺宝,更有“中间人物”的嫌疑,甚至更有人指责作者不应花这样的大力气来塑造这样的人物。但唐克新认为,这是他对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物的理解和刻画。“先进人物带动、促进中间人物,正是沙桂英精神的一个闪光点,工人阶级的荣誉感和先进帮后进的思想使沙桂英成为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中一个光彩熠熠的典型。”
对此,著名作家编辑魏金枝专门写了一篇《为〈沙桂英〉辩护》的文章,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总是从主观出发,希望在工作中不出现精神状态低下的人物,只希望出现英雄,而且是完整的英雄。这种心意固然是好的,但也确实违反了客观事物的规律。”而唐克新本人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应该遵循艺术规律,不能把原来真实的东西任意拔高而成虚伪的东西。《沙桂英》的诞生,体现了唐克新的文学良心和胆量。
唐克新后来被调到《萌芽》杂志当编辑,但他依然坚持下工厂,坚持写工人。十几年中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车间里的春天》《种子》《我们的师傅》,中篇小说集《失去了威信的父亲》和长篇小说《夜海飘流记》等。
面对创作上取得的瞩目成就,唐克新没有停止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粉碎四人帮后,他也开始反思工人形象的创作,他把关注生活的视野从工厂扩展到社会,从生产扩展到政治。期间,他写的《李天王》,就是反思后对于工人阶级人物特征的新观念,他向社会诘问,什么是老一辈工人身上应该继承的宝贵品质,老工人应该把什么留给后代。
1980年,短篇小说《选举》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大胆触及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领域——干部选举。作者正式运用文学方式,参与到整个民族对现代化的思考中去。
1984年,他又为读者奉献的反思形象是一个失去威信的工人,最后还竟成为“杀人犯”。这是当代文学从未出现过的工人形象。小说的震撼意义并不在于暴露了文革中发生在工人家庭中的悲剧,而在于揭示了工人心灵上最大的痛苦。过去曾经是最受尊敬的工人阶级,为什么现在被先进、被帮助、被提高,为什么表面上的先进伟大,实际上却失去了威信?作者用他艺术上日趋成熟的笔触给我们描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一段惨淡的人生,发人深省。
陆俊超的“幸福港湾”
陆俊超,1928年生于上海崇明县的一个海员家庭,自幼随叔父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侨居。叔父是教师,有很多藏书,因此陆俊超虽然上学时间不多,但却在童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书籍,特别爱看张天翼、严文井的童话。稍微长大一点后,喜欢看鲁迅的作品。成年后,可能由于在远洋船上生活的缘故,对欧美文学发生了兴趣,而且喜欢把欧美文学、欧美生活同中国文学、中国生活作比较。早在17岁那年,他就上船当水手。1946年回国后在国民党所属的商船上工作,在水手舱里度过了青年时代。1949年解放时参加船上起义,后来在中国和波兰合营的中波轮船工作,先后担任驾驶员、大副和船长。
陆俊超接触许多不同国籍和民族的海员,又经历过漫长的航程,到过各式各样的码头和港口,听过形形色色的故事,这些都为陆俊超准备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而这时,时机到了。陆俊超说:“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海员扬眉吐气,使中国真正有了自己的远洋事业。正是在这种完全崭新的生活刺激下,我的创作欲激发了,这才使我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

陆俊超

陆俊超作品

陆俊超作品
不过,陆俊超清楚地知道,要把经历变成精彩好看的文学作品,并非容易。他在仔细阅读欧美海洋沿岸国家作家所描写的海洋生活的作品后,有了这样的体会:“不但要把海洋写得生动,更要写出人物的精神,人的精神才是文学的灵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写出了一个老人的价值,这是当代文学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我还发现,欧美民族很早就有开拓海外市场的意识,民族性格比较开放,所以海员生活也比较丰富多彩。而中国人少有开拓意识,长期闭关锁国,民族性格也比较收敛,倒是中国海员的反抗精神却是出了名的。”
1956年,陆俊超的处女作《海洋的主人》写成,他像普通作者那样寄给了《萌芽》编辑部。中国的海洋文学很少,现代文学中只有冰心等人的一些零星描写,当代文学中陆俊超可谓是第一个海洋小说的作者。《海洋的主人》描写了一个年轻船长逐步变成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船长的过程。小说中优美的海洋风光,映衬着海洋主人的硬汉风情。当《萌芽》主编哈华从编辑手中接看这篇作品后,不由被感染了,当即决定发表。
初尝创作甜头的陆俊超大为鼓舞,他决定全方位地描写中国海洋工人这一伟大的群体生活。果然,在以后的创作中,他的观察“雷达”扫描到海洋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从后来他创作的《姐妹船》《劳动号油轮》《海的回声》《台风》《幸福的港湾》等小说中看到,陆俊超书写的对象从船员、水手长到船长,无一不是一曲英雄的赞歌,一曲集体主义的赞歌。
中篇小说《九级风暴》是陆俊超的代表作之一,它描写了一场不逊于海上九级风暴的起义斗争,很有传奇色彩。小说讲的是1949年9月,停泊在新加坡的国民党政府商船巨轮“凯旋号”,在地下党员和革命烈士后代的鼓动带领下,大多数船员响应起义,将巨轮开回新中国,回到人民怀抱的故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困难连着困难,在与国民党内外斗争中,斗智斗勇,赢得了胜利。同样写好后,陆俊超仍以一个普通作者的身份,寄给了北京《人民文学》。虽然他那时已认识了有关编辑,但陆俊超告诉我,文学作品靠的不是名气,也不是关系,“投稿”才能看到它的“真质量”。编辑部真是慧眼识宝,相关编辑在来稿中读到了它,不仅是情节,更是被人物的心灵所打动,主编审读后毅然决定刊出,而且是破例。于是,1959年8月9月,这篇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海员英雄传奇分两期刊出。据说,该刊中篇“连载”还是第一次。

陆俊超的书房
国际主义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陆俊超有段时间在中波公司工作,较多地与外国船员共事,较深地感受到国际主义的宽广伟大,所以从代表作《国际友谊号》到《铁锤和镰刀》《惊涛骇浪万里行》等,在结识和赞扬中国海员先进思想的同时,又宽泛地上升到了国际主义的高度,使之小说更真实,更显高度。
我们不能否认,陆俊超的小说中有过多的阶级斗争意识以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的描写,使小说承担了过重的政治功能。但这并不是陆俊超作假,而是当时的历史就是那样在发声。陆俊超独有的海洋小说还承担了历史记载的功能。如昨日的苏联已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但陆俊超的小说里,依然记录和保存了这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
那天,在上海西区的一幢老房子里,坐在那间简易的书房里,听陆俊超谈论他的创作之道。远洋轮出洋一般得几个月,我好奇地问,这期间是写东西的最好时机?没想到陆俊超却说,不。因为,他是大副、是船长,“掌握远洋轮的方向盘是来不得半点疏忽的,尤其是在远离陆地的大海之中,天气异常恶劣之时。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作为船长我也得全面管理。”所以,他的作品基本就是回港后,利用“积假日”写成的。
不过,他非常感谢船员们准确地提供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素材:“在船上,看来看去这几个人,讲话炒冷饭,翻来复去这么几句。穷极无聊,只好打牌或者恶作剧。从这个角度看,船员的世界又是太窄小的世界。然而,文学却要讲幻想、讲浪漫的。这需要人的化腐朽为神奇本事。几十个人,小小的天地朝夕相处,在漫长半年一年的航程中,把家里包括祖上的事都讲遍了。了解一个人没有比船上更有利。你不要他讲,他也要找你谈。船上的人各式各样,都看透了,闭上眼睛或写的时候,这些人物就一个个跳了出来。”
“把人物看透”,是陆俊超的本事,到了岸上自然能笔下生风。不用说,陆俊超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聪敏和刻苦。文革后,他仍没有停止创作,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相逢在安特卫普》是最好的证明。
陆俊超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他称自己是“慢手”。他说:“我自信每篇稿件都经过了长期酝酿,深深打动自己才动笔。完稿后至少朗读修改数遍,定稿后还将其搁置一段时间,我称之为冷处理,最后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再朗读一遍,若它仍能感动自己才将其寄出。我的主要职责是当船长,创作是业余爱好,我缺乏发表欲,追求的是质量,强调以勤补拙。”
一个为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海洋文学填补空白的作家,尽管当了大副、船长,依然在海洋文学创作中耕耘,可喜可贺。
记者手记
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陈思和曾在《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中写道:“海派文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繁华与糜烂同体共生;另一个是现代工业发展中工人力量的生长。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人文学创作留下的辉煌,它所描绘的是上海最为发达的工业行业、工业技术和最为先进的工人形象,它概括了海纳百川、积极进取的城市精神。这与当时提倡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民主精神的主流思潮相吻合。在当下社会,虽然遭遇拜金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冲击,但是工人文学关心民族工业的发展,关注上海的城市建设,为国家和自身利益大声疾呼,仍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描摹着我们所向往的“中国梦”。这或许就是今天我们重谈当年工人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
毋庸置疑,上海的工人创作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作为海派文学的一部分,显然创作不会停止。事实真是这样,文革后期,工人创作的热情开始涌动,文革一结束,被压制的创作热情爆发出来。接棒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成为基地和中心。《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屋外有暖流》《街上流行红裙子》《路》《大桥》《中国制造》《谁主沉浮》《大潮汐》《无暇人生》《红色康乃馨》等一批剧作应运而生,一批影视剧作家脱颖而出,他们是宗福先、贺国甫、贾鸿源、汪天云、陈心豪、史美俊等。这是继“十七年”工人文学后掀起的又一个繁荣期,特点是他们的创作在题材上有了更大的拓展,不仅写现实题材,也写革命历史题材,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反映工业建设,塑造工人形象,直面社会现实的创作特点。他们代人民立言,弘扬共产党员的公仆精神,鞭挞腐败分子的堕落行为,使我们在新世纪的上海文学中感受到一股强劲的雄风。显然这不是几句话能概括得了的,这或许是我应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当然我们更值得期待的是,当世界范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我们的工人文学作者一定会在新的领域,探求新的题材去描绘崭新生活,而欢呼新作品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