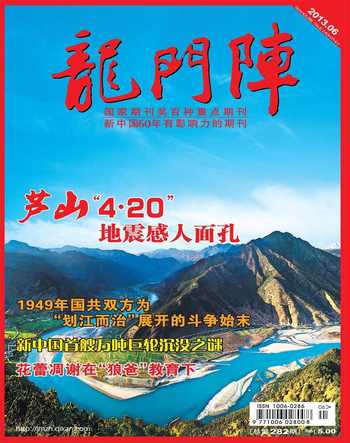何洁眼中的巴金伯伯
蒋蓝
2011年10月中旬,我到青城外山看望青峰书院主人、作家何洁。何洁系晚清名臣、两江总督何桂清之后,父亲是左联诗人何小石(何菲),母亲郑雪华与巴金的两个妹妹李淑英、李淑华旧时同在成都电报局当译电员,巴金的庶母是何家的姑妈,何家与李家算是老亲戚。其间我们谈到巴金,何洁说,“巴金逝世时我从不讲这些,是怕被人误会,以为自己在利用什么。‘巴金热早已烟消云散,现在我可以说了。”她走进书房,找出一封夹在笔记本里的信件递给我,一看竟是巴老的亲笔信!字迹娟秀,航空信封上落款是“上海文联巴金”,邮戳上可以看到,平信寄出的时间是1991年5月9日。这封信,把那些细微、绵长的情感一下子拉了出来。
何洁幼年患眼病,看不到任何东西。那时,她家住在成都红墙巷,听到母亲在家里招呼来访的“四姻伯”巴金,她也喊“巴伯伯好”,巴金总是爱抚地摸摸她的头。对这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巴伯伯,幼年的何洁充满了好奇……
武康路一一三号
何洁第一次亲眼看到巴金伯伯,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1957年春季,16岁的何洁随成都川剧团到上海“天蟾大舞台”演出。当时巴金住在上海武康路,何洁除了参与剧团事务,一有空闲就往武康路跑。
武康路全长1183米,宽12米至16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可谓宽裕。道路北端连华山路849号,为重臣李鸿章的花园,南端接淮海中路1843号,是宋庆龄故居。沿途两边遍布上海知名洋人和达官名人、商贾富豪的住宅,古木佳卉,一派静谧。当时,巴金的住宅门牌编号是武康路1号,后来反过来重新编号,便成了113号。
113号是沿街的第一座庭院,系英式乡野花园洋房,始建于1923年。陡峭的红瓦屋顶,赭色细卵石贴面,岁月又褪去了墙体的矜持,显得朴素而厚重。因为坡顶的关系,3层楼房看上去像是两层带阁楼的房屋,阁楼窗台呈半圆形,窗架为木头制就,下设10个小孔,使室内空气得以对流。南立面底层设有敞廊,北立面入口设置券心石的半圆形拱券。此地曾作为苏联商务代表处所,1955年,陈毅市长特将这套别墅批给巴金使用。院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枝繁叶茂。刚开始,巴金的妻子萧珊嫌光线太暗,而巴金却偏爱这两棵广玉兰,于是一家人就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40多年,成了巴金在上海栖身最久的住址。一楼是会见客人和记者采访的地方,二楼是巴金的书房和卧室。巴金住这样一幢租金不菲的洋房,却是当时唯一一位不拿国家任何补贴的体制内作家,他在此完成了《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译作、散文及小说。
何洁高兴地来到武康路巴金的家,拍打深色的铁门,为何洁开门的是巴金的岳母,何洁亲切地叫她阿婆。阿婆个子矮小,满脸笑意,可惜何洁听不懂她满口的宁波话。廊道两侧的花架上摆满了一盆盆七里香,庭院里有一个50平方米的草坪,几把藤椅围绕一张小桌子,那是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何洁第一次见到这位只闻其声的巴伯伯,他和几个人正在谈天。何洁高兴地跑了过去,那只曾经抚摸自己脑门的手,现在正握着自己的手,她觉得好像有点别样,但手的温度让她确认是同样的温和。这个满脸笑意的中年人,好像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稳重,轻言细语,根本无法察觉他的喜怒,就连挥手的动作都透着四川人罕有的轻与慢。
巴金亲热地向在座的各位介绍:“这是我们李家的老亲戚,来自成都。她母亲雪华是成都青年会的著名票友,现在女儿也喜欢上了川剧。”然后他为何洁逐一介绍在座的各位:作家张恨水、靳以,当巴金指着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介绍说“这是大戏剧家曹禺先生”时,何洁惊喜地睁大了眼睛,她简直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雷雨》作者就坐在自己面前!
长头发的曹禺一听何洁会唱戏,高兴得直甩头发,他热情地把小姑娘拉近,坐到自己腿上:“你会唱戏?可以唱一段给叔叔听听吗?”在巴金鼓励的眼神中,何洁站起身,拿了一个身段,唱了川剧《贵妃醉酒》片段,赢得满堂喝彩。怯意一去,何洁的本性就亮出了光彩。她意犹未尽,自信地说:“我还可以唱沪剧呢。”曹禺不大相信:“你初来上海,如何会唱呢?”其实这是何洁刚在“天蟾大舞台”现学的,她便热炒热卖地唱了一段《罗汉钱》,不料得到曹禺的高度评价:“有味道,有味道!”
曹禺说:“这出现代剧是剧作家宗华、文牧、幸之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创作的,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主演,盛况空前。这出戏的剧情并不曲折离奇,描写建国初期一对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故事。主人公李小晚与张艾艾相恋,以罗汉钱为定情物……”听到这里,16岁的何洁一脸鬼笑,鼓起大眼睛扫视大家,惹得各位大笑起来,笑声惊起了树梢上的几只鸟,它们停在空中,再从笑声的间隙回到树巢。
曹禺话锋一转,突然谈到《雷雨》。初出茅庐的何洁大声说:“我不喜欢《雷雨》,我害怕打雷!”巴金听了,笑得前仰后合,藤椅被摇晃得吱吱呀呀。曹禺拍拍何洁的肩头,很喜欢何洁的率真,由此开始与之通信,谈表演,谈人物,长达两年。
巴金问何洁平时看些什么文学书。那个年代,喜欢文学几乎就是青春期的唯一合法选择。何洁对巴伯伯说,自己也不喜欢《激流三部曲》,觉得读起来像翻译小说,只喜欢《憩园》,因为这篇的文风才是巴金独有的。“伯伯,你是用《憩园》告诉读者,祖宗的财产是套在子孙颈上的枷锁,只会使其坐享其成,最终丧失独立的能力沦为悲剧。”巴金“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他沉思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惊异,镜片上是一片白光和树影。何洁估计,巴伯伯可能觉得她这个大胆的小姑娘过早地看懂了小说,未必是好事。
临走时,巴伯伯亲自送何洁出门。这是古礼,尤其是长辈送晚辈。何洁记得,那时巴金走路的姿势十分凝重,动作缓慢,就像一个脚杆上套了铁沙袋的僧人。巴金站在武康路113号大门前向何洁挥手告别,好像送来一股股暖到心田的和煦春风。这时,恰有几个小学生从门前经过,他们向巴金行礼,巴金也客气地点头致谢……
这难忘的一幕,时隔50多年,何洁依然历历在目。她哪会想到,紧跟而来的“反右”雷声,就炸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她和钦点的“大右派”流沙河,竟然海誓山盟……
手艺人巴金
一晃,15年过去了。
1972年,命运多舛的何洁到上海治病,自然也要去看望巴伯伯。当时,她的处境非常困难,与下放监督劳动的丈夫流沙河住在金堂县城厢镇,她是借了几十元钱来上海治病的。何洁来到上海后,不好意思去打搅巴金,单独一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最后她还是决定去看看巴金伯伯。她心目中的文学圣地武康路113号,可惜已经面目全非了。落叶满地,学生们斗志昂扬地从落叶上踩过,发出碎裂的巨响,听上去有点惊心动魄。
为她开门的是一位中年人,穿中山服,戴眼镜,模样很像巴金。何洁心头一惊。后来才知道,这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的丈夫祝鸿生,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见何洁来了,巴金仔细端详了很久,他已经认不出那个满嘴戏词的小姑娘了,当巴金得知眼前站着的人是何洁,非常高兴,他与何洁在草坪上一边走,一边摆龙门阵。
何洁一直觉得那个草坪很阔达,现在竟发现它变得很小。周围已经耸起一些高楼,武康路113号深陷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中。巴金的书房早已被查封,所有藏书被搬到庭院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两张封条十字交叉,封死了阅读、思考的空间。
何洁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巴伯伯讲,讲自己没有工作,如何苦苦挣扎,讲自己的婚姻,讲“大右派”流沙河就是自己的丈夫,讲女儿余蝉和儿子鲲鲲,但目睹眼前的一切,她把话生生给咽回去了。
巴金的腰身已经不大灵便,身形有点佝偻,深勾着头,陪着何洁在庭院慢慢散步,一圈又一圈。巴金讲到何洁的父亲何小石:在北方左联作家中,何小石主要写诗,偶尔也从事翻译和小说写作,可惜保存下来的太少。何小石是一个绝顶的天才,二胡、胡琴、笛子、提琴样样都好,还会唱京戏,可惜天不假年,弃世太早了……老人偶尔斜睨一下那被查封的书库,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走着。何洁很快明白了这里的一切,她不怕,她说:“巴伯伯,我要把封条撕了!”巴金急忙制止:“不要动!不要动!二天(以后)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当时,何洁甚至产生了将巴金接走,送到一个安全地方的惊人念头。可惜普天之下,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来到厅堂里,何洁看到桌子上只有一本当时流行的时政刊物《学习与实践》,那是家里唯一被容许阅读的书刊。巴金不再说话,慢慢坐在桌子前。何洁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堆拆开的打火机零件,各种牌子的都有。巴金戴起袖套,从抽屉里摸出一本修理指导书,他竟然在学习修理打火机!巴金叹口气,说:“唉,无事可干,学门手艺也好哇!”
何洁不说话,看着巴金伯伯动作迟缓地摆弄零件,渐渐发现他很精于此道。他组装好了一只打火机,嚓嚓嚓掀动磨轮,火光四溅,但他又慢慢拆开,拆得七零八落,然后又开始试着组装,并且把不同型号的打火机零件相互组合……一代巨匠,他的生命被改刀、螺丝肢解,他就是用这种“无用功”,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何洁觉得,那个修打火机的巴金,比印象里的巴金还要慢。他彻彻底底地慢下来了。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骨头也会适应这一节律。他慢下来,像木质纹理那样慢,像绿叶回到枯枝那样慢。他听得见金蝉脱壳的声音,也听得见土拨鼠分娩的呻吟。但是,他不是一只懵懂的蜗牛,因为他知道,慢是镶嵌在生死之间的细腰。一个思想者与打火机相恋,就像是在煤矿中挑选出矸石,一方面是从金属器具里剔除不合理的东西,让团结、紧张、滴水不漏成为运动的和谐主义;另外一方面,他又仿佛是从黑中选美——那是他的寄托吗?他还有寄托吗?
每天擦拭妻子的骨灰坛
萧珊阿姨生命的最后几年,可谓备受摧残。她整天处于对丈夫的担惊受怕之中。1972年夏季,萧珊死于肺癌。临终前巴金没能赶到她的床前,她的葬礼也很冷清。萧珊的死,是巴金性格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巴金可以对一切横加的事端均沉默待之,那主要是因为他背后的萧珊,温情可以疗伤,也可以洗去屈辱。一旦这个温情失去了,他就看不到后背上被人涂鸦的东西了。夫妻之间,即便在易帜后的岁月里也有大量信件往返,至今还保存有近400封之多。1956年12月8日,萧珊给出差在外的巴金寄信说:“告诉我多一些,让我也可以追随你遥远的眼睛。”而巴金在《怀念萧珊》里,刻意提到了马克思夫人燕妮的那双明眸……这都不是偶然。
1972年,李小林已经怀孕。一天,大家谈到了一些伤感的事,何洁抚摸着李小林的肚子说:“宝宝快点出生吧,好为家里分担一点事情!”话一出口,小林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何洁也哭,但大家立即止住了声音。她们不敢再哭,一哭的话巴金就控制不住了。何洁确实咬牙止住了哭泣。李小林说:“记得母亲逝世时,爸爸见到母亲的灵床缓缓地推了出来,他五官挪动,真想捶胸顿足地痛哭一场,但也憋住了。”何洁觉得,巴金的抑制力到了惊人的程度。
何洁看到一个五斗橱顶部放着一个坛子,那是萧珊的骨灰坛。巴金颤巍巍地站在一把小凳子上用抹布擦拭。何洁抢过抹布说:“我来擦。”巴金轻声说:“我来,我来,我每天都要擦一遍!”
巴金的动作极慢,一遍一遍地擦,坛子光洁如新,反射着室内的灯光,也把巴金的身影印在上面。他擦拭了足有十几分钟,好像觉得累了,又伸直腰站了一会儿才从小凳子上下来,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骨灰坛。他没有流泪,但镜片灰蒙蒙的,何洁看不清他的眼睛!
何洁后来才知道,萧珊固然患有癌症,但在发病前,作协的一批人到巴金家里抄家,萧珊跑到三楼与他们发生了争执,她被人猛推了一把,顺着楼梯滚到了楼底。当夜萧珊就便血了。
知道何洁要回去了,巴金拿出一些工业券和副食品票证,让何洁去买些内地紧俏的服装、食品等,何洁拒绝了,因为她身上根本没有钱。巴金执意要送何洁点什么,最后叫女儿买回一大盒奶糖送给她。何洁一直不敢向巴老提自己的婚姻,害怕再给老人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她曾无数次鼓起勇气,可每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只是说,自己的丈夫是老家的一个工人。巴金点头,那就好,那就好……
当时巴金就睡一张小床,但他每天休息之前,总要在床边再铺一张小床,床单、枕头均是他亲自打理。巴金说:“儿子在外地,万一他突然回来了,就可以休息了。唉,儿子……”
听说沙汀患了神经衰弱症,巴金十分关心,详细询问过程,授意何洁与李小林去静安寺给沙汀购买了谷维素等不少药品,何洁将这些珍贵的药品带回成都,亲手交到沙汀手上。文学与亲情,是巴金感知世界的窗口,也是唯一的窗口。
为了让暮气沉沉的家里有一点生气,何洁又为巴金唱戏,《情探》《考红》《归舟》,一个接一个。这是怎样一种演唱啊,还有1957年第一次在武康路113号放声高歌的那种气韵吗?那是一种带着泪声的演唱,巴金静静地听着,低垂着头,偶尔抬起来,看看何洁,渐渐地,眼里泛起四川锦江的波涛……
何洁知道,巴金伯伯顺着乡音回家了。
为了彻底摆脱烦恼,巴金曾经说:“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到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请让我安静”。 巴金逝世7天之后,2005年10月25日,巴金家人将巴金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大海。
巴金的回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洁已经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她的中篇小说《落花时节》在1987年《十月》杂志第一期发表,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这时,她才鼓起勇气给巴伯伯写信,第一次将自己的真实生活情况以及写作状态和盘托出,并寄去了当期的《十月》杂志。
几个月后,巴金挥笔回信:
何洁同志:
从北京回来读到你的信。谢谢你的照片。你的事我也知道了。好些人夸奖你,你做得对。你上次到我家的情况,我还记得一些,但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我家里人都好,只是我的小妹(今年六十五了),去年小中风后至今手脚不大灵便。我近几个月来身体也不好,写字很吃力,因此不多写了。请替我问候流沙河同志,这些年吃够苦了。但比起刘盛亚同志来,他能活到今天,还是幸福的。我看过影片《巴山夜雨》,看到那位诗人就想起你的丈夫。希望他勤奋地写下去。愿你们过得幸福。
祝好
巴金
五月九日
巴金信中提到的刘盛亚(1915-1960)是重庆籍作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流放峨边农场劳改。1960年病故,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是何洁保存至今的巴金伯伯唯一的手迹。当何洁在1994年3月再度来到武康路113号时,坐在轮椅上的巴金,拿着何洁送来的五通桥豆腐乳,感慨地说:“你十几年前送的那床四川凉席,搭上补丁我还在用!谢谢你了……”其实,巴金就连平时使用的卫生纸,也是从成都买去的草纸。
那场浩劫,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对于这个问题,作家沙汀曾对何洁讲述他的一次遭遇:
“我在接受审查时,身上所有的鞋带、裤带被收走,老保姆给我送饭来,我是提着裤子跳过去,一只手接饭盒,一只手拧着裤腰。你说,是悲剧,还是喜剧?”
听完何洁的这段转述,正写《随想录》篇章的巴金沉思半晌,说:“他说得对!”
在何洁看来,巴金伯伯好像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他的行动不但持重、缓慢,而且他的内心也在一种“推刃”一般的慢性中,不停割伤自己。
何洁告诉我这些往事,我不禁想起2012年初采访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龚明德(他曾担任《巴金的一个世纪——庆贺巴金百岁华诞》等多种图书的责任编辑)时,他对我说,百年来新文学有两大划时代人物:鲁迅让人们看到了皇权与生存权的关系;巴金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灾难,并上升到人性思考。他的忏悔意识,他早年翻译的大量作品至今未受重视;他对“十二月党人”(编者注:指俄历1825年12月发动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武装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的倾情也是值得深思的。记得我一次去上海他家,恰好他收到一笔稿费8万元,他找儿女们借了两万元,凑10万整数就捐出去。他捐款用的名字是“李芾甘”,别人也不会在意。我写过数十篇文章谈巴金的人与文,做得远远不够。他的一生,完全印证了他的真话:“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我做了我能够做的事。”这样的话,几个人敢说?真是黄钟大吕之声。
1999年2月,巴老的病情突然恶化,巴老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要求安乐死,有关方面自然不会同意。结果巴金屈服了,一如他几十年一贯那样,最后说的是:“好吧,从今天起,我为了你们大家活着。”
一个人固然不能决定自己的生,看来更无法决定自己的死。觊觎者渴望的东西,在那个植物人的躯体内,俨然已经被彻底置换了。
所以,何洁说,我们至今都没有读懂巴金。
(压题图:1994年,巴金与何洁)(责编:孙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