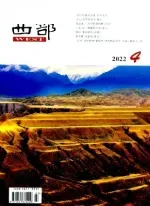征 服
文/王增锐
田里的禾苗窜到膝盖那么高就再也窜不动了。种子从种下到现在老天竟没掉一滴泪。正午的秧苗如同被火烤过一般,低着头立在田里垂死挣扎。村南大柳树下聚集着一堆人,他们在乘凉、聊天,人们正你一句我一句地咒骂着这鬼天气。忽听远处传来嘟嘟嘟的声响,人群闻声一齐向南望去……
只见南面大路上两辆摩托车前头开路,一辆红色小轿车尾随其后,风驰电掣般向北疾驰而来。
车辆来到村口,向西驶去。最后在村支书刘权贵家门口停下。轿车上下来几个人走向大门,其中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怀抱一个孩子,他就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村支书刘权贵。
消息像长了腿儿一样,第二天刘权贵买孩子的事就被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对于这件事,别人只当作是新闻传播而已;但对刘德才来说却是一个机会,一个扳倒刘权贵的绝好机会。
刘德才是村里贫困户。他好吃懒做,除去交粮,年年打的粮食不够吃。由于穷,他总觉得矮别人半截,走起路发蔫发呆,低着头,悄无声息,像只受气的绵羊。老婆和孩子拿他没有办法,整天骂来骂去。
村支书权贵是怎样招惹到刘德才的呢?
支书刘权贵的地紧挨着刘德才家的坟地。那年刘权贵拉土垫地基时,经过他家的坟地,将一座坟轧去了一半。老婆骂他,让他找权贵评理去。去了权贵家,权贵说下次不轧了,让他自己添添坟。刘德才没说难听的,自己添就自己添吧,德才像绵羊一样蔫蔫地回来了。后来权贵家拉土盖房,又在那儿块地取土,又轧了他的坟。德才又去找刘权贵。刘权贵和上次一样,说了同样的话。德才又像绵羊一样蔫蔫地回来了。第三次是刘权贵拉土垫院子时轧了他的坟。这下德才真生了气: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我穷我不欠你刘权贵的!你刘权贵欺人太甚!他见到刘权贵,两人三说两说就干起来了。刘权贵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像虎,又在他家,结果德才吃了大亏。从此他对刘权贵怀恨在心,总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德才得知刘权贵买来了孩子,就不安分起来,突然间说话嗓门子大了,眼珠子瞪圆了,走起来像占了七成理,嘣嘣嘣弄出声响了。他再不像绵羊了,与之前判若两人。
刘德才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去了刘书正的家。
刘书正,前任党支部书记。他在任期间,刘权贵任村主任。他见刘权贵交际广,手眼通天,县里乡里推门就进,能为村子办事,是个人才,就提前退下来了,将书记主动让给他。刘书正干了半辈子书记,虽未改变村中面貌,让人们走上富裕道路,但深得村民信任与尊崇。自从刘权贵当上书记,外界舆论装满他的耳朵,他对刘权贵也就越来越不满意了。
德才一进门就嚷嚷:“独门儿赵万海家四眼子绝户,收养了个男孩传宗接代,被派出所罚得过不了日子;人家刘权贵为已有三个女孩的儿子大张旗鼓买孩子,买得光彩,买得理直气壮,向哪说理去……”
刘书正已得知刘权贵买孩子的事。他有些不耐烦地听德才嚷嚷完,无可奈何地说:“权贵的孩子上了户口,说是替孤儿院收养的……”
“这话你也相信?口说无凭,得有证据。肯定是他买来的野孩子,又在乡里上了户口。乡里还不听他的,赵万海的孩子还不是他找人罚的!”没等刘书正话说完,德才就打断了他。
“那你说怎么办?”刘书正紧皱眉问。
“去乡政府调查,问问他们知道这孩子的底细吗,就给上了户口。看看他们做何解释。”
“你敢去吗?”刘书正心想又来了个背地当皇上的,就不屑地问。
“别说乡里,县里咱也不怕。”刘德才瞪大眼睛高声说。
“好,你去吧。需要啥材料我来写。”至今还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刘权贵,只是背地里说说而已,刘书正没想到穷困潦倒的刘德才敢跳出来闹事,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德才肯去跑腿儿,刘书正求之不得。
得到刘书正的支持和鼓舞,第二天一早,德才蹬着车子信心十足地去了政府大院。
他直接去了书记室,乡党委书记马永禄一人在办公室。
当马永禄得知德才是来调查刘权贵买孩子一事,感到很吃惊,便问:“你是干什么的?问这事干嘛?这是你该关心的吗?”
刘德才胸有成竹道:“我怀疑他非法买孩子,我问一问他的孩子哪弄来的,你们调查了吗,就给上了户口?”
“替孤儿院收养的。这有错吗?”马永禄很坦率的回答。
“哪所孤儿院?有证明吗?”
“你想干嘛?想要调查吗?”马永禄外强中干地问。
“没有孤儿院的证明,就是买来的或是偷来的。你们给他上户口同样犯法!”德才理直气壮地回答。
马永禄顿了顿,身子向椅子一靠,一面用手抚摸着光秃秃的头皮,一面极为平静地说:“孩子是从云南省那边弄来的,你愿去调查去云南好了。”
堂堂一个乡党委书记竟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理由,这不是袒护村干部吗?德才被噎地没了话,骂了句护犊子就愤愤离开了。
回家后,德才当刘书正的面大骂马永禄袒护村干部,护犊子。
刘书正说:“乡里袒护,你又拿不到刘权贵非法买孩子的证据,光发脾气有啥用,就得想其他办法。只要找到整治刘权贵的充分证据,乡里袒护也没有用了。”
德才想了想说:“刘权贵吃喝嫖赌样样全占,哪来那么多钱?没花大伙儿的才怪呢!应该查查大队的账目。”
刘书正点点头说:“和我想的一样。乡里纪检李书记是个好人,必须请他来,别人插不上手。”刘书正想了想又说:“在查帐前,我想先和权贵谈一谈,如果他认头花了大伙的钱,那该补就得补,该辞职就辞职;如果不认头,那就别怪咱们事先没通知他了,毕竟他是我一手提拔的。”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刘书正去了刘权贵家。
刘权贵热情招待,弄了一盘花生米,一盘兰花豆,豆腐干,豆腐皮“四大硬”,一瓶“沧州铁狮子”。平时刘权贵自己在家喝酒也没见他用过这些东西。
两人边喝边聊。酒过几巡,刘书正开始进入主题:“权贵,这几年群众对你反应强烈,说什么我就不再重复了,你跟我说句实话,究竟花没花大伙的血汗钱?”
刘书正突然来访,刘权贵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早就有了防备,极为平静地说:“哪有的事?甭听别人瞎起哄,别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地了。我刘权贵花村子的钱还不是为了村子?现在这社会,哪里离了钱能办事?昧良心的钱咱一分也不动……”
“这么说大队的账目没有问题?”
“花多少钱,办的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谁还敢查咱的账目不成?”
“我想看看账,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再说你是我一手提拔的,还你个清白不好吗?”刘书正挑明了。
刘权贵听后顿了顿说:“大队的账目,只有乡纪检才有权看。别人没权,也没这个胆看账!”
“这么说账目是没有问题了,不怕看了?
“一点问题没有。”
刘书正觉得他已做到仁至义尽了,就不再说别的,开始转移话题给自己收场……
一星期后,乡里下来工作组。
纪检书记老李带两人来到村大队部。大队会计老于等几名村干部带着账目早在大队部恭候。见乡里下来人,刘德才和刘书正也先后来到大队部。
工作组一页页地翻账,看得很仔细。刘德才在一旁紧着读,刘书正带个大眼睛,手握钢笔趴在桌上紧着画……再看大队会计老于他们,在院子里折来折去,心事重重,站立不安。
近五年的账目查到将近一半时,纪检李书记突然接到乡里电话,让他立即回去。工作组一撤,会计老于等人就涌进屋子将账目封起来。没办法,没有了工作组撑腰,德才就没权继续看帐了。
通过查账,发现问题真不少:就拿给村子修吃水井来说,用了二百块转,修井人员不开工钱,会计老于买了两条烟,总共花了不足二百元,而账上却是六百元。再有,为大队部灌液化气,液化气价格贵时两元一斤,灌满最多六十元,而账上却是九十元……
德才再也呆不住了,开始在村子传播查出的账目问题,鼓动乡亲们站起来造反。以前人们见了他理都不理,眼前就当没有他这个人。自从他公开去乡里调查刘权贵买孩子一事,有不少人见他就问这问那,热乎起来,客气起来,对德才另眼相看了。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和他一起公开反对刘权贵。
纪检书记老李再没回来。后来德才去乡里打听,听门卫说李书记被调走了。新上任的是一位姓贾的女书记。不管谁当书记,下面有问题没有理由不下来,再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她烧不烧。德才就直接去找贾书记。
贾书记曾经在大洼乡待过,经常下乡去大刘庄,德才一见就认识。她已听说大刘庄账目问题,她说现在正忙,让德才回家等候,她和工作组过几天就下去。
雨水姗姗来迟,玉米秧半人来深就撇出了玉米棒,这时老天下了场不太大的雨,旱情依旧没有得到缓解。这样高的玉米,秋后的收获可想而知!雨水似乎都去了南方。南方年年抗洪抢险,北方年年干旱,老天不叫人活了!人们站在大街上纷纷咒骂老天,哪有心情听德才上访的事。上级下发的农业开发款仍然没有消息,怕是指望不上了。后来有人提议集体集资打井,要不就没有活路了。
在德才焦急地等待中,乡纪检工作组终于又来村子里了。
这次账查得很彻底,工作人员有读的,有写的。整整一上午,近五年的账目全部都被誊写在桌面大小的几张红纸上。然后贾书记派工作人员将账目贴在大队部外面的公开栏上公示。为了防止账目被撕毁,德才找来照相机将账目全都拍了下来。
刘德才与刘书正将近五年的账目(九二年——九七年)进行了调查核实,账目涉及到的当事人,他们登门一一进行核对,工作繁冗复杂。账目中涉及的有村子修自来水、翻修学校等支出的;也有关于殡葬款,计划生育款等收入的。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核实,刘权贵近五年变相贪污公款数目被查清:
1、挪用上级给的农业开发款(定了公粮和其他用)
2、贪污殡葬改革款一万三千元
3、贪污计划生育款一万余元(不上账的不算)
4、贪污给村办自来水龙头款七千余元
5、从九一年至九六年五年村中总收入105万元,除去上交镇、打机井、盖学校、吃喝等大项开支64万,其余36万以其他名义报销。仍有5万元没有下落。
村中的账目大白于天下,人们对此反响很大,几天以来村账目问题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刘权贵贪污账目已查清,铁证如山。德才与书正开始商议下一步去乡里找贾书记和马永禄的具体步骤。
就在刘德才准备出发之时,听村子在乡里上班的人说纪检贾书记被调走了。这让德才不得不深思:为什么两位纪检书记一接触到大刘庄的账目,没过几天就突然被调走了呢?这也太巧了吧!德才想两次查账刘权贵都不在现场,是不是他在背后操纵的呢?这时德才感到自己的弱小,刘权贵的强大无比,从而想到整倒刘权贵的难度以及这样斗下去将会出现不可估量的后果。但他想他已没有退路了,既然已和刘权贵撕破脸皮,针锋相对了,就得斗下去,哪怕伤痕累累,遍体鳞伤,也只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了!
贾纪检书记调走了,德才就直接去找马永禄。
书记办公室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马永禄,女的德才不认识。但这位女子实在是美,是位可以当模特的美女。后来德才才知道那是新调来的纪检书记,马永禄的干闺女。
美女一见来人,便笑眯眯地与马永禄打声招呼,扭着小屁股懒洋洋地离开了。
德才说:“老马,你还有功夫和女人扯闲篇,村子出大事了。”他把查帐结果与马永禄详细说了说,问他打算怎么办。
马永禄听了不以为然地说:“都是些吃喝费,那也不能证明刘权贵他有贪污现象不是吗?”
“吃喝就是变相贪污!”德才一听他将吃喝费说得这样轻松就来了气。
“那不是给村子办事了吗?办事不就得吃点喝点?现在别说为公家办事,就是自家来了客人,你不也得弄点酒菜,喝几盅?没啥大不了的。”说完,马永禄很轻松地靠在椅子上。
德才听后很激动,咽了口唾沫,耐着性子说:“就算那六十四万里面含有吃喝费,那其余三十多万怎么解释?没有当事人证明,总不能也吃喝了吧?”
“现在这社会你不是不知道,哪方面都得需要钱去疏通,走关系,又不能光靠嘴,得用钱铺道,不就得吃点喝点吗?你没听社会上说吗?吃吃喝喝不算事,不吃不喝不办事,就是这个社会风气儿!上面光做好人,让下面做孬人,村干部一年吃个万八千的不算事……”
德才一听他大搞腐败宣言,公然支持腐败,公然为腐败撑腰,忍不住将桌子一拍,站起身大叫:“马永禄,你好没趣,有能耐你把刚才说的话写下来,签上名字,摁上你手印!”
马永禄一听直呼其名,五官移挪,气血冲顶:“那又怎么样?”
“我拿它告到中央!你敢写下来吗?”德才再次叫板。
马永禄一下子被叫住了,脸色发紫,忙转移话题:“你告我还是告刘权贵?我还有事,没工夫和你闲扯淡!”
德才见马永禄要走,用手一指大嚷道:“马永禄,刘权贵的问题到底解决不解决?”
“我不解决怎么样?你吃人不成?没有你这样说事的!”
“你等着,等村子收粮时咱再见!”说完德才摔门而去。
夏季征收工作即将开始,村主任刘二柱在大队部广播了一早晨。
以前家家种小麦,一到交粮时,人们都是往乡粮站拉运小麦,现在人们不怎么种小麦了,乡工作组下来直接向人们收取农业税。由于常年干旱,人们利用真空井浇地,时间一长,地表水被吸干了。村中有一眼深机井,有接近水源的,靠深机井浇小麦,成本又上不去……这些年小枣的价格一直猛涨,人们重视起了枣树,在麦田里栽种的枣树渐渐长大,由以前一家几十棵老枣树发展到每家几百棵,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枣之乡。小枣成为当地特产,这样特产税就充当了农业税中的一部分。
在工作组还未到村之前,德才又去乡里找过一次马永禄。马永禄还是那副嘴脸,铁嘴钢牙,包庇袒护刘权贵。德才与他大嚷了一通就回来了。
第二天,德才就接到一份处理决定书。这份处理书是由村主任刘二柱去乡里开会带回来的。上面是说当事人94至96年,97至99年度未按规定时间交清国家定购公粮和各项税费,让他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清全部欠款。如当事人不服,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本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乡人民政府将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看到这份处理书,德才就来了气:当事人是谁?为什么没有注明我刘德才的名字?我可以不接受。94年至97年各项税费我都如实上交了,有村民可作证,不存在欠交问题。98年大旱,颗粒不收,全村人都没有上交任何税费,为什么单单处理我?再有99年征收时间还未到,怎么提前下了处理决定,你乡政府就知我99年不交税费吗?德才带着处理决定去了刘书正家。
刘书正看了看处理书说:“征收工作就要开始,乡里怕你闹事,就提前给你下了处理书,来镇压你。”
德才更来了气,第二天一早,蹬车子去了乡里。
马永禄在书记室与女纪检书记谈笑。马永禄坐在椅子上,满脸是笑,涨红了脖子。女书记坐床边,床上床单凌乱不堪,两人像是刚刚在床上折腾过似的。
马永禄一见德才走进来,脸上立即沉了下来。他将干闺女打发走,一本正经地问找他什么事。
德才把处理书往桌上一摔说:“请问马书记,您这是给谁下的处理书?”
“给你的。有错吗?”马永禄看了看处理书理直气壮地问。
“给我的为什么不注明我的名字?”
“当事人那里没填,填写上就是了,这没什么大不了。”马永禄从桌上拿起处理书看了看不屑地说。
“没什么大不了,笤帚疙瘩还有名呢!你凭啥不注上我的名字?我可以不接受!不理你们!……”
“就这点破事吗?”马永禄打断话又问。
“这点破事?多了!我94——97年各项税费都交齐了,为什么说欠交?”
“听说你年年粮食都不够吃,好吃懒做,你说都交齐了,谁会相信?……”马永禄开始揭他的短。
“你放屁!”德才听后,忍不住大骂道,“谁年年不交粮?你可以将大伙儿每年交粮的原始账拿出来看看嘛!”
听到骂声,马永禄的脸腾地红了。他忍了忍吞吐道:“你说你交粮,你……你可有证据?……”
“那些年都是别人给我往乡里拉粮,他们可作证,你敢不敢去调查?”
马永禄擦擦头上的汗,耐着性子说:“你那也叫证据,谁不会找几个人作证?我还能找我儿子作证呢!”
德才见马永禄又开始胡搅蛮缠,便问下一条:“98年大旱,全村都没有征收,为什么单单处理我?是不是见我窝囊、老实、好欺负?还有,99年还没有征收,为什么就处理我,你们就知道我今年不交税费?”
“还有吗?”马永禄自知理亏,但又无话应对,只好装作极为平静的样子。
“没了!这还不足以证明你们政府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吗?”
马永禄用手抚摸着光秃秃的脑皮,装作毫不介意地说:“不就下错了吗?咱可重新下一份。”
“重新下?”德才听了火往上撞,“马书记,我问你,我挖了你家的祖坟,我说没挖能行?我睡了你老婆,我说没睡能行?”
听到这里,马永禄腾地站起来,用手一指德才大叫道:“你再他妈地胡说,就滚出去!把这里当你家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再敢胡来,小心以扰乱正常工作,把你抓起来……”
德才一面往外走,一面用手指着马永禄说:“马永禄,你等着,咱法庭上见!”
接下来德才与刘书正开始商议起诉大洼乡人民政府之事。就在这期间,他们中加入了一位新成员,增加了力量。他就是村南面粉厂老板刘大齐。
刘大齐占用村子土地,盖起面粉厂。前些年买卖一直兴隆。可现在当地没有了小麦,为维持面粉厂正常运转,他只好去外地购买小麦。见到一个个面粉厂面临倒闭,他便有了野心,他想将面粉厂的占地化为己有,变成自己的宅基地。他多次找刘权贵办理宅基证,始终未能批下来。为此,他对刘权贵有了很大的不满。
自从德才开始上访,揭发刘权贵买孩子,刘大齐就把德才的老婆叫到面粉厂上班。刘大齐就是通过德才的老婆得知德才上访的一些情况。他见时机已成熟,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要想起诉政府,就得需要钱请律师。有了刘大齐在背后支持,德才行动起来信心十足了。
德才去了县城,找到律师事务所,见到一位姓杨的律师。
杨律师四十来岁,听了德才的陈述后,不由得皱起眉头,显得很为难。
德才见此,便问:“是不是对这场官司没有把握?”
杨律师叹了口气说:“把握倒有。你明明交了农业税,政府却说你没有交。他们侵犯了你的名誉权,只是……”
“是钱的事吗?”德才见律师吞吐起来就问,“这两千元你放心,只要你肯出庭辩护,一分也少不了你的。”
杨律师摇摇头说:“不是钱的事,我看算了吧。告赢了又怎样?顶多给你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你不还得让人家管,以后办事你能离开政府,离开村子吗?自古民不与官斗。我这也是第一次与政府打官司……
听到这,德才不高兴了:“你是律师,吃这碗饭的,怕这怕那你就别干这行!再说我不起诉他们,又不可能再交农业税,过了十五日他们就得起诉我,到时候把我抓起来!冤不冤?”
杨律师口打咳声:“好吧,你回家等着,过几天我去你们村,去见见那几位为你拉粮的人,取些证据。”
政府工作组开始在村子里收购农业税了。政府大院的工作人员全体出动。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由大刘庄各队队长带领挨家挨户地串。他们所到之处不是大门紧锁,就是孩子或老人在家。本来收购工作难度一年比一年大,再加上德才上访,在村中大搞宣传,他们常常从早晨一直串到晚上掌灯,即便是这样,有些主人还是不见回家。
这期间,德才又接到一份处理决定书。上面所欠税费数目和年限全变了。德才想这又是在镇压他,就将其扔在一边,一心准备着起诉乡政府。
乡里为征收农业税下了血本儿,晚上见不到人,就早晨早早地来堵人们的被窝。一天不行就两天,两天不行就是三天……尽管德才逢人便大力宣扬拒交农业税,打倒刘权贵,为人们鼓舞士气,但人们终于抵扛不住政府工作组的持久战,大部分还是交纳了农业税。
在德才焦急的等待中,终于见到了杨律师。德才将律师领进家,然后去找证明人。
杨律师向几人询问了为德才拉运粮食的具体时间,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一张纸,让他们写下来,签上名字按上手印,就返回去了。
99年9月的一天,德才向县人民法院起诉了大洼乡政府。
由于上次下达的处理决定,在十五日之内德才没有去乡政府申请复议,他白天锁门躲出去,只有夜晚才悄悄回到家。
10月13日,德才作为原告,乡政府委托代理人刘某作为被告,在县人民法院开了庭。
一周后,德才得到了县人民法院寄来的行政判决书。法院认为,对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年度款数不符,事实不清,故法院不予维持。原告刘德才请求依法撤销对他下达的处理决定主张,法院给予支持。案件受理费40元,其他费用160元由政府负担。
这下德才心中有了底,他再也呆不下了,在大街上逢人便说,他打赢了政府,刘权贵就要倒台了……村中再次掀起一片沸腾。
接到判决书,德才没有兴奋多久,又接到一份政府下达的处理决定书,上面的年月及各项税与前几份均不同。德才正要去政府找马永禄,没想到他们又来此一招。
这次德才见了马永禄,他显得极为平静,似乎对打输了这场官司全然没放在心上。
刘德才气急败坏地将处理书摔倒在马永禄面前说:“你们政府纯属不觉死的鬼,输了官司,没脸了又下这破玩意儿!你们打算怎么样?对刘权贵到底做何处理?”
马永禄死皮赖脸地笑了笑说:“你赢了又能怎样,你不交粮我们就给你下达处理决定。上次让你钻了空子,说什么下错了,这次总没有下达错吧?刘德才,最后我奉劝你一句:自古民不与官斗,光棍不与势力斗。只要你不再咬住刘权贵不放,安心过日子,你之前欠交的农业税我们也就不追究了,何乐而不为呢?”
“谁他妈的欠缴粮了?民斗官死了也不怨,马永禄,咱走着瞧!”德才说这话像打出的炮弹。
接下来,德才又和马永禄吵了几句,见他如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蛮不讲理,无奈就气冲冲的离开了。
回到家,德才又找到刘书正、刘大齐等人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刘大齐说:“看来征服不了马永禄,休想搬到刘权贵,只有越级上访了。”刘书正也说:“只有将马永禄调走,来了新的书记,我们才会有希望。”“那路费、住宿等等可是不少的开支。”德才吞吐着说。“那不用你操心,只要你将钱用到刀刃儿上,用多少钱你就开口,既然都到了这一步,面粉厂倒闭也得向前迈。”听了刘大齐这话,德才心中像点燃一团火,越烧越旺。
一个月后,德才又接到一份处理决定,还是让他交三提五统费及税款。只不过数额又有所不同。德才看到处理书后,当天就把复议申请书交到村主任刘二柱家。刘二柱考虑到非同小可,就在第二天把复议申请交到镇司法所。德才就在家中等待复议结果。
转过年一春没雨,人们再也坚持不住了。村中出现了一伙儿开始集资打井。他们一带头,村里人纷纷开始了集资,自己打深机井。这样,村中来了打井团队,在各个洼指定地点展开了工作……
生活是紧要的,德才在刘大齐那支来老婆几百块工钱,又向亲戚借了些钱也入了股份。这期间,德才耽搁下了上访进程,整天去地里忙着和人们打井,妻子和别的女人一样在家里和泥,团泥球,为打深水井做准备。
几个月的辛苦劳作,各洼的水井先后喷出了甘甜的地下水……接下来,人们开始忙着浇地,耕种……
9月的一天深夜,德才和妻子还在睡梦之中,突然屋门被踹开,窗门玻璃碎了一地。妻子听到响声,赶忙起来拉灯。只见一伙人闯进里屋,不出示任何证件手续,将德才从被窝中拉出来,推推拽拽地带走了……妻子赶忙跑出去喊人。但为时已晚,德才被揪到车上,汽车马上开走了。
一路上,德才在车上死活不穿衣服,不住地破口大骂……他一直被押送到县看守所。
德才从梦中被带到看守所,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是政府执行2000年第一号决定,就这样他在看守所住了15天。
德才从看守所出来,两天后的一晚上,他和刘大齐一起来到刘书正家。书正说:“看来只有向县里上访了,乡政府庇护村干部,不仅对村民上访充耳不闻,而且采取暴力手段。再给马永禄下最后通牒,如再不解决刘权贵的问题,休怪咱越级上访。”三人达成一致意见,这次会议开到很晚才散。
两天后,德才去政府向马永禄下达最后通牒。
马永禄见了德才,揶揄道:“你还找破律师调查,结果怎样?你告到中央也没用。我劝你还是回家安心种地。”
德才见马永禄仍是那副嘴脸,蛮不讲理,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这天马永禄耐性极好,一点不急,任凭德才怎么骂,怎么指手画脚,他都无动于衷。
德才耍够了,也闹够了,一直到傍晚他才气愤愤地蹬车往家赶。
走在回家的路上,夜色降临,马路上来往的车辆瞪着两只贼亮的大眼睛如恶魔般急速穿梭。德才紧靠马路边,借着汽车的灯光慢慢前行。
走出政府大约一公里,后面突然追来三辆摩托车。他们赶到德才的前面,停了下来,将其拦住。德才刚从车上下来,来人不由分说拿手中的棍棒向他扑来……
等德才醒来后,不知是什么时间,也不知自己在哪里,脑袋隐隐作痛,用手一碰,满头是血……他慢慢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坐在马路边休息了好一会儿,然后狠咬牙推着自行车借着夜色一瘸一拐朝附近一个村子走去。
来到村子,德才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开亲戚的大门。这是德才的叔伯妹妹家。妹妹及妹夫费了好大的劲才辨认出德才,才将他让进家门。妹妹一边忙着给他上药,一边惊慌未定地询问他的遭遇……
等德才回到家,已到了后半夜。
德才躺在家中养伤暂且不提。在德才被打伤第二天,刘大齐的面粉厂因缺少证件经营被罚款。刘大齐问执法人员:“厂子一直合法经营,这么多年都按时交税,从未被罚过款,这次怎么会……?”执法人员说:“民不告官不究,你得罪人了,我们只是在履行职责。刘大齐一下想到了刘权贵,“别人怎么能有这个能耐?”
过了十多天,公安人员又来刘大齐面粉厂索要证件。刘大齐因拿不出所要的那么多证件,又一次被罚款,并且封了厂子。警车一走,刘大齐和老婆立即将门上的封条撕掉,并且当众大骂刘权贵,斗争形势进入白炽化状态。
黑道的突然袭击,让德才猝不及防,这对德才打击不小。德才在家养好伤,就来找刘书正,请他写材料。刘书正搞建设,搞外交并不怎么样,可对写材料却很内行,戴着大眼镜,手握钢笔记下德才近几年上访经过以及所遇到的遭遇。
与上次间隔二十天左右,公安人员再次来到刘大齐的面粉厂,进行第二次查封。这下将刘大齐全家惹急了,当着执法人员的面撤掉封条,并骂他们官官相护,为刘权贵当狗。开始执法人员非常客气,说只要不要再纵容德才上告刘权贵,刘权贵也就不追究他的厂子,让他安心经营。可刘大齐的老婆及女儿越骂越凶,并且当他们的面撤掉封条,这下他们就不干了,用手拷将刘大齐老婆及女儿拷起来,推上了车。刘大齐六十岁的人,患有心脏病,见女儿和老婆被拷起来,一下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的二儿子一看事闹大了,赶紧给公安人员跪下,请求放了她的姐姐,让她留下来照顾父亲。执法人员见要出人命,就放了刘大齐的女儿,带他的老婆离开了。这样,儿子和女儿赶紧叫车将刘大齐送往医院……
有了这几眼深水井,人们秋收有了保障。人们忙完农活,紧接着秋季征收开始了。
刘大齐从医院回到家,呆了一个来月,就病死了。德才与刘书正说,刘大齐是被刘权贵活活气死的,必须为刘大齐伸冤。德才处理完刘大齐的丧事,带着材料去了县政府。
在县政府办公室,德才见到一位姓郭的副主任。他听了德才详细叙述,深表同情,他让德才把材料留下,他们研究研究,让他回家听话。
这期间,人们黑白躲到庄稼地,任凭乡工作组在大喇叭怎样广播,人们就是死活不回家。一周后,政府工作组撤退了。
刘大齐已死,德才从被打后一直没有去政府闹事,刘权贵的气势一下又盛了起来。他开始在大喇叭广播起来,一张口就骂骂咧咧,一连广播了两天,锁门的依旧锁门,人们仍是无动于衷。后来他便点名破口大骂起来……
这下激怒了人们,被点到名的人,都来找德才,推选他当首领去找刘权贵。得到人们的尊崇与信赖,德才倍感激动,带领几十口人手拿农具迅速赶往大队部……
刘权贵正在谩骂,听门外有人大吵大闹,见势不妙,急忙从大队部出来翻墙,跑回家。
有十几个带头,胆小的也跟了上来,这样人越聚越多,一起拥进刘权贵的院中。
刘权贵见势不好,慌忙从屋里跑出来,顺梯子爬到房顶上。他从房顶拿起半个砖,举过头顶,威胁人们:“不怕死的就上来!”
这下没有人带头上房了,众人一下被镇住了。但人们没有退缩,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下来。
后来,刘权贵的老婆从屋里走出来,哭哭啼啼地央求大伙,如果大伙再不退出,她就要给大伙下跪。关键时候就得有人出面调和,这样一来,众人心软了下来,纷纷从院中退了出来。
第二天,刘权贵携妻儿离开了村子。
后来,人们得知,刘权贵搬到政府附近的商业街上,在那里租了房子,做起了生意。
从此,刘权贵家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再也看不到前呼后拥的小轿车了。偶尔他的儿子回来,但在家待不了多大会儿,就又悄悄返回去了。
刘书正说,这下不好了,人们有事就得大远小远地往镇上去找刘权贵,与他有矛盾的去了也白去,他把咱们又整治了。他劝德才再往县里看看。正当德才准备再次赶往县里的时候,听人说大洼乡党委书记马永禄被调走了,乡里来了位姓张的书记,他就没有急于去县里,停下来听听新任书记有何动静。
过了十多日,张书记开车来村子走访调研,在大队部与村中老党员进行了座谈。德才借此时机,将他上访的经历以及遭遇向张书记详细说了说。张书记说,早已听说了他的事,今天下来一是向党员们落实一下;二是在村中暂时找一位书记代替刘权贵。众人听说要将刘权贵撤下来,一下子兴奋了好一会儿……兴奋过后,人们都不解地询问,刘权贵根基那么深,背后为他撑腰的大有人在,他怎么会就这样被轻而易举摧毁了呢?张书记说:“他已被你们赶出村子,村子人们容不下他,为他撑腰的人再多有什么用?”最后经党员一致推举,刘书正继续担任大刘村村支书。
临走时,德才问张书记马永禄现在怎么样了,去了什么地方。张书记说:“大洼乡政府打官司败诉,在县里市里引起强烈反响,马永禄降职到县民政局去上班了。”后来,德才带着村里及乡里开的证明,去了县民政局,真的见到了马永禄。据德才说,马永禄不像从前了,绵羊了,见了他点头哈腰,一点也没有难为他,为他办理了六百元贫困补助金。
刘权贵被彻底扳倒了。村中人一下子掀起了热潮。德才在村中的威望高了起来,从此他走在大街上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的名声在外,无论走到哪儿,都向人们讲诉他上访的经历……
第二年,农业税全部免缴,村中人欢天喜地,再也不用为缴农业税东躲西藏了。可村中依旧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为此老书记刘书正整天忧心忡忡。德才怕遭到刘权贵再次打击报复,出门便随身携带匕首以防不测,活得也并不轻松。
后来,刘书正对德才说:“虽然你扳倒了刘权贵,胜利了,可你并没有征服他。他现在已没脸回村子了,恐怕祖孙三代都抬不起头了!你也就与他结下了死仇,以他的性格,我可断言他总会寻机报复,斗争仍在继续。”
“那又怎么样,咱不怕,这都是让他逼的。”德才一下被触及到伤痛之处,无奈道。
“人活着是来征服人的,不只是为了战胜,战胜他只能与他成为仇人,征服他就不一样了,很可能与他成为朋友。”刘书正富有哲理地说。
“怎么征服?总不能将他赶跑了,再去找他求饶下跪吧?”德才不以为然道。
“不至于那样。现在他买卖兴隆,发了大财,也不缺钱花了。可就是没脸回家了,我想给他个台阶下,找找乡里,把他叫回来继续做大刘庄书记,毕竟他是个人才。”
“如果他不领情呢?”德才问。
“咋个不领情,他总不能一辈子不回村子吧?死了也不往家里埋吧?”
“再让他当书记,总得有条件吧?”德才问。
“当然有了,不给村子办事,叫他回来干嘛?如果他肯回来继续做书记,并且答应人民群众的条件以及对他的监督,将你们这些年的矛盾化解了,这样才叫将他征服……”
第二年春天,一条水泥马路如一条被驯服的巨大蟒蛇由南向北蜿蜒盘踞在村子正中,街道两旁每隔一段距离都安上了路灯。每到晚上,灯光将整条街道照得亮如白昼,人们走在大街上,无论看哪里,都是清清楚楚的。
这一年,不知怎的,老天变了脸,雨水一场紧接着一场地下,人们来不及下地务农庄稼。地里的玉米,一改往年死沉沉的容颜,仰望着老天,露出得意的笑容,卯足了劲拼命往高里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