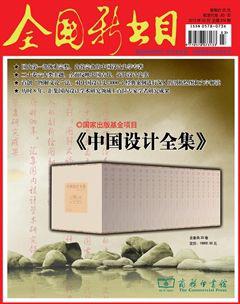我为什么写一本书叫《蛋壳里的北京人》
《蛋壳里的北京人》面世又是一次毫无准备的上路,直到把书稿交给出版社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生命中却总是有一些未知的呈现让你慨叹不预设的欣喜。喧嚣春节期间上市的《蛋壳》却默默地孵化出了高品质的读者,二月份北京图书大厦的销售排行它已悄然蹿升到了第四名,三月份当当网文化类图书已升至第三位。
这本书历时四年,从2009年集中采访到2013-1月成书出版,期间经历了工作上,身体上乃至家事的起起伏伏,包括我所负责的电视节目的革新,包括亲人的故去……可以说是耗时良久,也耗费了大量精力——既钻了故纸堆,也坐了冷板凳,最终结果不敢说尽如人意,但总算无愧己心。
《蛋壳里的北京人》里写了大量跟古建筑有关的东西,作为一个建筑的门外汉,自然不敢夸口对古建有什么精深造诣。但因为个人的兴趣,多年来积攒了很多北京古建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此外作为一个传媒人,我意识到这种情绪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多年来一直试图寻求一个带有共鸣性的出口,在多方尝试后最终落脚于古建筑。原因很简单,但事实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总之采访之前的案头准备和公关外联也是不小的工作量。但本着“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工作原则,我以决心和诚意争取到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采访。
就在《蛋壳里的北京人》面世前后,华新民来电相告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父亲华揽洪在法国去世了;上周,拿到新书的单士元女儿单嘉筠在电话中告诉我,90多岁的马旭初老人已不能下床……望着这座城市仅有的活化石默默地在物质化浪潮中一点点风化,虽心有不甘却徒叹奈何。
总之,我想,当每位读者翻开本书时,不仅是我个人在与您交流,还有一群人在诉说他们的心声,而这种倾诉本身就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
希望读者诸君能与我和“我们”一同对话。
蛋壳是为了包裹生命体而存在的。它是完美的、精致的,也是脆弱的、易碎的。有的人可以轻易击碎它,有的人则会精心呵护,把它看得高于生命……
蛋壳的比喻也并不罕见: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
假如把建于精神之上的北京城比作一个完美无缺的蛋,一个具有精神物象的生命体,那蛋壳就好比城墙,蛋清就好比九经九纬的棋盘街、四合院,蛋黄就是紫禁城。如果包裹生命体的蛋壳被打碎了,只留下化石一样孤零零的紫禁城,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找寻这座伟大城市的生命体征?
在这个物质和精神强烈对撞、剧烈撕扯的城市里,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有自己的阵营。所以,我们不无悲凉又不乏希望地说:每个文化人心中都有一个精致而易碎的蛋。
也许就是那只蛋。它在遍布全国的摧枯拉朽的造城运动中,这不仅是北京一个城市的疑问。它更像是中国的缩影,而对于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新移民”,这样的描述和思绪令他们感同身受,说出了笔下无却又人人心中有的况味。很多北京土著感叹:“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到北京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美丽和故事,王春元这个‘外来户让我们这些老北京汗颜。”
而对没有生活在北京的其他中国人,这无疑是一个瞭望和触摸北京的渠道,因为北京从来就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更是全体中国人的北京;
对外国人来说,这更是带领他们看中国的一个指南,因为对很多老外而言,北京即是中国。
总而言之,《蛋壳里的北京人》在尝试打开北京城内在精神气脉的途径,它给出了你“为什么要生活在这座城市?”和“爱上这座城市”的原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