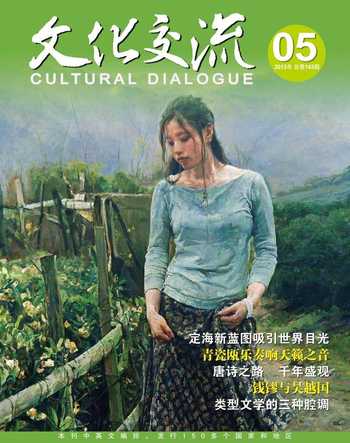周世义:山重水复中国心
鲁娃

浙江人周世义是商人,也是画家。商人是歇下来的商人,画家是从未专业过的画家。周世义的客厅里堆满了画,有世界名作的拷贝,也有自己的画作,还有他绘画习艺的心得随笔。他穿着休闲的衣装,在他巴黎奥斯曼经典建筑的豪华公寓楼里放下画笔,然后从漆成深红色的老式电梯里上上下下。
周世义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之路,甜酸苦辣的滋味足够用余生来回味了。
一
周世义与潘笑黎结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他俩都在浙江温州。笑黎的“黎”是后来团聚巴黎时改过来的,是周世义送给新婚太太的礼物,够浪漫。
周世义是“老三届”。初中毕业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通知书都已攥在手里,不料“文革风暴”起来,学校统统关了门,便没进学校。后来很多人去了广阔天地,只有他,因为父亲在海外,农村也不接纳,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打点零工。
邂逅在街道企业上班的潘笑黎时,他离乡出国的心意已定,可潘笑黎不允。周世义难以割舍纯洁的姑娘,一遍遍徘徊在门前幽暗的灯影下。有一天,他推门而入,把两张去上海的轮船票往潘笑黎手里一塞,说出不出国随你,先陪你妈妈去看看外面的天有多大。船进吴淞口,船长递来一封信,说是周世义托他转交的。潘笑黎拆开来读,满纸赞美上海的诗情画意。姑娘不傻,当然明白周世义的醉翁之意,下船一看,外边的世界也真是大,真繁华,排斥“走出去”的意志就软了下来。
周世义再接再厉,天天上门教潘笑黎学外文,一副胸有成竹的家教模样,实地里也就初中生的ABC,学着学着索性拽了女友出去“压马路”。那时的“压马路”是谈恋爱的唯一形式,“压”晚了,饥肠辘辘,兜里又没几个钱,就买两只大饼,周世义一口咬下一大块,潘笑黎腼腆着,心里却怨他小气,一拂手,大饼掉在地上滚成了铁饼。
但是,周世义的鸳鸯蝴蝶梦还是成了,潘笑黎不仅成了贤惠的太太,还与他前脚后步到了巴黎,开始有声有色地闯荡世界。
二
周世义来巴黎是1974年,他24岁。笑黎则晚了两年。
他父亲周老先生原是香港远洋轮上的海员,后来辗转到了法国做餐饮业,据说肩负着中法关系解冻前的特殊使命,因此身后享有盛誉,而初来乍到的周世义对餐饮业没有兴趣,他来是要画画的。没处摆弄他的画笔,就混了个打造漆器的营生,在一些家具摆设上描绘花虫鸟鱼,虽不是高雅的艺术,毕竟也沾了点边。三四年时间不算长,却足以让周世义从幻想的天际跌落到俗世尘烟中。
等潘笑黎追随而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妻子之后,他的小舟不再独桨单臂,就在巴黎三区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宇宙皮件公司”,制造、批发一体。格局还是温州人的格局,他的优势在于有捕猎般的一双眼睛与手中握有的那杆画笔,不用请专业设计师,层出不穷的新款图样就在自己的设计思维翻飞,出其不意地跳出来,看着顺眼,做出来十有八九就好卖。那会儿的时机又好,巴黎绝对是一个时尚消费的大都会,他的店门口动辄就是一条长龙,都是零售店的采购员,各式人种都有,就像世界风云际会。
当然也会有眼花缭乱灵感短路的时候,他一条道走到底的顽固与执拗就上来了,觉也不睡,即便上了床也要爬起来,就在窗前桌后坐着,两手托腮,苦苦冥思。月光照进来,在他的脸上晃,蹙起的眼眉就阴晴不定。一坐坐到天亮,阳光洒了进来,他笑了,疲惫中的丝缕的快慰。或皮包,或皮带,或别的什么新皮件,转弯抹角的难题解决了,柳暗又花明。所以他很牛,自信没有过不去的坎。
第一桶金打捞上来,金灿灿的耀眼。他转而又开出批发、制造之外的零售店。不开则已,一开就开了三家。一条命名为“宇宙”的周氏销售链得以在巴黎伸展。
三
有了钱的周世义是踌躇满志的。他穿戴齐整,出出进进于社团,尽着一个海外游子的本分。那时温籍侨团只有一个华侨俱乐部,他是从不言退的中坚力量。心系华夏情牵故土,生性又决不吝啬,那游子的本分就越来越多地聚焦在集资捐款上。
温州大学筹建初期,海外捐资的七幢教学楼,在法国的温州人捐了三幢,有两幢系两位老一辈侨领所捐,余下那幢就是周世义率俱乐部成员集的资。
原本闭塞的家乡要建机场,这是多好的事啊,自然又是一呼百应。金温铁路启动那会儿,他在温州,又恰在市长的车中,虽然囊中稍有羞涩,还是捐出一个月收入5万法郎。市长当即提出机关人员捐出月工资的倡议。
其实那些年周世义不算真有钱,真有钱是后来的事,所以他常鞭策自己,要让生意节节向上。立业固然是男人的为世之本,但他还有率性的另一面,他希望自己无论哪方面都是最好的,比如慈善义举。
到了1993年,听闻母校温二中要扩建校舍,他辗转反侧,一夜都是青春年少时的美好记忆。他想把这些记忆凝固成一个标志,留给后人的中学时代。他写信,打电话,后又专程飞了一趟温州,认资60万,捐了一座科学楼。那时的60万就是一座巍然矗立的教学楼了。回到家,周世义刻意低调地告诉潘笑黎,其实是怕先斩后奏挨一顿抱怨。哪知妻子比他还大手笔,只那么淡然一笑,“捐一座楼,好啊!”竟连多少钱都不问。
再后来,是2007年,周世义伉俪赶去参加温二中世纪庆典。前一天,从朋友家赴宴出来,妻子突然沉吟道,参加校庆,该带份礼物过去的。正中下怀呢,他趁机说,这礼要送就送大的,小的拿不出手哩。妻子说,大就大呗。他有点说不出口,“我想设个基金会,没100万恐怕拿不下。”妻子说,100万就100万。神态安恬如常。他反而愣怔得说不出话来,胸腔里涌动一阵阵热流,心中不禁叹道:“知我者,妻也;大气者,潘笑黎也。”
鉴于校庆110年,这笔基金又追加到110万,设立年度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扶助贫困学生。潘笑黎还是那句话,110万就110万。周世义从而捧回温州二中名誉校长的桂冠。
四
事实上,对母校的义捐、对母校的眷恋还有更深层的一个理由。周世义是特殊年代出来的初中生,错失了受教育的良好机缘。但他有三个很棒的孩子: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圆了他的梦。因而他自诩,这才是人生最大收获。
大儿子学计算机,法国大众银行的程序软件就是他设计的。这类职位保密度高,必须履行层层筛选与就职宣誓。小女儿自小学钢琴,3岁就被抱上琴凳敲击琴键,拜的都是高师名家。弹到18岁,突然改弦易辙,学了化学,再读物理学硕士,如今是娉娉婷婷优雅的大姑娘,在标致汽车公司做结构工程师。二儿子在父亲眼里更出类拔萃,法国名校硕士,又考了金融博士学位,在伦敦的美国花旗银行做部门“老大”。时下全球金融危机,他撂下工作就去了北京清华大学学中文,说要再度淬火……三个儿女都在法国出生,母语是他们的软肋,但父辈的爱国爱乡情结一直在熏陶着他们,他们始终都是中国的孩子。单说老二,“5·12”汶川大地震,他在伦敦不仅自己捐款,还向年轻的白领阶层募捐了数目可观的赈灾款。
虽然谁也不肯放弃专业继承家传,但周世义不在乎。只要孩子认准国门,他就无怨无憾。所以,他的基金会搁在那儿,多少也是对子孙后代的提醒与交代。
五
闲下来的周世义并不闲,日子满,心也满。满的日子满的心都属于中国。
返乡时,去医院探视外乡来的打工者,见病人患重病买不起药、拽着大夫苦苦哀讨廉价药方,周世义不忍,当即掏出三千块钱。病人亲属扑通跪下,拽都拽不起来。
到延安旅游,歇脚在黄土高坡的窑洞前。走进去,看见一对老头老太太坐在炕头,衣衫褴褛,面容干瘪,分明是半截子入土的人。洞里除了几串黄玉米几串红辣椒,家徒四壁。唠了几句家常,说是什么都没有,就坐等死了。周世义红了眼圈,摸出一沓钱递过去,老人烫手似的一挡,张张百元人民币飘落炕上,老夫妻抱头呜呜地哭,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还有一次在云南,路经孤儿院的门,看见一拨孩子可怜兮兮趴在矮墙上,满脸饥渴。周世义旋即推门而入,掏光口袋里仅有的八千块钱。院长闻讯赶出来,热泪涟涟地献了洁白的哈达。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即便已尽了力,周世义也没有任何快感,一颗慈悲的心总是湿漉漉涌动着潮热与苦楚,为同胞的贫穷难受。
汶川大地震,更使周世义悲哀心痛。次日,他凌晨四点就起了床,越洋电话打到乐清,说要捐20万赈灾款。电话打到乐清是因为他有房地产的两幢大楼还在那儿扫尾。可这电话委实过早,那边连赈灾的头绪都没理出来。接着又往这边使馆打,除了发动社团赈灾,自己还两头认捐。那一周的煎熬让他面容清癯,瘦了。他守着电视,茶饭不思,心一阵阵揪紧了。
真可谓山重水复中国心,悲天悯地性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