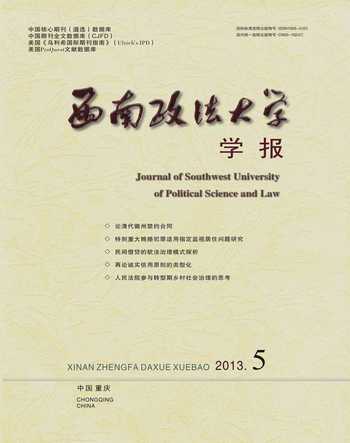《WTO协定》中“shall”/“should”词义实证研究
摘要:条约用语的意义模糊并非一个独立问题。通过对WTO案例的实证研究可知,“shall”与“should”在权威的公共英语词典和法律英语词典中都有多义性特征,由此导致成员方和争端解决机构对WTO诸协定中“shall”与“should”具有强制性抑或劝告性意义产生分歧,影响了WTO相关规则的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国际法本身的局限性、条约用语的含义可能会随上下文而变化、成员依据其利益对国际法规则作不断变化和不一致的解读、语言模糊性等。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可以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习惯法解释规则合理、准确地选择“shall”与“should”的恰当含义。二者既具有强制性含义又具有劝告性含义,如何在具体语境下确定其具体含义,尚未被不充分的条约实践和条约法规则所证实。
关键词:WTO协定;“shall”和“should”的含义;条约解释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囿于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法律英语、公共英语中情态动词自身的模糊性,“shall”与“should”在不同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究竟表示义务还是仅为修辞,会导致人们对法律条款理解和翻译中的困惑,增加了WTO成员基于自身利益解读涵盖协定的任意性以及争端解决机构专家解读的自由裁量空间,损害了WTO法应有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在法律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shall”、“may”、“must”、“should”,就翻译而言最困难的是“shall”。但是,“shall”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是构成独特的英文法律文体的一个最主要的辞汇[1]。“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中,‘shall一词可谓俯拾即是,多达3000余个……考虑到‘shall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因此需要找到一个统一和固定的译法,……。”[2]还曾有人统计过,“shall”在美国《联邦宪法》中出现了304次,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出现了310次。学者Frederick Bowers指出:情态动词“shall”被广泛运用于法律英语的主要原因是“shall”被看作是具有法律权威的一种象征。参见:Frederick Bowers.Linguistic Aspects of Legislative Expression[M].New York:Macmillan,1989;施蕾.法律英语中的情态动词shall及其翻译[J].工会论坛,2008,(2):122.
笔者在对《WTO协定》文本及相关判例的研究中发现,“shall”在法律英语中的含义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选择问题,不仅涉及到语言哲学对语言模糊性问题的研究和争论、(法律)英语语言学领域学者间的分歧,还直接涉及涵盖协定中相关规范内容的法律效力问题——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问题。迄今为止,WTO专家组/上诉机构相关案例尚未澄清如何确定“shall”和“should ”间的联系与区别,其多义性常导致对相关协定的含义在理解时出现分歧。条约的特点、法律的特点都导致了其规则的静态性、抽象性,同时,由于规则所使用的语言的限制,非母语国家或地区在准确理解规则用语时存在困难,即使是在规则所用语言为其母语的国家,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文化的影响,对规则用语含义的理解也会产生歧义。语言本身表达的不完善性导致对规则进行解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为了达成谈判,谈判者故意使用了模糊的字眼,形成“建设性的歧义”[3]。因此,在语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WTO案例实证研究以揭示其含义及应用,减少理解、适用和翻译中的困惑,避免英汉互译中的失真和对语义的曲解甚至滥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shall”和“should”的含义国内有学者对“shall”和“should”的译法作了研究。“在1995年译本”中,“必须”与“应”混用,显得十分混乱。“须”与“需”同音,且语气非常强硬,中文中使用该词的语言环境非常少,如果将乌拉圭回合协议中几千个“shall”均译为“必须”,未免使中译文过于生硬,中国的法律条文也很少使用,而是通常使用“应”、“应当”和“应该”等表述。因此重译最终将“shall”译为“应”, “shall not”译为“不得”,“shall be free to”译为“有权”。与此有关,“should”也译为“应”,“should not”译为“不应”。(参见:索必成.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的中文翻译[G]//陆文慧.法律翻译——从实践出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01-302.) 从法律规范意义上说,对“shall”的研究,其最大意义在于确定相关规则的法律效力,即是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这是研究该词语的实质意义,至于如何选择恰当的汉语词语来表达其不同意义,或许仅具形式意义,与语言习惯有一定关系,关键问题是人们能否分辨出其法律效力含义的不同,而非语气之强弱。West公司出版的《布莱克法律词典》目前是法律领域最权威的工具书,在美国被誉为法律界的“圣经”,该词典对“shall”的含义有5种解释[4-5]: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冯寿波:《WTO协定》中“shall”和“should”词义实证研究1. Has a duty to; more broadly, is required to.
2. Should (as often interpreted by courts).
3. May.
4. Will (as a future-tense verb).
5. Is entitled to.Preston M. Torbert mentions that “Shall” can express “anticipation and determination” (Preston M. Torbert, 2006: 110), “rhetorical emphasis” and “obligation”. Apart from these, “Shall” could be further used for expressing the order, obligation, responsibility, right, privilege and commitment.
“虽然‘shall在法律英文中有许诺的意思,但是从大量的法律条文的用词习惯上看,‘shall的主要任务是强制某人做某事;况且,许诺并不等于许可。”[1]57但在法律英语中,出于法律确定性的特殊需要,“shall”的含义有限,不同于其日常用语中的诸多情态意义。对该词含义选择方面存在的主要争议是在特定上下文中(非)强制性含义的确定,以及 “should”是否可指强制性义务、如何判断。当“shall”与“should”表示有法律约束力的含义时,与“must”的意义基本相同,可译为“应当/必须”,以与“should”的非强制性含义“应该”区别开。至于第3种含义,“shall表示准许、许可,与表‘义务截然相反,例如,‘Such time shall not be further extended except for cause shown.其否定式‘shall not表示‘不准、不许之意,事实上此处‘shall等同于‘may。在英文法律文本中经常会看到‘No person shall…这一结构,但逻辑上存在问题,正确的使用应该是‘No person may,因为此处是对‘许可的否定、禁止,而非针对义务而言。……‘shall表达一种权利而非义务。例如,‘The secretary shall be reimbursed for all expenses.……就连英美国家法律工作者也不能完全正确使用‘shall一词。”[6]“现代英语法律和合同条文的主句成分中的‘shall,在汉语中有很多种译法。通常被译成‘须、‘应,有时被译成‘应当,也有时译成‘要、‘将、‘可,还有时被译成‘必须,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译。”[1]54此外,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得”在台海两岸立法语言中的基本用法——“在立法语言中这两个‘得有着显著差异,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是:第一,表‘可以的‘得原来表示授权,而表‘应当的‘得用来设定义务;第二,‘可以往往意味着‘可以不或‘可以其他,而‘应当则意味着惟一的指引。”[7]
《兰登书屋法律词典》(Random House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Law) 对“shall” 的法律解释有以下三项[8]:(1)在特指法规或司法解释中,表示命令、必要性和强制性(expressing mandate, necessity or compulsion, especially instatutory or judicial directives);(2)表示决心、肯定和强调(expressing determination, certainty and emphasis);(3)表示计划、意愿和预期(expressing futurity, especially plan, intention or expectation)。
专门研究法律英语中“shall”等情态动词应用的研究者关于“should”含义的研究结论为:“In summary, Should is used to represent obligation in general and moral sense.”[5]36也有学者认为:“‘should虽然在法律英语中经常使用,但主要局限于各种合约(尤其是销售合约)条款的条件句中,其作用相当于‘if,但表达的是一种虚拟状态的条件,一般可译成‘假如、‘尚诺或‘如果。”[1]54但在1999年加拿大-影响民用航空器出口措施案中,上诉机构根据公共英语词典和专业法律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larendon Press,1995,p.1283;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Clarendon Press,1993,Vol. II,p. 2808;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1990,p. 1379. 确定了“should”的含义:“通常隐含着责任或义务,尽管通常仅指礼节上的或权宜的义务,或道德义务,据此以与‘ought区别开来。”WT/DS70/AB/R ,2 August 1999,para.187 and footnote 120. 不过,对“should”究竟是否以及何时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含义,上诉机构在此语焉不详。“shall”与“should”都具有非强制性的劝告性或道德期待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shall”在具体法律中的用法究竟是完全表示义务还是有修辞性质,并不是很清楚。结论为:(1)“shall”表示“义务”和“责任”时通常被翻译成“应当”、“应”,有时则不译;(2)“shall”用于表示“决心”、“肯定”和“强调”是为了增强法律语言崇高、庄严的意味,主要起修辞性的作用,用 “shall”或者用一般现在时态没有本质区别;(3)“shall”在法律文本中很少表“预期”[9]。
“但某一用语的字典含义并不等同于其在规则中的通常含义。由于字典的功能在于提供最一般的非专业意义的含义,其具体用法未必与经过谈判使用的规则用语相符。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尽管在解释中离不开字典,但不唯字典。”[3]223WTO法律专家对其含义的确定需要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予以澄清,包括对该词语的通常含义、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条约序言、嗣后惯例、谈判历史资料等解释要素的综合衡量与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二、WTO争端解决机构中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解释WTO案件裁决报告的长度动辄数百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专家组/上诉机构对WTO规则含义的准司法解释,其中,某些案例涉及“shall”和“should”的含义辨析。
(一)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含义是“shall”与“should”的主要区别
在欧共体关于肉和肉制品(荷尔蒙)案的专家组报告中,曾将是否具有强制性作为区分“shall”与“should”含义的标准:“第4段(该段非强制性)和第5段(仅是将要通过指导方针来实施的一个目标)试图对成员实施其已确定的保护水平自由设置某些限制。换句话说,它们应该(非应当)考虑到使对贸易影响最小化的目标和应当(shall)避免在水平方面的任意的或不合理的区别,如果……。”WT/DS48/R/CAN,18 August 1997. 由于凭借第5.4条用语的指引,尤其是“应该”(非“应当”)和“目标”,专家组认为,《SPS协议》中的该条款并没有施加一项义务(impose an obligation),尽管如此,使对贸易消极影响最小化的该目标无论如何在解释《SPS协议》的其他条款中必须被考虑到。此处,专家组将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shall”与“should”的最重要区别。
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税收待遇案中,专家组认为,该1981年谅解并没有以通常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之特征的命令性(mandatory)语言来表示。该谅解使用了诸如“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export activities”和“should for tax purposes be”这样的词语,此处人们或许期待一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使用“shall”这一词语。该谅解并没有以人们可能期待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明确方式表达出来。WT/DS108/R,para. 7.65. 可见,该案的专家组认为,“shall”应当是上述《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第1个解释(Has a duty to;more broadly, is required to),而“should”不具有强制性含义。但是,该案的上诉机构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上诉机构认为,“因此,我们分享专家组关于1981理事会单独行动(the 1981 Councilaction alone)的正文并没有解决美国和欧共体间相互冲突的争论中的模糊性。”“我们注意到,在该方面,我们没有分担专家组关于在‘法律文件中使用‘should一词的疑虑。我们认为,许多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使用了‘should一词,并且根据上下文,该词或许要么意味着劝告,要么表达一项义务。”WT/DS108/AB/R,para. 111.
在印度专利案的专家组报告中,欧共体认为,虽然印度政府在其国会或其他地方或许发布过声明,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下列事实:《印度专利法》第12.1条中包含了一项强制性规定,即当关于专利申请的完整说明已被存档时,要求管理员(controller)向审查者提交任何申请书。而且,如果在管理员看来说明书中所声称的发明根据该法并非可授予专利,该法第15.2条要求管理员拒绝该申请。这两个条款都含有助动词“shall”,该词并不允许管理员行使任何的自由裁量权。欧共体认为,此处两个“shall”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含义。此外,TRIPS协议第51条、第39.2条、第25.1条和第22.2条中的用语清楚地创设了授权行政部门采取具体行动的权力之义务……,这些词语中就包括了“shall”一词。WT/DS70/AB/R,para.4.19. 19 December 1997. 在该报告中,还有涉及“shall”与“should”之区别的段落:“考虑到它们的通常含义,DSU第9.1条的用语是指导性的或劝告性的,而非强制性的。这些用语表明应该(不是‘应当)建立单一的专家组。……就其本身而言,第9.1条不应该(should not)影响DSU下成员方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和义务。”该段表明了“shall”与“should”间含义上的主要区别。
2012年1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聚丙烯包装袋和圆筒织物保障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附件中,表明GATT1947第19条中的“shall be free”具有强制性意义,“……GATT第19条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确定了必须得到满足的一系列条件,旨在使某一WTO成员可以采取第2部分中描述的行动步骤。第19条的其余部分规定了采取该措施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程序要求和纪律。如果第一部分没有得到满足,该授权将不存在。”WT/DS415/R/Add .1,para 6,31 January 2012. “shall be free”后的“对该产品全部或部分中止义务……”既是该缔约方的权利,同时也是相关缔约方的义务;第19.2条中的4个“shall”具有法律义务含义。在该专家组报告附件(ANNEX B-5)第8段中,土耳其认为:“在该解释基础上,第9.1条规定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性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土耳其想强调的是,《保障措施协议》第9.1条中所含的‘shall一词为成员方将‘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于满足上述规定条件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一项义务。”土耳其在此主张第9.1条中“shall”的含义为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2012年1月美国-影响丁香香烟生产和销售措施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尽管专家组的论证可被解读为表明部长级会议或许可以无视《WTO协定》第9.2中的具体要求,但该款的用语并不表明对该要求的遵守是可有可无的。在该方面,根据《WTO协定》第9.2条的规定,我们忆及,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应当在监督该《协定》实施情况的理事会建议的基础上行使其对《WTO协定》附件1中包含的《多边贸易协定》的解释予以采纳的权力。我们认为相关理事会的建议是第9.2条的基本要素,构成了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行使其采纳对《WTO协定》进行解释的权力之法律基础。因此,对被包含在《WTO协定》附件1中的《多边贸易协定》的解释,在监督该《协定》实施情况的理事会建议的基础上,必须(must)被采纳。”WT/DS406/AB/R,para.254,January 2012. 也就是说,第9.2条中的“shall”使得相关规定成为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的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职责。还是在该报告中,上诉机构为了论证《多哈部长决议》属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a)条所规定的“当事方间嗣后订立的协定”的范畴,认为“协定”这个词语从根本上说是指实质而非形式。因此,如果《多哈部长决议》清楚表达了成员间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he TBT Agreement)第2.12条中“合理时间间隔”一词含义的共同谅解以及对该谅解的接受,那么,《多哈部长决议》就具有该公约第31(3)(a)条所规定的“当事方间嗣后订立的协定”的特征。在确定情况是否如此时,上诉机构发现第5.2段的用语和内容是决定性的。在这一点上,上诉机构注意到,成员间关于TBT协定第2.12条中“合理时间间隔”一词含义的谅解被“shall be understood to mean”这些词语来表达,这不能被视为仅是劝告性的(merely hortatory)。该段核心观点表明,TBT协定第2.12条中留出“合理时间间隔”由于“shall”的使用而对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法律语言中,‘shall与第三人称及第二人称连用时是情态动词,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特权、许诺等,其作用相当于‘must、‘be required to 、‘be to (do)、‘have to。检验‘shall在法律条文中是否用得恰当,可简单地用‘must去替代:如果可替代,则属于情态动词,是法律上的用法。虽然‘shall在语用上相当于这四个词或短语,但在实际应用中,其中‘must、‘be required to、‘have to的语气和强制作用比‘shall更为强烈。专门从事法律翻译的资深专家似乎在重要法律的翻译实践中逐渐达成共识,并正在约定俗成一条规矩:即让‘must以及‘be required to与汉语中的‘必须对等(‘have to基本上不在书面的法律英语中使用);让‘shall与‘须、‘应、‘应当对等。虽然在法律条文中‘shall的现有译法十分多样,但本文的分析已排除几种不恰当的译法,其中包括‘将、‘要以及‘必须等。”[1]59此处,该文作者还提出了一个识别“shall”是否具有强制性意义的参考办法。
(二)二词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含义
在一些案例中,专家组/上诉机构认为,“shall”与“should”都意味着责任或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税收待遇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尽管在口语中‘should一词常被用来暗示劝告或表明倾向,但是,该词并不总是以那些方式使用,它也能被用来表达责任或义务。例如,该词以前曾被我们在DSU第11条的语境中解释为专家组的一项义务。类似地,我们认为,第13.1条第3句中的‘should一词,在第13条的整个上下文中,是在规范意义上而非仅在劝勉意义上被使用。换句话说,根据DSU第13.1条的规定,成员对专家组向其作出的信息请求负有‘立即和充分反应的责任和义务。”WT/DS70/AB/R,para.187,2 August 1999. “如果被专家组要求提供信息的成员没有通过提供该信息的方式作出‘回应的法律义务,那么,该专家组根据第13.1条第1句规定的毫无疑问的寻求信息的法律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争端中的成员或许就会随意阻碍DSU第12条和第13条赋予专家组实情调查的权力并自行控制收集信息的过程。换句话说,成员或许会阻止专家组完成其调查构成争端事实的任务并不可避免地阻止专家组继续分析这些事实的法律特征。DSU第12.7条在其相关部分规定,‘……专家组报告应当列出对事实的调查结果、相关条款的适用性及其所作任何调查结果和建议所包含的基本理由。如果阻碍专家组查明争端中真实的或相关的事实,那么,它就将不能确定相关条约条款对上述事实的适用性,并将不能向DSB作出任何有原则的调查和建议。”我国商务部WTO法律专家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一书中也将第11条中的“should”翻译为“应当”,从而将其解释为具有法律义务含义。“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专家组应定期与争端各方磋商,……; 专家组应当对有关事项进行客观评估,……。”(参见:杨国华,等.WTO争端解决程序详解[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61.) DSU第13.1条规定:“每一专家组应当(shall)有权向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人或机构寻求信息和技术建议。……成员应当(should)迅速和全面地答复专家组提出的关于提供其认为必要和适当信息的任何请求。未经提供信息的个人、机构或成员主管机关正式授权,所提供的机密信息不得(shall)披露。”在日本农产品案中,上诉机构认为,DSU第13条和《SPS协定》第11.2条表明专家组拥有一项重要的调查权力。专家组有权向专家和其选择的任何其他相关来源寻求信息和建议。WT/DS76/AB/R,para.129,22 February 1999; WT/DS58/AB/R,para.106. 由此可见,根据DSU和适用协定的相关规则,“shall”与“should”在特定语境中都可指责任或义务。
在危地马拉对来自墨西哥普通水泥最后反倾销措施案中,在专家组报告的一个脚注中对“should”所具有的劝勉性或强制性含义进行了分析:“尽管‘应该(should)这个词语在口语中常被用来意指劝告,但它也能被用来‘表达一项责任(或)义务。由于第6.7条在相关部分规定附件1的条款‘应当(shall)予以适用,我们看不到存在不应该(should not)在强制性意义上解释附件1(2)的理由。我们认为,对附件中条款的劝告性解释应该与第6.7条不一致。而且,危地马拉人还没有主张附件1中的第2段仅是劝告性的。相应地,在该基础上我们认为附件1的第2段应当在强制性意义上予以解释。”WT/DS156/R,24 October 2000,footnote 854. 也就是说,根据《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和“should”的上下文情况,专家组得出该“should”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附件1第2段中应当解释成具有强制性意义的“应当”(shall),而非具有劝告性意义的“应该”(should)。
(三)“shall”与“should”都具有非强制性的道德义务含义
如上所述,二者都具有无法律约束力的道德含义。王宝川在其专门研究“shall”的硕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这两个情态动词都可具有道德义务含义。“Shall” is used to express obligation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it is sometimes replaced by “Should” for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ying dang”. The “Should” in English and “ying dang” only express a good morally wish instead of an imperative mood demanding someone to act. In this case, the priority is given to the discretion of parties, which also reveals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illocutionary act) of the statement someone observe a promise conscientiously.(参见:王宝川.论Shall在汉英法律翻译中的应用[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 2010.)不过,笔者在本文中将该道德义务含义译为“应该”,以区别于具有法律约束力含义的“应当”。 “shall 当作强制性较弱的should使用,例如,‘Any person bringing a malpractice claim shall, within 15 days after the date of filing the action, file a request for mediation.像此类句子,许多英美国家法院认为shall起的是指导性作用而非强制性作用。”[6]50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条约用语的意义模糊性并非一个独立问题,一些条约用语可能随上下文的变化而影响对其含义的具体选择。因此,“shall”与“should”含义的确定既需要依据权威公共英语词典和法律专业词典的界定,又要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条约解释要素来加以综合判断,其中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裁决即使不构成先例,也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引作用,并对案件当事方具有约束力。
(四)学者对TRIPS协议第7、8条中“should”含义的理解分歧
条约用语意义的模糊性会导致条约当事方权利义务的重大不确定性并引发争端,因此,条约具体规则与条约目的间的互动关系,已成为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有学者认为,从条约解释的角度看,与“必须/应当”(shall)条款形成对照,TRIPS协议第7条是一个“应该”(should)条款,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尽管该措辞的选择已导致某些工业集团和评论者认为该条款“仅是劝告性的规定”,其解释性价值与序言中的任何规定相当,但是,不应忽视该条款在协议中的位置。事实上,根据Gervais教授的观点,具有该性质的第7条被包含在协议正文中而非规定在序言中的事实似乎是为了提高其地位。其观点在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案中获得上诉机构的进一步支持:条约解释者应对涵盖协议中“实际使用的词语给予充分考量”[10]。第7条不可被用来减少其他条款中“必须/应当”(shall)或与此相当规定的范围,多哈文件并没有提升第7条的法律地位[11]。第7条使用了“应当”(should)一词进一步提醒成员,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一定带来更多创新、知识的传播或技术转让[12]。可见,围绕情态动词的差异与第7条的效力问题,学者间存在很大分歧。
尽管第7条中“应当”(should)与“必须”(shall)之间在语法上可能存在某种差异,但应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以及WTO司法实践,将其置于TRIPS的第一部分(总则和基本原则)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量,鉴于第7条规定的5个目标构成了整个TRIPS的法律基础,是解释、实施、发展TRIPS条款的路标,已构成国际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的重要内容,已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适用于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所有领域,而非个别领域的具体规则,WTO成员依据TRIPS所享有/承担的具体权利义务是建立在TRIPS基本原则体系(包括第7条公共利益原则)基础上的,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具体体现,是TRIPS具体条款的精神和灵魂。任何依据条约用语来限制、否认第7条效力或者曲解其本义的作法,是与WTO司法实践相悖的,因为“根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许多案件中的观点,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是对条约的‘有效解释,即条约中的每一个术语都是有意义的,不能随意忽略或者不予考虑;二是‘协调一致,即同一个条约中的不同条款相互之间只能是互补关系,而不会互相冲突。”[13]弗斯指出,一个词的词义随其所在上下文而变化,达罗夫也指出: 多义词的含义通常要通过言语的上下文来揭示[14]。笔者认为,既然条约序言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一些西方学者主张位于TIRPS协议总则和基本原则中的第7、8条的地位与序言中相关规定相同,果真如此的话,一方面,似乎可以得出TRIPS协议正文中根本没有必要再重复序言中已有内容的推论;另一方面,也是对法律基本原则之功能的曲解。
语境或上下文能限定和区分一词多义,因此,在解释第7条的含义及效力时,不应贬低或无视第7条的公共政策目标,把处于协议基本原则地位的第7条与协议的其他具体规则相提并论,更不应因为第7条本身的用语而否定其基本原则的地位与效力,甚至人为地、非善意地加以曲解,因为条约的善意解释是善意履行的前提。有学者把第31、32条关于条约解释规则诸要素间的关系概括为:“善意解释是根本原则,约文解释是基本方法,参照目的和宗旨解释是条约解释正当性的保证,使用准备资料是解释的辅助、补充手段。……Jeff Waincymer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曾指出,规避WTO协定的实质意义的一种严格的文本解释,是对善意原则的违反。”[15]国际争端在较大程度上是条约解释争端,本质上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国际(准)司法机构常陷于平衡利益与维护条约一致性间的困境,因为“各国会依据其利益对习惯国际法作不断变化和不一致的解读”[16]。WTO法律规则中存在的局限性离不开依据条约目标和宗旨、缔约方共同认可的价值进行判断、甄别、解释,同时,也不应忽视法律规则及其具体目的。
三、产生分歧的原因及问题解决(一)三个主要原因
1. “shall”在英语法律文本中用法的复杂性与混乱
如前所述,条约用语含义理解上的分歧原因之一在于法律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国际条约缔结谈判中为达成妥协所需要。“法律是模糊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致在特定案件中法律的规定常常不确定。……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虽然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模糊的,但是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必然包含模糊的法律。当法律是模糊的时,人们的法律权利、义务和权力在某些案件中(并非在所有案件中)变得不确定。……当法律是模糊的时,对某些案件的司法裁决将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官在原则上不可能总是相同案件相同处理。法律中的可预测性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可望而不可及。”[17]但在国际法中,模糊性可能同时也是利益冲突的各方就某一事项/协定达成妥协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如同许多GATT的规则,这种含糊的规定看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8]。条约用语含义理解中存在着分歧是因为“条约是谈判导致妥协以调解经常是广泛的分歧的产物。就多边条约而言,谈判国的数目越多,满足各方冲突利益的富于想象力的灵活起草的需要就越大。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不清楚或模棱两可的用词。尽管在起草时非常小心并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没有任何条约是不可能产生一些解释问题的。”[19]可见,语用模糊在国际条约谈判、缔结中具有相应的重要性,是一柄双刃剑。“模糊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产生模糊的原因与自然界本身的界限模糊不清有关, 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有关, 也与发话人讲究交际策略有关。模糊和精确是互为对立的统一体。在一定的范围内,精确方法是更科学的方法; 在另一范围内, 模糊方法则是更科学的方法。关键是使用要得体, 该精确的地方模糊不得, 该模糊的地方精确不得。当前, 对模糊现象的研究正在国内外广泛展开。”[20]“模糊语言存在于法律英语中有其特定的原因。从立法角度看,恰当地运用模糊语言,能有效提高语言表达的概括能力与正确程度,实现立法的科学性, 从而帮助人们以有限的立法资源应对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和法律行为;从执法角度看,模糊性的存在也给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再加上法律现象总是复杂的、 无限的, 因此有限的法律语言难以承载、 传递未知的法律现象。”[21]上述主客观原因决定了法律用语的准确性与模糊性并存。
2. 词语的多义性: 语言本身之不确定性
“在宽泛的意义上,模糊性被视同歧义性。歧义性规范是一种框架,在这一框架之内,该规范表达的意义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通过使用一种歧义性表达,立法者授予法院自由裁量权,让法院有权在那些意义中作出选择并进而形成个别性规范。”[17]22抛开“文本的语义可能是除它当前看似的东西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17]22这个论断的哲学合理性基础,似乎可以窥见其所表达的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生命力。英语词语本身的多义性、句法等都可能造成法律解释中的困难。如前所述,“shall”与“should”都有两个以上的含义,都可以表示劝告性意义,又可以表示法律中的强制性意义,在一些情形中,人们并不清楚其是在那一种意义上被使用,而对这些不同含义的理解、选择,将直接涉及到WTO成员诸协定项下权利与义务的确定以及专家组/上诉机构对相关争端的依法公平裁决。因此可以说,解释也就是一种语义选择行为。
3. 解释者忽视条约目标和宗旨的作用
条约和构成解释条约的诸要素都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特征。对条约上下文的不同考量也会直接影响对“shall”与“should”含义的选择和确定,这是因为条约词语的意义与其使用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同一条约内部以及不同条约之间存在冲突、漏洞、模糊等现象并不少见,因此,法律解释问题在国际条约中更具重要性与复杂性。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条约解释的通则之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具有之通常含义,善意解释之。”即应从通常意义上来理解条约用语,“通常意义的确定不可能抽象地进行,只能根据条约的上下文及其目的与宗旨而予以确定。……在实践中,考虑其目的与宗旨更多地是为了确认一项解释。如果一项解释与该目的和宗旨不相符合,它很可能是错误的。但第一项给予文本解释以优先地位。”[19]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是全面考察该用语的上下文、条约的宗旨和目的后得出的。应当考察的内容包括:条约约文、序文和附件[22]。Arthur Watts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强调,第31条是一个‘完整不可分的合并的(解释)操作方法”[15]146。Anthony Aust也认为,第31条名为“解释之通则”,该单数名词形式强调该条只是包含在第一项中的一项规则。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条约解释中的三个主要因素:条约约文、它的上下文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解释条约时人们自然地是从约文开始,随后是上下文,然后是其他事项,特别是嗣后的资料[19]203。李浩培先生指出,国际法委员会认为条约解释程序是一个统一体,从而第31条的各项规定组成一个单一的、互相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完整规则[23]。第31条第1项规定的诸解释要素之间“并没有法律效力上的优劣或上下等级之分”[15]23。此外,公约第32条对约文解释方法规定了谨慎的限制:如果依第31条规定的解释方法“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二)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简明英语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法律文本中shall的使用也呈逐渐减少趋势。”[24]但WTO协定英文本是客观存在,必须重视对其中“shall”与“should”的研究,以努力实现翻译中“信”的目标。
1.专家组/上诉机构解释条约所遵循的规则
条约的解释是为了确定缔约方间的权利义务,以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一致的方式解释具体规则,将有助于加强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为了确定哪些语境因素或上下文和该表达的使用有关联,DSU第3.2条要求争端解决机构“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协定的现有规定”,这或许就是凯尔森、罗纳德·德沃金眼中法律用来防止漏洞的各种资源的一部分,同时为争端解决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划定理性的边界。因此,WTO协定的解释应遵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的规定。鉴于DSU第19条的规定,尽管语境自身可能具有无限性,但DSU第3.2条为专家组对具有语境依赖特征的词语意义的选择确定了具体的考量要素,其中包括了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对确定用语含义的作用。对“shall”与“should”含义的准确确定将直接涉及到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是否正确履行了其职责以及其建议的准确性和合法性,特别会涉及到是否变更了协定项下所规定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WTO中脆弱的政治协商一致只允许WTO司法机构在进行解释时保持司法克制,严格按协定的规定进行解释,这是《WTO协定》和DSU所确立的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神圣原则。WTO并不具有司法能动主义的政治性协商一致。……WTO上诉机构的司法能动主义面临着成员方的强烈政治控制。WTO司法机构为了使自身裁决获得成员方的支持,不能越权解释……。”[25]成员方应重视争端解决机构对《WTO协定》文本含义的解释。关于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本文来说,即对“shall”与“should”含义的解释与确定,直接关乎成员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和WTO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当然也将会对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公信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作为《WTO协定》解释规则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也不能消除所有条约用语的模糊性,其本身甚至就可能存在着模糊性。
2.注重个案分析方法
由于“shall”与“should”均具有一词多义性,因此,在特定语境中其含义的准确选择便需要明确的适用规则,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还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均未在公约中/准司法实践中对此予以明确,因为尚不充分的准司法实践还难以明确问题,需要个案分析处理。
现以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中争端解决机构如何通过个案分析方法确定“shall”的含义来观察“shall”的含义选择与对具体法律上下文的依赖。“专家组认为,从第6条第10款看,给予单独待遇是一项原则,而抽样是惟一例外。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的这一认定提出了两个解释性问题:一是关于确定单独倾销幅度,第一句的‘shall和‘as a rule是表明了一项强制性规则,还是仅仅反映了一种偏好;二是第二句所允许的抽样,是否为第一句所设定规则的惟一例外。上诉机构认为,助动词‘shall在法律文本中通常用于表示强制性规则,而‘as a rule的含义则是‘usually,‘more often than not。‘shall和‘as a rule结合起来,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偏好。如果该款的起草者意在避免设立确定单独倾销幅度的义务,则可能会使用‘it is desirable或‘in principle,而不是‘shall。尽管‘shall一词设定了强制性规则,但这一义务却受到了‘as a rule的限制,而这一限定必然是有含义的。上诉机构认为,这个词表明此项义务并非绝对,预示了例外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词,确定单独倾销幅度的义务就无法与《反倾销协定》中背离这一规则的其他规定保持协调了。”[26]
3. 加强对WTO案例的研究
“法律的模糊性不等同于法的不确定性,也不等同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强调法的模糊性和合理利用法的模糊性走的是一条与传统法学精确化道路完全相反的路径,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系统——‘模糊法学。模糊法学在立法、司法及部门法学中有广泛的应用价值。”[27]此一说法肯定了语言模糊性这把双刃剑的一端。尽管WTO相关案例裁决的结果仅约束该案的当事国,但实际上,专家组为了其裁决报告不被上诉机构所推翻,常常会引用以前的专家组报告中的法理分析和相关结论。我国应密切关注未来WTO争端解决机制出现的新的法律解释。WTO争端解决的个案是直接依据DSU和其他适用协议作出的权威裁决,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体成员方对于DSU和其他适用协议的普遍理解和认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会根据具体案件不断对WTO协定的各条款作出解释,甚至有可能就同一条款作出新的解释,从而推翻旧的案例[28]。对此,我国应当随时把握争端解决中的新动向,并对国际贸易争端中相关成员以法律的不确定性或对该成文法用语的不同解释为借口而规避国际条约义务的作法保持警惕。
四、结语很显然,在翻译上值得探讨的法律英语中的主要情态动词是“shall”,“must和may”在本文中只是供作比较的情态动词,在普通英文中的用法和译法与在法律英文中没有太大差异,而“shall”则不然,它在普通英文中较少使用,在法律条文中用得极广,这是构成法律英语主要特征的关键字[1]59。“shall”是法律英语理论和实践中最复杂的一个情态动词,该复杂性主要源于其本身易产生歧义的表意缺陷。理解“should”含义的难点在于其强制性含义确定标准。关于解释问题,确切而言即关于解释在法律中的作用问题,学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理解即是解释,即法律的每一次适用都需要一种法律的解释。国际贸易和法律的复杂性、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语言能力和法律能力的局限性共同导致了法律用语理解上的困难。对“shall”与“should”的含义如何解读,不仅会涉及会否变更成员在涵盖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效率、合法性基础,而且还可能会侵蚀国家主权。或许,德里达所创立的如下悖论能成为合理平衡并缓和WTO司法解释哲学中能动主义和克制主义冲突的一个参考标准——“一项判决要想成为正义的判决,它必须是负责任的而且是自由的判决。因此它必须‘既受法律的约束也不受法律的约束:它必须既保存法律,同时也破坏法律或者将其搁置。”只不过,专家组/上诉机构对“shall”与“should”含义的公正解读必须戴着DSU第3.2条和第19条所共同铸造的镣铐跳舞,通过对语言规则和法律规则间关系的探求,并通过对习惯国际法解释规则的遵守,努力降低法律规则表达的模糊性所可能造成的法律不确定性,最终实现澄清条约用语意义的目标——增加条约中当事国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JS
参考文献:
[1 ]李克兴.英语法律文本中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及其翻译[J].中国翻译,2007,(6):54.
[2 ]索必成.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的中文翻译[G]//陆文慧.法律翻译——从实践出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01.
[3]韩立余.既往不咎——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6.
[4]Bryan A. 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K].7th ed.West Group,1999:1379.
[5 ]王宝川.论Shall在汉英法律翻译中的应用[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
[6]赵宏坤.浅述法律汉语“应当”的误译[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1,(1):50.
[7]苏小妹.法律语体中的情态动词“得”[J].求索,2008,(2):158.
[8]李剑波,种夏.法律英语中情态动词shall和may的翻译[J].US- China Foreign Language,2006,(6):39.
[9]许加庆.法律英语文本中情态动词shall的用法及翻译[M].学理论,2009,(5):190.
[10]Peter K. Yu.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RIPS Agreement[J].Houston Law Review,2009,(46):797-1046.
[11]Daniel Gervais.The TRIPS Agreement: Drafting History and Analysis[M].2nd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2003:116.
[12]Carlos M. Correa.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97.
[13]朱榄叶.WTO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1995-2002(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
[14]孙志祥.合同英译理解过程中的“合法”前提和“求信”标准[J].中国翻译,2001,(5):53.
[15]张东平.WTO司法解释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26,145.
[16]Jack L. Goldsmity,Eric A.Posner.国际法的局限性[M].龚宇,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59.
[17]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M].程朝阳,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
[18]约翰·H·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M].张乃根,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70.
[19]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实践[M].江国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0.
[20]王宏.模糊语言及其语用功能[J].外语教育,2003,(2):12.
[21]魏敏.论法律用语的语言特征——论模糊性及其翻译[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112.
[22]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5:315.
[23]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351.
[24]陈小全,刘劲松.法律文本中shall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中国翻译,2011,(3):65.
[25]程红星.WTO司法哲学的能动主义之维[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54-255.
[26]杨国华.WTO的理念[M].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177.
[27]陈云良.法律的模糊问题研究[J].法学家,2006,(6):18.
[28]陈欣.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司法克制主义vs.司法能动主义[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