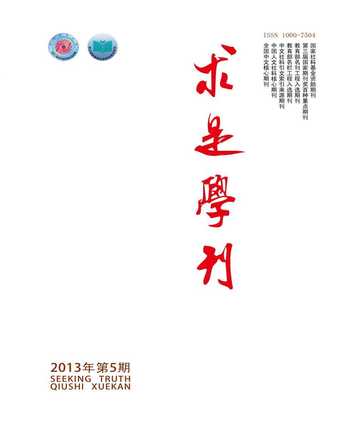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
摘 要: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熊十力;法家
作者简介:宋洪兵,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韩(非)学史略”,项目编号:12YJAZH118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014-09
韩非子素来为后人冠以“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头衔。其实,韩非子不仅为商君之法、申子之术、慎子之势的集大成者;同时,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也是一位综合各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蔡元培称:“韩非者,集周季三大思潮之大成者也。”1郭沫若也曾明确指出:“韩非确是把申子与商君二人综合了,而且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段。这综合倒并不限于申子与商君,如从渊源上来说,应该是道家与儒家。而在行程的推进上则掺加有墨法。”[1](P363)可见,韩非子思想不仅与其前代之法家、道家、墨家思想颇有渊源,而且更因韩非子曾师事荀子这一历史事实而使其与儒家的关系极为密切。2然而,韩非子与儒家之间存在深厚的思想渊源丝毫不能减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的重重隔阂和尖锐对立,尤其在政治主张方面,儒家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礼治”或“德治”与法家现实主义色彩的“法治”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种政治主张的彼此排斥与对立,诚如阎步克所主张的儒家“人治”与法家“法治”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着并非无关宏旨的区别”。[2](P212)所以,冯友兰在评论儒法关系时深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3](P143);瞿同祖干脆以“敌对”一词来概括儒法关系。[4](P330)儒家与法家恩怨扭结,彼此堪称思想领域的天敌。
因此,秦汉以后的儒家士人对韩非子等法家人物的种种品判,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基于学派立场的意气与冲动,对韩非子“毁德、反智、焚书、坑儒”等政治主张以及韩非子的人格进行口诛笔伐,以泄韩非子“毁我仁义道德”之愤懑。历代儒者对韩非子人品与思想的评论难以做到“了解之同情”,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如此的学术史背景,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在抗战期间撰写的《韩非子评论》1一书,以相对公允的治学态度研究韩非子,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本文不揣浅陋,拟在分析《韩非子评论》一书内容的基础上,探讨熊十力对韩非子人格及思想的深入研究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和不同流俗的观点,并就治“韩非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极力主张矫正“五四运动”对传统儒学批判态度的偏失,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从正面来阐释儒家的真精神,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熊十力不仅了解西学,而且精通佛学,最为服膺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之学”,并着力使之系统化与体系化。熊十力专注于儒家传统形而上之本体论的研究和创建,主张充分开掘人的内在本性,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肯,自发自开”的“新唯识论”和“体用不二”的体用观,并“力图通过重建儒家的天人统一观来回应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说明现代人的生命安顿问题”[5](P86)。由于熊十力思想的根本特征以重构儒家心性之学形而上本体论为依归且主要目的在于为国人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所以难免带有厚重的“务虚”色彩,致使同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漱溟批评熊十力“癖好着思想把戏,其势要把不尚理论者引向理论去”[5](P89)。也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儒家传统且以“心性”一系为思想旨趣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却以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立足于现实,对韩非子思想以及韩非子人格做出了远比此前儒家士人公允、深刻的判断和分析,亦因此而展示了熊十力思想中不仅关注“形而上”,同时也关心“形而下”、关心社会现实的另一面。
熊十力“韩非论”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超越了单纯学派立场的态度之争而趋于一种平实质朴的观点之争,从而在研究起点就比此前的儒者高明许多,这或许与熊十力立足于传统不满于一味引进西学以嫁接于中国本土之上所带来的“水土不服”有关,同时亦与其直认儒家思想乃“真民主自由之法治”的传统本位立场有关。在熊十力看来,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法治等观念,反倒不如中国之传统文化精神。如认为“圣人责长民者以父母之道,此为真民主自由之法治。人类如不自毁,必由此道无疑。真民主自由,今之英美,何堪语是?”(第45页)在《韩非子评论》中,熊十力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西学盲目引进的不满。他说:“外来法,虽纸上有之,而实不能自行,毕竟无法”(第63页),又说:“春秋,尚书,三礼,甚可考见圣人制刑之意。惜乎今人不肯究,乃一意抄袭外人。夫商韩惨酷,固无理;而中外异情,则外袭非所宜也。”(第84~85页)
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盲目抄袭外说的强烈不满,熊十力对传统文化的那份维护情怀逐渐开始游离其固守的儒家立场,法家和韩非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其传统观念中变得“有用”起来,甚至对韩非子治乱国用重典的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六经之言刑,本主罚当其罪,无可故轻故重,此以常理言也。然治乱国用重典,经亦有明文。民国以来,居上位者,释法而用私,大官承势谋私利,国贫而家富,宠帅不能战,而皆善殖财。或且以贪骂人,而自纵部属为之,无知而娇恣,败国犹不失宠任。至于民刑诸法,抄袭外人,本不适于国俗。法吏出自都市上庠,以取资地,为谋官求财之具。所学不过抄袭外说,于国法、民习,都不措意。一旦居官断狱,则缘金钱,与绅士酬应,而任意出入。法毁,而民日习于滑,地方多事,良民无可安生。如是而欲毋危亡,不可得也。”(第91页)在此,熊十力透露出以下观点:其一,法家重刑思想实则源出于六经;其二,重刑可以应对民国时期的贪腐行为;其三,民国时期照搬西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导致民风凋敝,良民无可安生。尤其值得注意者在于,熊十力对现实的批判视角与韩非子的思路竟然惊人相似。试比较韩非子的说法:“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韩非子·有度》)(下引《韩非子》只注篇名)“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孤愤》)显然,熊十力的这种语调与逻辑,纯粹是“韩非式”现实思维模式的复活而非“儒家式”理想主义的再现。
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与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密切联结。《韩非子评论》写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日寇的铁蹄正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土的沦丧、大众的嗟伤,夹杂着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无能,使熊十力无法纯粹停留于儒家思想的理想层面,转而对于法家尤其是韩非子思想的现实功能给予高度关注。所以,熊十力对于韩非子思想的“救世功能”极为欣赏,以为韩非子的尚力思想与独立精神堪为当世之导师。他说:“韩非生于微弱之韩,故其政治思想,在致其国家于富强,以成霸王之业。其坚持尚力,吾国人当今日,尤当奉为导师。熊先生亦以此有取于韩子。”(第6页)又说:“韩非之思想,古今中外竞争之世,所必有也。”(第7页)而韩非子思想中“自恃而不恃人”的独立自主思想也与熊十力基于国情而生发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爱国热情产生了强烈共鸣:“韩子于内政、外交,一以自恃而不恃人,为立国精神,为坚强自信而绝不游移之国策。……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第48页)正是立足于现实关怀而非单纯的理想主义,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给予充分肯定。
因遭受异族侵凌之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因爱国热情而肯定韩非子思想的救世功能,因韩非子思想的救世功能而高度赞扬韩非子为一爱国者,乃是熊十力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评价的内在理路。关于韩非子人格的评价问题,历代学者围绕着韩非子入秦一事及其《说难》一文,聚讼不绝,遂使韩非子人格品质问题成为一桩千古悬案。其中,尤以儒者站在儒家立场对韩非子人格的批判为甚,鲜有对韩非子人格持赞誉态度者。究其原委,盖与韩非子学说中力诋儒者以文乱法、于国无用的思想倾向有关。由于韩非子在《说难》中以冷削尖刻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法术之士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采取卑躬屈膝、奴颜媚骨、阿谀奉承的方式以讨主子欢心的百变嘴脸,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如何把握听话者捉摸不定、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并投其所好,最终获得信任和重用。因此,后世论者往往将《说难》篇的主旨联系起来而认定韩非子是一个品质败坏的无耻小人。后世学者评论韩非子人格的另一视角是有关韩非子使秦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围绕着韩非子到底有无用秦之心这一争论焦点,逐渐形成了“韩非子是卖国贼”与“韩非子是爱国者”截然相反的两派。从韩非子“使秦”而有心“用秦”的立场来审视韩非子人格的学者尤以司马光与江瑔的言论为代表,他们认为韩非子为了谋取秦王信任不惜出卖自己的宗国,对韩非子之死也持咎由自取的观点。司马光《资治通鉴·秦始皇十四年》云:“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悯哉!”受此观点影响,江瑔《读子卮言论黄老老庄申韩之递变》也说:“韩子则变之为视天下为无一可信之人,终于残民而弃国。”而专治韩非子思想的人,则往往对韩非子“情有独钟”,倾向于肯定韩非子的人格,将韩非子定位为爱国者。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韩非子集解序》中说:“非劝秦不举韩,为宗社图存,书至无俚,君子于此,尤悲其志焉!”陈千钧针对司马光对韩非子的评价表达了如下看法:“意司马氏以杨子无所不至一语,因断其欲覆宗国以售其言,遂以非之救国,而反为卖国求荣矣,岂不冤哉”,认为“韩非子救世之志,与古之圣贤有何异哉?”、“韩非具有勇敢牺牲之精神”。[6]
如果说两派之间观点的对立可以归因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与价值信仰,那么,熊十力自儒家学派内部发出的声音则应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诚然,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宗的熊十力,同样站在儒家立场对韩非子“务法而不务德”以及“毁德、反智、趋于暴力”的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和强有力的批判,如称“韩非攻儒,无一语不妄”(第85页),甚至存在对韩非子人身攻击的倾向:“余以此知韩非诬词,直同犬吠耳。”(第66页)但熊十力作为一个真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旦具体到韩非子人格的评价时,便能够摒弃学派间的态度之争而力图公允地给予其恰当的历史定位和人格尊严,这在历代儒者当中实为罕见。
熊十力对韩非子人格的定位,乃基于其对韩非子当时所处境遇的分析和判断,认定韩非子绝无用秦之心而实存爱国之志。在熊十力看来,战国时期,秦韩为近邻。秦自穆公以来,世用客卿,六国有才能之士,大多都在秦国取得了相应的职位,可谓仕途顺畅,韩非子对此知之甚切。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韩非子却独独没去秦国效力,即便是在韩王不见用之时,韩非子仍然无此想法,及秦王发兵攻韩时方才以使者身份出使秦国,而韩非子出使秦国的唯一目的,不在于弃韩而用秦,而在于劝秦存韩,终为李斯等人害死。基于如此判断,熊十力断定韩非子乃高尚的爱国志士,即使为之执鞭也心甘情愿:“其爱国情思深厚,其风节孤峻,使韩子生今日,余为之执鞭,所歆慕焉。……韩子论政虽刻核,其志节,可谓诚悃极矣。”(第25页)对于韩非子何以不入秦原因的阐释,除其存有爱国之心外,熊十力还颇有新见地指出,韩非子对秦国怀有鄙夷之意。理由是“韩子虽主极权,并非昏狂之徒所可用,亦非阴鸷沉雄、机智深阻、狡变不测者,遂可行使极权而无害。商鞅,孝公始用秦以开霸业,而韩子犹不许以用术,但称其为法而已。孝公已狠,吕政阴鸷,视孝公尤无道。韩子必心薄之。……观韩子之志,视吕政当如腐鼠耳”(第30~31页)。缘此逻辑,韩非子不入秦当在情理之中。熊十力此论,可谓创见,亦不无道理。另外,熊十力对韩非子实话实说的坦白与率真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韩子直揭霸王主义之面目,异乎晋文辈假攘楚之名,而实怀侵略野心,又始终爱国,而不屈于秦,是则韩子之坦白弘毅,犹有可敬者也。”(第68页)
综上所述,该怎样解决对韩非子人格的评价问题,虽然众说纷纭,然而从一位以“心性之学”为宗的现代新儒家之口道出的韩非子的“爱国者”1形象,或许对于了断这一桩千古疑案有所启迪。毕竟,甘为思想领域的天敌执鞭的勇气和胆识,固然说明了一代儒学宗师熊十力胸襟的广阔,同时也更能说明其对手品质的高洁和可敬。
二、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的学术评论
熊十力在肯定韩非子人格以及对于“当今社会”有所助益的同时,也对韩非子思想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令人深省。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的评论相对比较全面,内容涉及韩非子思想的方方面面,包括韩非子思想的总体定性,对韩非子法术势理论的分类阐释、对韩非子非儒的批判、对韩非子人性论的认识、对韩非子思想内部自相矛盾之处的深层解析以及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短命灭亡之间的关系等。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研究最为精彩的地方,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他对韩非子“法”、“术”思想的研究和评论方面多有创获;同时对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灭亡关系的探讨也值得后人借鉴与反思;对韩非子思想中自相矛盾之处的阐述,也新见迭出。
第一,熊十力认定韩非子思想的总体性质是一种有关“法术”的政治思想,而在“法术”当中,终究以“术”为先,是一种“术治中心主义”。因此,熊十力对韩非子之术治思想着墨尤多,一改以往依“法术势”顺序研究的惯例,先从韩非子之“术”讲起。韩非子曾在《定法》篇中批判商鞅徒法而无术、申不害徒术而无法的思想,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后世学者围绕着韩非子思想,产生了“法治中心主义”1、“势治中心主义”2以及“术治中心主义”3的观点。而熊十力便是术治中心主义的早期提倡者之一。他认为:“韩非之书,千言万语,一归于任术而严法。虽法术兼持,而究以术为先。”(第22页)在熊十力之前的学者对于韩非子之术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权术而言,主要集中在《内储说上七术》所论及的“挟智而问”、“倒反言事”、“除阴奸”等阴狠狡诈的政治权术方面,从而对韩非子之术批判甚烈。扬雄《法言·问道篇》说:“申、韩之术,不仁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则狐狸蝼螾不蝼腊也与?”熊十力虽然也对韩非子的术治思想表示了反对意见,如他说“韩非之术,终不免出于阴深,流于险忍”(第42页),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既有观点,而是将道家思想与韩非子术治结合起来考察,极有见地地指出:“术,固可万能至是乎?人主用术,何由得无失乎?韩非以虑及此,是以归本于道家也。”(第26页)在熊十力看来,天道虚静,万物自化,圣人无为,一任自然,因天道行事而不以私智逞强,当是韩非子术治与道家无为结合的根本所在,就此而论,像德国一味盲动之希特勒对于韩非子思想可谓望尘莫及。所以他说:“韩子言圣人去智巧,故其得力处,全在因天道,究物理,此其能术之所本也。可见用术之所以必出于正也。”(第35页)唯有致虚守静,才能立本;立本方能知几,知几而后可言术。因此,违道逞智者不能言术。可以说,这是熊十力“韩非学”最有价值之创见。
以往学者大多忽视韩非子于此处对君主的素质要求而摘其一端攻击韩非子的专制和集权思想,熊十力的洞见之处就在于,他能明确指出韩非子之术并不仅仅是阴毒狡诈,也不仅仅是政治权谋,在某种意义上,韩非子之术其实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规范和制约。唯其如此,熊十力才不止一次地对以往学者对韩非子的误读提出了批评。他说:“晁公武谓韩非极刻核,无诚悃,其言自是,而未免肤泛。彼于其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处,全无所窥,但言刻核,岂知韩子乎?”(第24页)又说:“韩子因天之道,反形之理云云,近人有下一句,失却上一句。所以不堪担荷世运。”(第36页)熊十力对韩非子术治思想的研究,于此可谓光彩焕然,切中韩非子术治思想之真意。诚如其所自坦言,熊十力可谓韩非子的知音。
第二,熊十力基于韩非子“援道入法”思想的准确判断,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精彩的剖析。盖因韩非子道法相依之故,熊十力同样对于不解韩非子思想真实意思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韩子释老氏之言慈,而曰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此中意思深远,惜乎今人不足与语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此前的认定韩非子法治思想乃“刀锯斧钺妄加滥杀无辜”4的观点,熊十力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子以为守法者,乃自己对于自己之慈爱故然,决非由强制而然,真善美哉,斯意也。今人乱法、毁法,太下贱,太不自爱。”熊十力直认韩非子解释《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所得出的“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的观点是“道尽民主法治精神,美哉洋洋乎!”(第51页)姑且不论这种将韩非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法治思想定位为“民主法治精神”的解读是否存在过度诠释的嫌疑,单凭熊十力自韩非子思想内在的逻辑理路来分析判断而不是意气用事或心血来潮的判断,就显得质朴可信得多。
熊十力已隐约察觉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理想成分与现实取向之间的矛盾性。他认为韩非子“因道全法”的思想乃是民主法治精神,但由于韩非子思想本质上又是提倡霸王主义和集权主义,二者之间的矛盾恰好体现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对于这种两难,熊十力同样没有一味去指责韩非子,而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极力探求韩非子当时为何不沿着“民主法治精神”走下去转而鼓吹霸王主义。“韩子不向民主主义去提倡,何耶?韩子亟于救韩之亡,思以集权振起,此其所以不言民主也。”(第51页)唯有感同身受、设身处地,才能做到“了解之同情”,熊十力之于韩非子,可堪足谓。对于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立法权问题,熊十力也依据《韩非子》题中应有之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代以来,学界一般认为,韩非子包括法家的最大的缺点,在于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掌控于君主之手,因此,法家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7](P189)这种观点虽然符合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然未免存在以后见之明责古人思想的苛刻做法,试想,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怎么可能知道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度?韩非子虽然没有解决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权问题,但绝非意味着韩非子在对立法权方面没有考虑,熊十力发现了这点。他认为《韩非子》一书中的“圣人”乃指“虚静无为之君”,认为“君心虚静故,无有偏蔽,能得天下之情,故能制法,以平天下之不夷,矫天下之不直也。故必圣人而后能制法。非昏乱之主可妄作也。韩子以平不夷、矫不直为制法原则,可谓千古不易之论”(第53页)。表面上看,似乎此种结论的得出恰好论证了韩非子思想是“人治”而非“法治”,但若再结合韩非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经》)以及“缘道理以从事,则无所不成”(《解老》)的内涵来分析,“圣人”制法也并非可以随心所欲无所节制的。当然,韩非子此种思想到底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是一回事,但韩非子有此思想又是另一回事。那种认为韩非子是极端专制主义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第三,有关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灭亡之间的关联,历来是古今学者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自秦汉以降,历代史家基于秦实践法家思想二世而亡的兴亡教训,指出秦亡原因在于“师申、商之法,行韩非子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以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董仲舒语),进而认为韩非子思想“惨礉少恩”(司马迁语)、“仁义不施”(贾谊语),得出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司马谈语)的断语,《汉书·艺文志》也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从而将韩非子思想与暴政和亡国之道连在了一起。熊十力研究韩非子,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短命而亡关系的探讨,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熊十力意识到,秦朝暴政与韩非子思想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他说:“秦之祸天下后世而自祸者,韩非不得无罪也。”(第71页)但他在探讨韩非子的“法术”思想时,又始终不离韩非子所论之“道”,从而认定韩非子思想虽在表面上与秦朝灭亡有关,但从深层意义而言,秦朝的政治措施不是韩非子真思想的体现,而是对韩非子思想的背离。因此,秦朝的短命不能归咎于韩非子。熊十力将“道”与“法术”结合起来考察的治学方法,使得我们更切近地了解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灭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因为“道”与“法术”的结合,势必要求君主顺天应人、因道全法而去好去恶以保持公正性与客观性。韩非子“因道全法”的思想与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殆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熊十力正是基于“韩子援道以入法,首于形而上学中,求法理之根据。……以法理解老,而使法理于玄学及宇宙论中,得有根据”(第50页)的认识和判断,才得出秦政“误读”韩非子思想终致贻害天下苍生的结论来。“(吕)政卒妄袭其说,以遂兼并之欲于一时,终自亡而已矣。韩子极权之论,必有道者而后可行。无道,而恃其阴鸷以用之,虽逞志当时,而祸害之中于苍生者无也已。”(第31页)又说:“智巧者,阴鸷之狂慧,可以侥幸一时之利,以此谋天下事,终当祸苍生以祸己也。秦政不得韩子之真,而窃其似,卒蹈于凶,万世之殷鉴也。”(第37页)此数语切中要害,可谓深刻至极。也正因如此,熊十力的“韩非论”较诸此前学者对韩非子思想的评论,高明之处显而易见。
第四,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的深层研究,还体现在对韩非子思想中的自相矛盾之处的分析方面。众所周知,矛盾概念一词首先由韩非子提出,其在《难势》篇所讲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寓言故事如今已是家喻户晓。韩非子曾以自相矛盾的逻辑来嘲笑儒家的尚贤理论,认为“贤之为势不可禁”与“势之为道也无禁”之间势不两立彼此矛盾。因此,后世学者寻求熟谙矛盾律的韩非子思想中的“矛盾”自然成为一个热点。如刘家和先生及蒋重跃教授就曾分析过韩非子思想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认为韩非子的法与术、法与势之间都存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8](P86-88)蒋重跃还进一步详细论证了韩非子思想中有关“当涂重人”与“法术之士”在忠奸方面的矛盾,认为韩非子用忠奸来辨别这两派人物的思想包含着尖锐的矛盾,是不合逻辑的。[8](P227)同时,还认为韩非子《五蠹》篇物质与道德关系的论证“存在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8](P147)。
熊十力在《韩非子评论》中的一大亮点就是详细论证了韩非子思想中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对后世研究者极有启发意义。针对韩非子既提倡“抱法处势则治”又反对“尧舜之贤”的观点,熊十力指出能“抱法处势”的人本来就是贤者,此正好与“不待贤”的观点相出入,即:“夫能抱法用势以治之中材,正是贤。而又曰不必待贤,何其自相矛盾之甚乎?”(第62~63页)这也切实道出了韩非子思想的困境,关于这点,萧公权在评论韩非子的“中主”与圣贤时也曾有过类似观点:“韩子所谓中主,就其论法术诸端察之,殆亦为具有非常才智之人。……其难能可贵不下尧舜。”[9](P235)另外,针对韩非子《五蠹》篇中古时人寡财多故易让同时又说尧禹为天子时禅让是去监门之养、臣虏之劳的观点,熊十力尖锐地指出:“夫人寡财多之世,天子何必劳苦若是乎?其持论矛盾,不自悟也。”(第66页)暂且不论熊十力的论述是否真为韩非子所未料及而自犯的矛盾(这需要从《韩非子》原文来分析和理解,限于篇幅,此处从略),但就现代人的理解来看,如此深刻的分析,在熊十力同时代的同类有关韩非子思想研究的著作中实属罕见,其间蕴含的思想魅力令人赞叹。
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的评论,虽然不免站在儒家立场对韩非子反儒的观点进行责难,但其绝大多数看法都从学术立场而非学派立场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韩非子思想,往往慧眼独具语出而中的,体现了一代大家严谨的治学风范和良好的学术素养,对于后来者继续研究韩非子思想,实在功不可没,与有力焉。当然,熊十力的某些观点,比如“春秋蕴涵最民主的思想”、“法家正统原于春秋”以及“韩非有自做国君愿望”等,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甚至商榷的。
总体而言,通过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启示:其一,儒家与法家并非天敌,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彼此谅解,甚至惺惺相惜。一方面,各自观察问题的视角与方法不同而导致的观点分歧,并不足以构成对对方人格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儒家与法家思想各有侧重,均对应于社会的特定领域发生作用,因而亦不足以根据此学派而否定彼学派之价值与功能。熊十力赞赏韩非子的人格并且肯定韩非子思想的现实功能,同时也能给予同情之理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二,对于熊十力及其学术思想的认知而言,其不仅仅关注形而上,同时也关注形而下;不仅具有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有接地气的现实关怀。其三,熊十力在抗战时期这一特殊语境中对“韩非学”的研究所具有的态度与方法并未受到应有重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矛盾的转移,其他现代新儒家未能继承他对韩非子的包容与理解,牟宗三等人的“韩非学”研究主要以批评为主。
三、“了解之同情”如何可能?
研究思想史,必然涉及对某一个思想家身世及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评论一个思想家很难,而对于一个历来有争议的思想家的历史评价,尤为不易。究其原委,大概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时空间隔,年代久远,今人与古人超越时空之完全沟通存在困难。诚如陈寅恪所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10](P247)。其二,门户偏见,个人好恶,是影响研究者评判古人的一个常见现象。盖如蔡尚思所言:“不问是非得失,唯论门户学科”[11](P115),合于己意则褒之,不合己意则贬之,“恃其聪明,强古人之材料以就我……及一按原书,立觉其纰缪百出”[11](序)。其三,以后见之明苛求古人,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西哲黑格尔就曾说过:“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12](P46,112)由此,对古人具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自然成为历史研究者的理想追求。
耐人寻味的是,古今治“韩非学”的学者,多半都存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缺憾,遂不足以称之为“了解之同情”。首先,后代学者对韩非子身世及思想的研究受到资料方面的限制,关于韩非子思想,仅存《韩非子》一书,而其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质疑1,而人们对于韩非子身世的了解,除了《史记·韩非列传》以及《战国策》“韩非谗姚贾”的记载以外,别无所知。如此一来,就很难在详细获知韩非子身世经历的基础之上进行中肯的分析和评价。其次,古代研究者受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秦朝灭亡的教训,往往基于学派立场或者某种“后见之明”对“务法而不务德”的韩非子进行了诸多有违韩非子本意的歪曲解释和不公正的责难,门户之见与意气之争在“韩非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其三,及至近代,学界要么以韩非子法治比附西方法治,要么责骂韩非子思想是专制思想并不懂民主政治,纯粹拿后人的思想方式去改铸韩非子,要么使他在“法治”的荣光下成为中国的先驱,要么使他在“专制”的阴影下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商榷和反思的,很难称之为“了解之同情”。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了解之同情”?古今中外的理论家们依据不同的观察视角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归纳这些答案,不外乎以下几类:其一,在思想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评论思想家的功过是非,这要求研究者由“局外人”的角色转换为“局内人”,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然后才能表一种了解之同情。[13](P178)其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学者认为:“把当下当成历史,可以是历史学的一种有用的眼光。”[14](P355)因为把当下当历史时,人们就会根据自己感同身受的经验和体悟,设身处地地理解具有相似历史语境的古人,从而能与古人在一定程度上感同身受,引发共鸣。其三,不以常识问题衡定古人思想的得失。古人并不傻,有关常识问题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着相同的认识,例如关于古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孟子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但孟子所言仅为一常识,人们常常据此责难韩非子思想囿于一偏,只要法治不要道德。然而,韩非子岂不知“善之于政”的重要?不知“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人们更多应该思考的是,古人为何“违背”明显的常识反其道而行之?
正因如此,更需要学者以一种“了解之同情”来研究韩非子。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遵循着“虽绳治韩子之短,而未尝不择其长也”(第91页)的原则,对韩非子思想做了相对公允的研究和判断,所以其许多论断才为前人所未有者。究其原因,就在于熊十力所处的时代与韩非子产生了某种共鸣。“是什么动力激励历史学家设身处地地思古人之所思,想古人之所想呢?对此,柯林武德的答案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是从史料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而问题又是从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15](P91)韩非子所处的韩国在战国时期为七国之中实力最弱者,“外则列国纷争,以强凌弱,内则重人把权,以下弑上”,而欲解决此问题,就必须稳定政治秩序,使得政治清明,富国强兵,从而“结束分崩离析的战国政局”,这便是韩非子的“问题意识”之所在。[16](P15)
如前所述,熊十力《韩非子评论》撰写于日寇侵略之时,当时之社会急需正本清源、整顿腐败之吏治、富国强兵以御外侮,这与韩非子所面临的“问题意识”高度一致。所以熊十力才更能理解韩非子的情非得已之处,才对其人格大加赞赏,才对其吏治思想以及对君主近乎苛刻的要求方面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自然多了几许“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较诸郭沫若同样写于抗战时期的《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大量对“专制”的激愤之语而言,《韩非子评论》实有令人赞叹之处,足堪引为今之研究韩非子者之借鉴。
参 考 文 献
[1]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 陈千钧.韩非新传[A].学术世界[C].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5.
[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 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9]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0]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 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7.
[13]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4] 赵汀阳.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15]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6] 王邦雄.韩非子的哲学[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