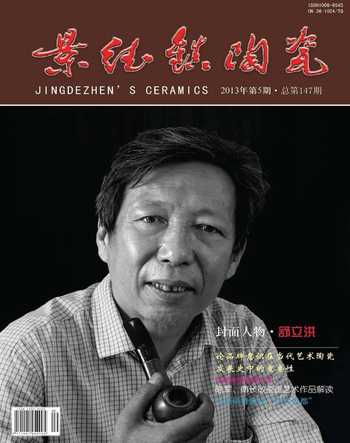美术家的“饭碗”
大家都在关注美术,我关注美术家的“饭碗”。今年,侄儿从师大美院毕业。上个月,我特地去看看他。当问他有什么打算时,他表示要继续画画,当一名职业画家,态度似乎很坚决。我原准备建议他先去找一份工作再作打算,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为了表示鼓励,以2000的价格订购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题材不限,尺寸不论,他自然非常乐意。昨日照片传了过来,也难怪有底气,画得真不错,是临摹了俄罗斯画家伊里亚?列宾的托尔斯泰像。自家大伯伯,不算经济账,还配好了画框。除去画框、画布、画笔、颜料,侄儿所得一千五六百元。而他母亲告诉我,他为画这幅画,毎天从早到晚鼓捣了近二周。就算十个工作日吧,八十个小时,一个学画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绘画所得只抵一个钟点工。切莫以为是我在剝削他,就这价格,我认真地动员亲属订购,居然没有响应。
这就是巿场,没办法的事情。侄儿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人生路。我在侄儿高考时就劝告他不要考美院,以他的综合学力,进一所好一点的普通高校没问题。可侄儿从小喜欢画画,实在不想放弃,只好随他了。其实我女儿也是可以考美院的,是我阻止了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五百强大型外企做一名IT工程师,有不错的收入,挺好的。新中国美术,有过一段欣欣向荣的时期,美术作品,被赋予了政治宣传的功能,只要你能画,不怕没事干。一幅画,印刷几十万张,不算怎么样,换了现在,不得美死。许多人一画成名,家喻户晓。随便跑进一户人家,总能在墙上,桌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找到美术作品。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美术渐渐淡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宣传画不搞了,年画不贴了,连环画不看了,美术好像很坚决地要和大众说“拜拜”,连图书插图都看不见了。而在过去,请戴敦邦、贺友直这样的画家给图书配插图,是要排队的。
留给美术家“吃饭”的地方只有市场了。可怜美术家除了要会画画之外,还要会经营。说起巿场,许多学子看到的其实是高端市场。如同在足球学校踢球的那帮小孩子,问他为什么踢球,很多人会说,我要做中国的梅西。想法自然不错,中国的梅西,如同中国的凡高,不那么容易复制的。事实是,美院的学子,毕业十年后,还能完全靠画画养活自己的很少。在迷茫中挣扎,在哀叹中改行的庞大队伍中不乏极有天赋的画家。在中国,普通人少有欣赏或购买艺术品的需求。就我的视野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有那一位美术圈子以外的人,跑到画廊去买一幅画钉在墙上供自己和家人欣赏。巿场上的美术作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价格几何,升值空间。老百姓在新闻里听到齐白石的画作创下拍卖纪录,有人天价拍到徐悲鸿的赝品,这就是他们眼中美术的全部。有人调查了美术作品的去向,除了收藏家和富豪之外,很大一部分流入官员的手中。一部分是作为礼品赠予的,一部分是为了减少现金持有而买下的。一位美术界资深人士,著名美术馆的馆长不无忧虑地认为,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官员早晚被逐出艺术品巿场,美术家得以生存的空间将大幅萎缩,中国美术的前景不乐观。当然,我们也不用担心后继无人,打个不太合适但很恰当的比喻,就象养猪,养的人多了,超过巿场需求,卖不动了,于是大家都不养,供应紧张,价格猛涨,很多人又重新开养。美术家的生成也是一样的,再说随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对美术作品的欣赏有了需求,谁又能说他们不会进入和参与这个巿场呢?
原载《瓷器》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