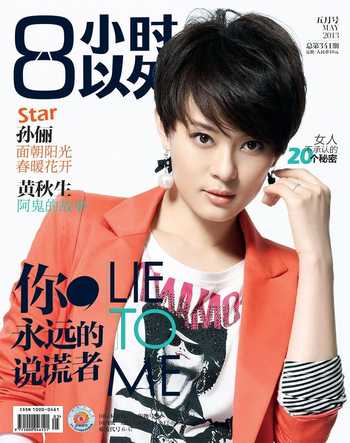秦砖汉瓦君子人格

“2013博鰲亚洲论坛”的首场对话会,主题为“诚信的力量”。会上,有嘉宾说:诚信就是自己人格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现今的商品社会,人们追求钱,不追求诚信。
然而,孔子说:无信不立。
一个人,要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成功,没有诚信是不可能的。诚信可以安邦,可以齐家,诚信者,一诺千金。
诚信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被现代人广泛利用的“一诺千金”这个成语,出自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许多人都同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由于改朝换代,季布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他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巨额赏金所惑,还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终使他免遭祸殃。“一诺千金”从此载入史册。
这是季布的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身价,是诚信的力量。
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周易·乾》中也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
相较于“诚”,“信”被人们更早地与为政之道结合起来。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治理国家时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论语·颜渊》)。“信”还是国与国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老子界定了“信”的本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时指出:“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他自己则信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说即使对不守信用的人也要信任他,这样才可以使人人守信。而荀子,更明确地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
谁都愿意与君子交往,包括小人。君子可靠、守信,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一个故事。春秋时,鲁国曲阜有个年轻人名叫尾生,与孔子是同乡。尾生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和朋友交往很守信用,受到四乡八邻的普遍赞誉。后来,尾生迁居梁地(今陕西韩城南),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一见钟情,君子淑女,私订终身。但是姑娘的父母嫌弃尾生家境贫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姑娘决定背着父母私奔,随尾生回到曲阜老家去。那一天,两人约定在韩城外的一座木桥上会面,双双远走高飞。黄昏时分,尾生提前来到桥上等候。不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雷鸣电闪,滂沱大雨倾盆而下。不久,山洪暴发,滚滚江水裹挟着泥沙席卷而来,淹没了桥面,没过了尾生的膝盖。尾生想着要与姑娘“桥面相见,不见不散”的誓言,遂不肯离去,最后抱着桥柱被活活淹死。
这个故事出自《庄子·盗跖》。后人用“尾生之信”、“尾生抱柱”等喻指人坚守信约、忠诚不渝。尾生的做法不免迂腐,换作今人,肯定会变通。一位留学英国的朋友说,在英国坐地铁很好逃票,不过英国人不逃票,因为英国人傻。好多人都说外国人傻,不会变通。可这种傻,是因为人家有信仰,在没人的时候也要守规。其实这与孔子说的“君子慎独”(在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严于律己)是一个理儿。君子的信仰是良心,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像尾生一样为了诺言宁可赴死的精神。人之区别于飞禽走兽,就是因为人有信仰和精神,这不能用得失来衡量。
在古代,“诚”与“信”单用较多、较早,连用较少、较晚。管仲曾将“诚”与“信”连用:“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荀子也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认为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荒诞则产生社会惑乱。
“夸诞生惑”最典型的就是《吕氏春秋》中记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襄公七年(公元前771)春,周王朝出现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还得从周幽王的宠姬褒姒说起。褒姒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令人沉迷,却唯独不好笑。周幽王为此甚是烦恼,下告示说:“凡有逗褒姒一笑者赏银万两。”大臣虢石父见到周幽王的告示,赶来说:“臣有办法令王后开心一笑。”虢石父附耳对周幽王说了几句话,周幽王大喜。次日,周幽王亲自去请褒姒郊游,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烽火台,周幽王搀扶着褒姒下车,一步步走上烽火台。二人迎风远眺,果然惬意无比。随后,周幽王令人点燃烽火,一股狼烟直冲云霄,煞是壮观。过不多时,只见远处烟尘滚滚,原来是诸侯见烽火乍起,以为外敌来犯,派兵来救幽王。见诸侯上当,褒姒果然展颜一笑。周幽王大为受用,随后又来了两次烽火戏诸侯的游戏。不久后,西戎真的打到京城。周幽王赶紧把烽火点了起来。诸侯以为幽王又在开玩笑,全都不理他。救兵没来,周幽王和虢石父被西戎杀了,褒姒被掳走。
因失信而失国而丧生,绝非偶然。
根据《郁离子》记载,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麻秆儿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至。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一百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鱼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被淹死了。
中国人从小——甚至在出生前——被树立的就是这种观念:信则立。为了成就诚实守信的理想人格,父母们颇费心思。
《列女传·周室三母》记载,有一位母亲叫太任,她“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端一诚庄,惟德之行”,从怀胎之始即对胎儿进行诚信熏陶。太任生出的孩子后来成了周文王。
在中国,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古代父范母仪、以身立信的例子不少。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有曾子取信于子的故事:曾参是春秋末期鲁国有名的思想家,孔子门生中七十二贤之一。他博学多才,且十分注重修身养性,德行高尚。一次,他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办事,年幼的孩子哭着吵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便对孩子说:“你在家好好玩,等妈妈回来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孩子听了非常高兴,不再吵着要去集市了。妻子回家后,曾参便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妻子说:“我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在家里等着才说杀猪的,你怎么真杀了?”曾参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世事,会模仿别人,尤其是以父母作为生活的榜样。今天你欺骗了孩子,明天孩子就会欺骗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明天孩子就会不再信任你,这会毁了孩子的。”
现在有“富二代”,有“官二代”,多为贬义。而“名门之后”,却是令人羡慕的褒义词,因为名门不仅仅意味着名望,更有人文精神的积累和传承。
在古人常见的启蒙教材中,诚信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清人李毓秀编纂的《训蒙文》(后改名《弟子规》)提出:“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笠翁对韵》则推崇:“管鲍相知,能交忘形胶漆友;蔺廉有隙,终为刎颈死生交。”写诫子书是我国古代家庭诚信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篇》专讲诚信,通过“伯石让卿”、“王莽辞政”的典故告诉子孙“巧伪不如拙诚”之理,认为伯石、王莽“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告诫子孙不可“以一伪丧百诚”。
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把诚信丢了。我们在秦砖汉瓦里寻宝鉴宝,却忽略了“诚信”这一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正如“2013博鰲亚洲论坛”上嘉宾们所说,目前我们已陷入诚信危机。
这和教育有关,更和主流人群、媒体的导向有关。比如,前几年,有关“厚黑学”、“潜规则”的书很流行,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处世指南。殊不知,你今天黑了别人,明天别人也会黑了你。
为什么不换个方式——以信立?
北宋词人晏殊,官至宰相,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诚信。在他14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晏殊发现考试题是自己几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地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宋真宗更加信任他。
诚信是人类的美德,诚信是公序良俗。当一诺千金的君子人格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个社会是文明的,人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