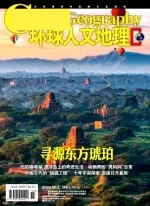在世界之巅遥望西藏
贝尔·格里尔斯



我曾站在喜马拉雅山发愿,一定要去西藏,一定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在当时,这是个有点“不成功便成仁”的使命。如果我爬上珠峰,成为珠峰攀登史上最年轻的登山者,那么之后我至少有得到探险类工作的机会——不管是做演讲还是带队探险。攀登珠穆朗玛峰至少是筹集赞助费进行其他探险的跳板;另一方面,如果我失败了,我也愿意死在山上或败退老家——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学历。
在珠穆朗玛峰山顶,向北可以看见穿越整个地平线的西藏,向南可以俯瞰广阔无垠的喜马拉雅山山脉一直延伸到尼泊尔平原。整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超越这个最高点。而对于雄心勃勃的登山者来说,这座山峰下数千英尺的巨岩坚冰是隐藏的危险混合体,它索取了太多顶级登山者的性命。
喜马拉雅山脉有91座高峰的高度超过7300米,每一座高峰都高于陆地上的其他山脉。珠穆朗玛峰则是心脏——自然界至高无上的荣耀。许多人都努力过,许多人都死了——自那以后,登上珠穆朗玛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梦想。直到1953年5月9日,珠峰才第一次被登上,成功登顶的攀登者是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
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以珠穆朗玛峰为目标的商业性登山探险。登山者得支付6万美元,才能有机会成为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一分子,但这也招来一些缺乏经验的登山客户。因此,探险队带队人常常会有很大的压力。经常要付出的代价是,这些人在发现自己要爬的山实在太高之后,才明白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经历,是充满诱惑的灾难。
1996年,由于风暴反复无常,加上登山者经验不足,灾难性的惨剧就发生了。有一次,山顶的8人在晚上全部丧命。接下来的一周里,珠穆朗玛峰又掠走了3条人命。葬身那里的不止有新手,也有老手。其中的罗伯·霍尔,就是拥有世界上最高赞誉的登山专家之一,因为全力营救另一个倒下的登山者,罗伯·霍尔耗尽了自己的氧气。他遭遇了一个致命的组合——体能枯竭、严重缺氧与极度寒冷。
当时,不知何故,在夜幕降临之时,温度计指数突然一落千丈,在海拔8748米之外,在气温低至零下50℃度的寒冷里,罗伯坚持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罗伯通过无线电通讯连接上探险营地的卫星电话。当时他的妻子简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坐在山上无力动弹的罗伯对妻子说:“我爱你!乖乖睡吧,我的甜心。不必太牵挂我。”这是他们最后的通话。教训如此清晰:你要对山心存敬畏,要了解在某一海拔与遭遇恶劣天气时该怎么做,哪怕是最强壮的登山者也不例外。另外,千万不要被野外诱惑,要知道,在你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样的大山时,钞票是保证不了任何事的——尤其是安全。
攀登在珠峰臭名昭著的南坳,我心灵再一次被震撼。南坳是一片约有4个足球场大小的巨大岩石区,遍地是老探险队留下的遗骸。1996年,猛烈的风暴袭来,登山的男男女女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努力寻找他们的帐篷。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其他人的尸体仍然躺在这个寒冷的地方,很多人的尸体甚至被掩埋于冰雪之下。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阴森恐怖——这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除了坚强得足以到达这儿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无法访问的地方。直升机只能勉强停在基地营,更别说飞到这里来了。无论花多少钱都不可能直接把人投放在这里,唯有精神力量强大的人才可能有幸到达。而这些特点恰恰是我喜欢的。
1998年5月26日早上7点22分,珠峰之巅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任眼泪倾泻而出,在冰冷的脸颊泛滥。我血脉贲张,不敢相信自己突然站在了世界之巅。艾伦兴奋地拥抱我,朝着我的氧气罩兴奋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尼尔仍然朝着我们蹒跚而行,当他走近时,风力开始减弱了。
在神秘的西藏之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们下方的山岭沐浴在绛红色的日光中。我的朋友尼尔也登上山顶,他跪了下来,在身上画十字。然后,我们一起扯下氧气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站起来环顾四周,我可以看到地球的两端(我发誓),地平线的边缘似乎有些弯曲,这是我们地球的弧线。科技可以把人送上月球,但却不能把人送到这里。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神奇之处。突然,我左边的对讲机清脆地响起来了,尼尔兴奋地对着它说:“基地营,我们已经跑出了地球。”
这时我感觉,西藏是那么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