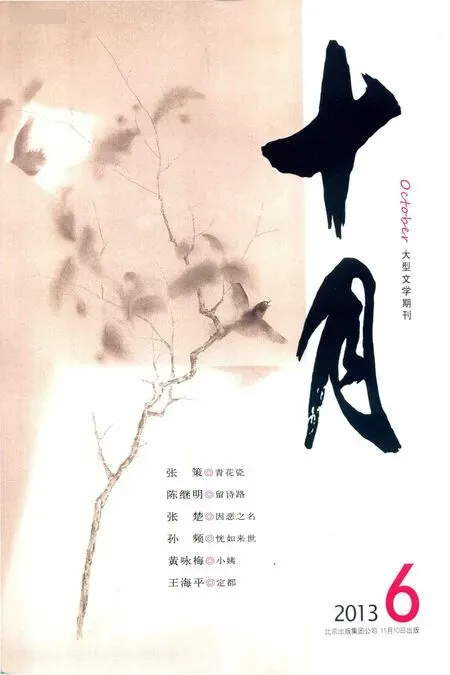低语,让神听见
陈原
悬崖是道路走向地狱的拐弯处
我是一个绝望的传达者
一个苍老丑陋的信使
掌握着最古老的巫术
跛足行走于洪荒的宇宙
我是一个悬崖的提醒者
并因此在巉岩峭壁筑穴
与苍鹰秃鹫为伍
在悬崖居住用篝火照亮悬崖的深度
像时间里的化石静听时间的迅猛
或者像刻进石头里的筋或者骨节
没有语言的世界我的眼睛更加明亮
藏下浩宇的深邃
我的茅屋是宇宙的棚宇
拥有太阳的辉煌金顶
那垂挂的阳光的巨瀑
穿透邈远到达邈远
而在到达渺远的中途证明阳光的过程
我在此处守望着人
守望着在灾难里奔跑
却全然不知的人
守望着破栏而出的人
这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洪水猛兽
我看到了他们向悬崖逼近逼近
依然是狂欢的姿势一切不知
悬崖悬崖悬崖啊
道路向下拐弯拐进地狱
奔跑依然迅猛依然继续并訇然跌落
山风依旧大地上突然没有了人
一片叶子砸响荒原的巨大沉静
无边的静和空无边
我不逃离但我站立的意义被否定
绝望比悬崖还深
我不是幸运者,不是
没有幸存者我也不是
我依靠灾难而活在灾难的具象里固守意义
人消失灾难也消失
我不能站在这里证明灾难
我是最后的坠崖者
以证明我作为人的身份和宿命
而我在坠崖的飞翔里写下最后的诗歌
刻满所有的崖壁,那无数棱角的笔画
作为文字消亡的最后证明
万能的意志啊请留下我的巫者一样的羊群和
牧草
从此世界被羊说出并提起
羊是大地的智者它们来自悬崖边
知道悬崖的坐标
能够躲避所有的悬崖
它们能在牧草里嗅出悬崖的味道
嗅出自己身上的灾难和不祥
它们开始新的法则开始新的时间
人是羊永远寻找的记忆
是它们无法更改的史前
是它们躲避的耻辱的符号
它们必将获得无限的牧草
那是它们唯一的幸运
永恒 将一切载远
静静的下午
世界的模样不知疲倦地重复
除了人的踪迹
一切静止山脉恒卧
河流厮守河床
天空在上
大地仰躺
风和季节的轨迹永不改道
远和近墨守古老规则
世界的声音从远古重复到现在
日轮滚动
我与世界一起静止
灵魂回到肉体
并以肉体的姿势端坐
只有地球的公转与自转
以及运动的时间
将静止否定并载远
世界:有,或者没有
黄昏神降临的时间
是神刚刚走过
留下痕
被我捕捉
渐渐暗淡的水纹
轻轻响亮
然后在一种秘密里守恒
神的背影
构筑着黑夜
照耀另一个世界
光的明灭里
一扇门开启
在对称的世界里我们只看到一端
当我们处于此端
便否定着另一端
就像在对神的肯定与否定里
循环往复
黄昏
是诸神的时间
世界在垂直里近
或者遥远……
大地像一扇门被推倒
大地之门
你的语言多么辽远
呼唤的殷切变成沉淀
从容地等待
多少轻叩柴扉的身影
在原野也在天涯
踉跄的脚步
驻足,或漫响大地
没有关闭
没有敞开
甚至没有分割
柴门只是呈现大地的器官
世界没有内外
没有这边和那边
没有此处与彼处
只有驻足者的叹息和沉思
门下藏着的路
指引着世界
和你我
在自己的心里建一座庙吧
即便不相信神灵的存在
即便不再建构自己信仰的锯齿环佩
当一切都被拒绝
和拒绝了一切
也该在自己的心里建一座庙
一座很小的心龛
把自己安放在里面
敬着供奉着自己那面神像
用自己对自己的信任
和一种自我的道义供奉着自己
用自己面对自己的力量和虔诚
用自我的规范和约束
用自己对自己的自私和认同
用身体里那些不规则的想象和欲壑
支撑起一个庄严的
端正的自己
供奉自己
需要一颗更加诚实和敬畏的心灵。
当每个人都这样供奉着自己
我坚信,神既出
——黔南扁穗雀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