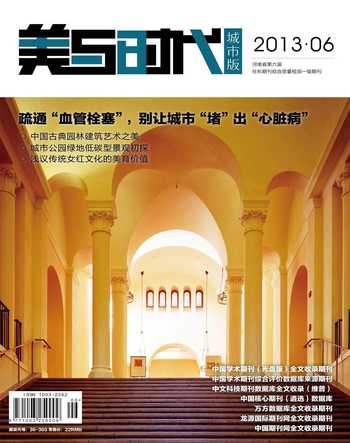论钱选《八花图卷》、《花卉四段》材质与设色手法的差异
江淼

摘要:
南宋的《花卉四段》与钱选的《八花图卷》都是工笔设色的“折枝花”手卷作品,《花卉四段》与《八花图卷》虽同为手卷,但在材质与设色手法方面有着差异,文章就这一问题做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八花图卷》;《花卉四段》;材质;设色手法
《八花图卷》,纵29.4厘米,横333.9厘米。纸本设色,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绘海棠、梨花、杏花、水仙、桃花、牡丹、桂花、茶花八种;右下角钤“舜举”(钱选字)一印,并有赵孟頫题记。
《花卉四段》,纵49.2、横77.6厘米,绢本设色,藏故宫博物院藏。画折枝海棠、栀子、芙蓉、梅花共四幅,第一段海棠树干上署有“赵昌”二字款,从字迹、画风分析,此款系伪托出处。画面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印玺。曾被陈自明、清内府收藏,不见著録。
一、材质的不同(纸本与绢本)
两宋院画使用的材质多为绢本。除了出自宫廷的奢华喜好外,另一个原因是绢的质地紧密光洁,韧性较强,更适合多遍、反复上色,有助于绘出富丽多姿的格调。钱选之所以选用纸本作画,一方面与宋末元初造纸术的推广有关,另一方面,纸本具有自然生动的渗化效果,更能表现文人书写性情所需的水墨趣味。
当然,由于纸质相对绢本纤维粗疏、脆弱,这就要求绘画者用色更加肯定,用墨、用色均以浅、薄为主。纸质的使用可间接反映钱选的素质,其花鸟画的整体特色因之而更为淡雅。这在客观上对钱选绘画风格的形成一定影响。
二、设色手法的区别
两部作品在直观上的显著差别之一是颜色的应用。以白色为例试作简单比较。众所周知,白色具有很强的覆盖力,稍不注意就会画“闷”,是最难运用的颜色之一。《八花图卷》中八种花均施白粉,但白而不僵,宛若天成。与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南宋李迪的《白芙蓉图》和《红芙蓉图》等作品相比,钱选敷施的白粉完全融入画作之中,自然、通透,决不喧宾夺主。《花卉四段》的白色晕染甚或更为过分,显得一团粉气,与钱作相比,更是相形见拙。
在对叶子颜色的描绘上,我们以两幅画都有的海棠花为例进行比较。《八花图卷》中的海棠花,叶子以墨线勾勒施以墨绿,晕染错落有致,变化生动,这样更能衬托花的娇媚。最为高妙的是海棠花后部的远枝,叶子用色极为浅淡,辅以精细的浅赭石勾线,拉伸了空间关系,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而《花卉四段》中的海棠花则是一味的用艳丽的石色,颜色装饰感稍强,没有多少层次感。
其实,院体画与文人画都是历史演进中的产物,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我认为,将院体画的一批作者视为不无贬义的“画工”是个误识。其实,鼎盛时期的皇家画院凭借国家势力将全国最优秀的画家集中到画院中进行专门化创作和研究,他们被称为“画工”,仅出因于他们的御用性(因而不同程度地丧失个性),但并非较之“文人”欠缺文化训练和文化积累。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在院画盛行时期,最终以“黄家富贵”取胜,是因为宫廷难免用画作作为宣化政教,粉饰太平的工具,另一方面,其皇室特殊的文化性格决定了院画富贵华丽的审美取向。然而,正是这种取向,将艺术创作的精致、华美的审美类型推向极致,为古代艺术花园中贡献出了一枝装饰美的奇葩。问题是,随着南宋国势的衰颓,院画艺术也随之趋于工丽小巧、萎靡不振,所谓“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者” 。正是赵孟頫指斥的“近世”之作的病症。就这点而论,《花卉四段》“用筆纤细,傅色浓艳”,外观上继承了院画的主要特征,但工丽小巧,少了一份生机和活力。由是而观,钱作于“高古细润”之外,已另见“高古简淡”之风。不过,更重要的是,“妙处正在生气浮动耳”。
【参考文献】
[1]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2]孔六庆.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卷[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