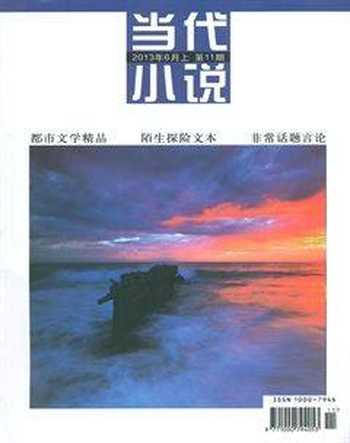苏丽和我是同学
乔土
苏丽。他睡着的时候,那个名字再次从他的睡梦中跳出,如一颗流星般划过。他醒来,左眼又疼了。他捂着眼睛躺在床上,十多年了,这个情况经常出现。他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不清楚左眼跟那个叫苏丽的女孩究竟有什么关系。他怀疑自己肯定出了问题,脑子或左眼。他决定到医院去看看,接待他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医生。
他对医生说,其实我是认识她的,她是我的小学同学。
因为最近十多年里苏丽这个名字时常会出现在他的脑子中,而且每次出现时他的左眼就会莫名其妙地疼上几分钟,所以他搜肠刮肚地尽可能地挖出脑海中最深的记忆。他说,那个叫苏丽的女孩好像比我大一岁或两岁,她来的时候我正在上二年级或三年级。那是我们村办的一个小学,二十多个孩子一到五年级不等,全挤在一间校舍里,老师只有一个。那天,新来了三个或四个差不多大的孩子,苏丽就是其中一个。他们都是刚进村的那个地质队里工作人员的子女。因为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所以我已经忘记了苏丽是自己的同级还是长一级的学生了。之所以或这或那,是我对苏丽的记忆确实模糊了,而且年代实在太久了,快三十年了。
不过,他又说,我对苏丽父亲的印象很深。苏丽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大家都叫他苏工。地质队刚来时没有房子,有家属的队员就在村里租房子住。苏丽的家就租在村中的一所老房子里。苏工戴着眼镜,镜片像个酒瓶底,一圈一圈的。我之所以能记着苏工,是因为苏工有一个笑话。苏工和妻子在锅灶上做饭糊饼子,妻子蹲在灶台前烧火,锅里热浪翻滚,蒸汽溢满了小屋,苏工两手团着玉米面,趴着头往锅里贴,蒸汽扑到他的脸上,把他的镜片扑得像两片眼罩。等盖好锅把镜片擦拭亮,忽然发现锅台后趴着两团玉米面,原来他把玉米饼子贴到锅外了。这事成了村里的一大笑谈,以至苏工离开后,还流传了好几年。
女医生也笑了起来,用漂亮的眼睛鼓励他说下去。他又说,村里来了地质队,村里像我一样大的孩子们有福了。因为地质队每个星期都会放电影,有时一星期放两次,大银幕就挂在我们村的球场上,我和伙伴们满场子追逐打闹,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我最初的文学修养就是来自那个球场。
至于当初和苏丽说过什么话,还是看电影时和苏丽做过什么事,我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根本就没有。只记得大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也许是一年多点吧,苏丽就离开了村小学,因为她的父亲调到招远去了。关于苏丽的离去,我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只记得苏丽走后很长时间曾来过一封信,信是给林老师的,林老师在教室里读了,大意是苏丽很想念在这里的时光,最后说了一些思念的话,不过十多岁的小孩子又会说些什么呢?苏丽在最后提了一些朋友的名字,我清楚地记得第四个名字是我的,因为林老师读到这里时还看了我一眼,说:“苏丽对你记得很深啊,你是她写的这些朋友中惟一的一个男孩……”弄得我满面羞红,很不好意思。有时我就想,自己脑子中常出现苏丽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件事呢?我真的说不清楚。
这就是我脑子里关于苏丽的全部记忆。要不是最近十多年里,苏丽这个名字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就像一颗流星般划过,要不是每次划过苏丽的名字时我的左眼都会疼,我也许早就忘记那个叫苏丽的女生了。
我也曾做过一些工作。那年在鲁大上学,吃饭时我的脑子里再次划过苏丽的名字,在我左眼疼痛时,我忽然灵光一闪,我觉得苏丽就在我身边。于是我想法查询了学生档案,学校的在校女生将近三千人,并没有叫苏丽的女生,我又把姓苏的女生挑选出来,仔细研究,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但结果仍是让人失望。我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从此再没做过这么幼稚的事情。
女医生静静地听完了他的陈述,让他躺在床上,俯身去查看他的眼睛,问他,你是说先出现苏丽的名字再眼疼的?
是的。他说。
你确定不是先眼疼然后再出现苏丽名字的?
这……他答不上来了。他一直认为是苏丽的名字引起眼疼的,而现在被医生问过后,他有些说不清是不是眼疼引来了苏丽的。
这很重要吗?他说。
你左眼有点小问题。女医生并没回答他,用药水给他做着清理,说,不过没大事。
我也在鲁大读过书。女医生放下药水,不过你查学生档案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对了,我忘记查毕业学生的档案了。他说着,使劲眨了眨被女医生弄花了的眼,眼前清晰了许多,他忽然看見女医生胸前挂着的牌子写着两个熟悉的字:苏丽。
他的脑子迷糊起来,只听见女医生说道,其实我也一直记着我的一个小学同学,那天晚上要不是他在小树林里喊了一声,我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
他隐约想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看电影,他肚子不舒服,好不容易挨到换片,他跑出来方便。因为是解大便,他怕有味被人骂,就跑到了离球场很远的小树林里,正准备方便时,忽然听到树林里有一男一女的争吵声,他心急着赶回去看电影,又怕自己大便时会被树林里的人出来看见,就喊了一声:谁在里面?树林里跳出一个人撒腿跑了,那人跑的时候手里扬起的一把沙石打到了他的脸上,把他的左眼迷住了。在他摸眼睛的时候,另一个人从树林里跑出来朝村子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要回家,村里的二流子螳螂在小树林里截住了我……女医生说。
他的左眼猛地又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