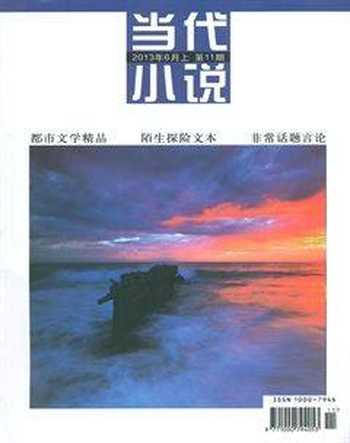离婚记
汤成难
1
我该干点什么?
这个问题又在困扰我了。我把自己扔在阳台的摇椅上,看着一小块天空发呆。这个时候,总是会发生点事情,比如太阳会在这个时候悄悄落去,远处的钟楼会疲惫地敲响五次,楼下的那个马脸女人一脸神圣地走向菜场……可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仍然没有想好该干点什么。
我的丈夫李大勇出差了,一个礼拜后才能回来。我的儿子李小强上学去了,也将一个礼拜后才能回来。临走时,前者给我一个拥抱,说,嗨,宝贝,好好保重自己。后者也给了一个拥抱,从身后反扑上来,说,嗨,老妈,你老帅了。一前一后充满雄性的拥抱使我幸福不已,我的牙齿颤抖了,然后一个上午便在这种颤抖中洗衣,刷碗,打扫卫生。是的,还有什么比干家务活更能表达女人的幸福呢。
然而,只是到了中午,我便感到极度空虚,好像谁说过,一处的快乐不能抵消另一处的痛苦。现在我深刻感到,早晨的那种幸福感不能抵消此刻庞大的空虚。
我把手机打开,搜了一圈,似乎没发现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对象,于是把电话拨向了李大勇,告诉对方我此刻的无所事事,李大勇接通电话就说,嗨,忙死我了,忙死我了。他把这四个字重复了两遍,刻画了自己陀螺般的身影。当然,临挂电话前,李大勇还是为我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诸如逛逛街,睡睡觉,看看电影,或者,找闺蜜刘美红……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刘美红的——我的高中同学,但是这些年来似乎疏于联系了。我把电话拨过去,立即接了,好像对方正在等这个电话。我没有说自己“空虚”,这个词对于刘美红来说太文绉了,我說,小红,我现在真是无聊得很。对方在电话里狂笑了一阵,然后扯着嗓门说,正好三缺一。
三缺一,也就是说,有三个人正迫切地需要你。这种感觉让我的牙齿又颤抖了一阵。挂断电话十分钟后,我的闺蜜刘美红,丁小云,还有王芳准时出现在我家的门前。
刘美红脱掉鞋,惯例在屋里巡视了一番,说,家中没有一个男人,当然无聊得很。刘美红的话引得丁小云和王芳咯咯笑起来。她们仨都是我的同学,高中时住一个寝室,先天条件,决定了闺蜜关系。毕业后我们来往甚密,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当然也包括搓搓麻将。可是,这些年我怎么就和她们疏远了呢?用刘美红的话说,你那是忙着相夫教子呢。这话又把丁小云和王芳惹笑了。这个晚上,我们没有打麻将,而是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感怀“这些年”和“那些年”。我们谈了房价,谈了金融危机,当然更主要的谈了各自的家庭状况。刘美红谈到了她的公婆,丁小云谈起了她的女儿,我也谈到了我的丈夫李大勇。我说,他呀,还是那么不爱干净,臭袜子到处扔,早晨给他洗衣服,白衬衫简直脏透了,上面竟然还缠了一根很长的头发,金灿灿的,太有意思了。
我突然停止说话,因为三双眼睛正惊异地看着我,瞪得滚圆。刘美红说,你竟然笑得出来。我说怎么了,你们不觉得有意思吗,那根头发缠在纽扣上,有这么长。我用手比划了一下,然后忍不住又一阵大笑。
刘美红说,这显然不是你的头发。我点头表示赞同,因为我是黑色短发。
刘美红又问,那到底是谁的头发?
丁小云和王芳异口同声地说,另外一个女人的头发。
刘美红又问,知道这根头发说明了什么?
丁小云和王芳立即回答,李大勇在外有了女人呗。
这回轮到我惊异地看着她们了,我说怎么可能?三个人一同反驳我:怎么不可能!
舆论的力量就在于,一个人告诉你一件事时,你可以不相信,一群人告诉你这件事时,你不得不相信。我狠狠地深呼吸了一口,调整突如其来的情绪,然后在三个人的怂恿下寻找早上的那根头发。
它仍然躺在垃圾桶里,一副妖娆的姿势,如我描述的——长长的,金灿灿的。现在,它像一个刑犯被我们揪了出来,正传递于每个人的手中。
刘美红看了一会儿,啧啧两声,说,果真有点故事。
丁小云也对着这根头发端详了很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最后,头发又传递到王芳手中,她没有说话,而是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
2
在交代我的丈夫李大勇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我的工作。我在一家超市后勤部,工作清闲,干一天活,休息一天。这是李大勇的关系,我曾多次提出换个工作,希望自己能像个陀螺似的忙碌起来,李大勇都给予了反对,食指在我眼前摇得像钟摆,他说,嗨,女人千万别像个陀螺似的,陀螺是形容她们的男人的。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陀螺已经飞快地转到北京了。李大勇的单位去年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他也随着大流前赴后继了。刚开始的两地分居,使我们激动不已,小别胜新婚,周末夫妻——一不小心我们就踏进了一种潮流。那些时候,我们分外珍惜这样的感觉,每周两天的相聚便显得格外甜蜜。我们在候车室里等待,告别,拥抱,像电影里一样,把每一次吻别都进行得荡气回肠。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去车站送别了,李大勇说,嗨,没意思,又不是刚分那会儿,都这么长时间了。李大勇喜欢说“嗨”这个字,这是他进了京城之后学来的,说得那叫个字正腔圆。他说,嗨,这么长时间已经没了那股新鲜劲儿了,对吧。李大勇不是征求我的意见,而是表述他的观点,即关于时间的问题。于是我顺着他的观点往下想,对的,时间已经把我们的新鲜劲儿干掉了,时间把我们的思念干掉了,时间还送来了一根女人的头发。
这根头发搅得我几夜未能睡好,原本庞大的空虚已被庞大的怒气代替,当然,这些怒气并没有通过一根电话线向李大勇发射出去,刘美红交代了,这事得当面问,千万不能急。
星期一到星期五,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这期间李大勇打来几个电话,关心我最近还空虚么?我平静地说一点都不,并为自己不显山露水感到得意。李大勇对我的回答表示了欣慰,说,嗨,找点儿事情打发时间嘛。
是的,现在我打发时间的方法仍然是把自己扔在阳台的摇椅上,一同躺在摇椅上的还有那根头发。我已经不再看太阳落去,不再注意远处的钟声,马脸女人是否准时去的菜场……那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星期五姗姗来迟,我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直到李大勇洗漱完毕,才开始了头发事件的审问。这个时候李大勇已经迫不及待地躺在床上,这里的意思我懂。我没有立即呼应,而是严肃地站在他的跟前,于是就有了居高临下的意思。我翻开一本书,那根头发便夹在里面,像是沉睡了一整天,此刻正显得慵懒。我问他这是什么?
书呗。李大勇回答。
仔细看。我命令道。
李大勇伸着脖子又看了一眼,说,嗨,头发,是一根头发。他认真看了一会儿又说,嗨,这是一根女人的头发。然后他又把脸转向我,问,什么意思吗?
我说你说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李大勇像在绕口令。
什么意思你比我清楚。我说。
什么意思我一点儿都不清楚。李大勇继续狡辩。
这的确是一根女人的头发,可这根头发是从你衣服上发现的。我义正词严道。
我衣服上发现的?我衣服上怎么会有女人的头发?李大勇埋着脑袋思索着。
是的,你的衣服上怎么会有女人的头发。我重复道。
嗨,这是个什么事嘛,你就为这事浪费我们的大好光阴。李大勇突然把书扔到一边,把我一下子拉上床。
我推开他,说,你得向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大勇身体翻了上来,一脸笑容,说,好好好,我交代,这是一根女人的头发,它是我衣服上的,我和这头发的主人有染……
这回我是一脚把李大勇踹下床的,那股力气由前几天庞大的怒气合成。我说,李大勇你真的在外有了女人,李大勇你他妈的混帐,李大勇我要和你离婚!
李大勇一脸惊愕,愤愤从地板上爬起来,鼻子喘着粗气,指着那根头发说道,一根头发怎么了?一根女人的头发怎么了?
3
一根女人的头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发现一根女人的头发究竟怎么了?
当我把这些问题抛向刘美红的时候,后者狠狠地批评了我,刘美红说,你说怎么了?这根女人的头发怎么会缠到他的纽扣上,怎么没有缠到我的纽扣上,怎么没有缠到你的纽扣上。刘美红的话使我低下脑袋看自己的纽扣,是的,怎么没有缠到我的纽扣上。当我发现这点时心里又一阵难过。李大勇回来的这两天,就头发事件,我们谈了四次,当然,主要是我谈,李大勇极不配合,所以结果可想而知,我一次比一次猛力追问,他是一次比一次狂躁暴怒。我说如果是没有的事,你澄清一下或发个誓什么的不就行了。这句话就使李大勇暴怒了,他说,我发什么誓,我发什么誓,我凭什么要发誓。
就这样,我们把原本用來亲热的时间都花在了争吵上,也就是说,我拒绝了李大勇。这个时候的求爱举动就是一种贿赂,一个誓言远比一管精液更能使我心安。说真的,我希望李大勇能直面头发事件,或者向我作个解释,比如,在乘公交的时候,前面一位金发女郎蹭到了他胸前;或者,京城的沙尘暴,将地上的一根金发吹在了他纽扣上。诸如此类,但李大勇却采取回避态度,甚至比以往提前两个钟头赶往了北京。
半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刘美红丁小云还有王芳正在我家的沙发上谈论那根头发,突然外面一阵敲门声,打开门,是一个金发女郎,怀中抱着同样金发的婴儿。我问对方找谁?金发女郎说,找我儿子的父亲。我问她,他父亲是谁?怎么会在我家?女郎轻蔑一笑,说,他的父亲是李大勇。我和刘美红几个都傻住了,那根头发从我手上跌落下去。
醒来后,心里堵得难受,起身给李大勇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忙音,拨了很久,终于通了。我说,李大勇你他妈半夜给谁打电话啊。李大勇振振有词:我在谈事。我说有什么事非得半夜谈啊。李大勇回敬我说,你有什么事非得半夜给我打电话啊。我这才想起要说的内容,调整了语气,我要你把头发的事和我好好解释一下……
电话突然挂了,李大勇没等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再拨,已经关机。他的态度使我下半夜一直处于愤怒状态,我冲着墙上的结婚照声嘶力竭道,李大勇,我要和你离婚!
第二天早上,我肿着眼睛去单位请假,我说,家里有点事,必须立即去一趟北京。“立即”这两字也让领导“立即”批准了。出了办公室,正好遇上马大姐,理货部的,闲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在办公室闲扯,内容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日子是如何风调雨顺。听说我请假了,马大姐一脸悲戚,问是否吵架了?我点头。马大姐说,嗨,夫妻间的事就跟货架上的商品一样,弄乱了,再理一理。我一脸严肃,打断她,说,我的货架现在要倒塌了。
4
火车把我送到北京是次日上午。李大勇外出了,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办公室很敞亮,即便如此,也不能使我的内心敞亮。这期间接待小姐进来续了一次茶,送来一本杂志,还问我是否需要她给李主任打个电话?她的笑容使我不舒服,一副趾高气扬。我说不用,我自己会打。
隔着玻璃门我的目光四处搜寻,除了看到一个染着棕色头发的女孩外,一律是黑色。走廊里有人来来往往,我专注地看着那些走路时总能摇摆出声响的女孩,这些使我心里一阵难受。我想李大勇也会这样专注地看她们吗?
李大勇的办公桌一如既往的凌乱,电话机歪在一旁,文件堆了很高,电脑也没有及时关掉,鼠标被不小心触碰后显示器亮了,我看见了QQ里头像的闪动,看见了排列在上面的都是女性头像,我还看到所有的聊天记录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这些被清除的痕迹里曾经都隐藏了些什么……我转过脸,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难受,然后我便看见桌上的相框,一张合影里李大勇笑得得意忘形,还有三个女孩,一样笑得得意忘形,照片下有一行字:工程管理精英团队。是的,李大勇和那些女孩是一个团队,团队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告诉别人,他们是一伙的,他们之间有一种牢固的关系。李大勇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显然我的存在吓了他一跳。他问我怎么在这里?我说我怎么不能在这里。李大勇看了看外面,发现没有好奇的眼睛后,转过身十分不友好地说,你来干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你随便翻我的东西干什么?李大勇的三个“干什么”让我顿时窝火,目光再次睨了一眼桌上的照片,几个人的笑容怎么看都像幸灾乐祸。于是我愤愤地对他说,李大勇,我要和你离婚!
5
在北京的这几天过得很快,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眼天安门和紫禁城,好像千里迢迢就是为了送一句“离婚”。其实,原本我是带着愿望去的,我希望我的突然出现能使李大勇感到惊喜,然后向我解释那根头发的事情。误会,他会说,我可以发誓。是的,一根头发算什么事儿呢,我会捂住他的嘴,不让那些毒誓从他嘴里溜出来。然后我们再一次小别胜新婚,做一场惊天动地的爱。而实际情况呢,我们一见面就交战上了,先是在他的办公室压低火力地战斗,然后又转移战场到他的住所继续战斗,李大勇说我疯了。我说是被你逼疯的。李大勇说我看是你想把我逼疯。我说好吧李大勇,我们都被对方逼疯了,两个疯子还怎么生活呢,我要和你离婚李大勇。李大勇说好吧好吧离婚就离婚。于是两个人比劲儿似的把能砸的东西一律砸向对方。
从北京回来,我感到浑身虚脱,对于离婚这件事,李大勇最终并没有同意。我给刘美红和丁小云王芳分别打了电话,神情沮丧,在电话里告诉她们我去过北京了,李大勇可能真有了女人——三个人挂了电话立即就到了。丁小云说,看吧,男人就是这样,这种事总不能干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刘美红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我要离婚。刘美红问李大勇是否同意了?我摇了摇头,刘美红就激动起来了,说男人都想在家红旗不倒,在外彩旗飘飘,门儿都没有。王芳则坐在一旁不说话,认真听着。其实我特别希望王芳能说点什么,她比我们三个想法多,有头脑,心里也存得住事。我说王芳你说点吧。她听了笑了笑说,唉,说什么呢,真是围城里的人想出来,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我说我不想听这些,然后打断她。要交代的是,王芳至今还没把自己嫁掉。
送走我的闺蜜们,心里明亮多了,仿佛有了坚定目标和明确希望。我现在明白了,一个成功男人身后一定有一个女人,一个勇敢女人身后一定有一群闺蜜。是的,我想离婚,我要离婚。刘美红说,我们女人可以忍累,忍苦,忍痛,但决不能忍气吞声。刘美红说人活就是一口气,这叫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刘美红又说她家的那个,去年和他的初恋女友又联系上了,好在发现早,两人只通了几个电话,要是有什么暧昧举止,她肯定跟他离了。刘美红顿了顿,似乎觉得不解气,说,离之前也要把他那祸根给剪了。刘美红用手做了一个剪的动作。丁小云也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恋爱自由,离婚自由,“婚”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女人头脑发昏干点事儿。她说要是她家那个在外有女人,她也早就离了,离婚有什么不好,离婚自由的意思就是,离婚了,就自由了,唉,我现在就希望能自由。
她们的一番话给了我不少力量,一个礼拜我都显得斗志昂扬,我感到我不是在进行一场离婚,而是一场战斗,战斗的结果必然是李大勇输得惨不忍睹。
周末李大勇没有回来,李小强问爸爸呢?我说,北京,不回來拉倒。然后我又转身问李小强,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会不会不高兴?李小强几乎没有想,就跳了起来,他说,嗨,老妈,你太帅了。他给了我一个熊抱后又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离吧离吧,我早就梦想你们离婚了。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李小强说是啊,我们班很多同学爸爸妈妈都离婚了,他们老幸福了,爸爸给他们买玩具,妈妈也争着给他们买玩具,羡慕死人了。我从地上站起来,说,没心没肺的东西,跟你老子一个德性。
不过,李小强的话还是给了我很大鼓舞。作为奖励我带李小强去了一趟他爷爷奶奶家,晚饭时,我突然有些难受,内心波澜。于是停下筷子悠悠说道,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和李大勇过够了。两个老人看着我一脸无辜,问我李大勇怎么了?我说李大勇在外肯定有了女人,我要和他离婚。他们惊得放下筷子,说他竟有这个
胆子。我顿时咽不下饭,眼泪簌簌掉在碗里。老人立即拨通李大勇的电话,对着话筒一阵光火,说你这个不学好的东西,你有本事了啊。电话那头似乎不太明白,问怎么回事?老头就骂开了,说,你其他本事不学,净学别人找女人啊。李大勇大概狡辩了一下,老头又继续道,说没找女人你周末怎么不回来,你在那和谁厮混呢。
我的泪水与老头的骂声共鸣了,是啊,他不回来,这个时候他会在哪个女人的身边呢?
挂了电话老两口一阵叹气,说怎么生出这么个龟儿子。然后又振作精神安慰我,说,我们支持你离婚,离了婚,我们不要这个儿子,我们要你,让他滚出去!
我也抹了一把眼泪,动情地抱着李小强哭了一阵,说,我要跟他离婚,我一定要跟李大勇离婚!
6
已经三个礼拜了,李大勇没有从北京回来。但我知道,不出四个礼拜,李大勇就会离开那里。
从北京回来前,我特意去找了李大勇的领导。那是我跟李大勇交战后的次日,我的眼睛恰到好处地红肿着,我对那个矮胖的经理说,能否把李大勇调回扬州市场。对方很疑惑,但仍然表示出关心,问我出什么事了?我支支吾吾,我……我们……我和李大勇……我们之间——我用几个含混的词语暗示了原因。矮胖经理似乎明白了,给我一些宽慰,说调离的事需要和经理室商量一下,不过,得等李大勇交接完手头的事情,也是需要三四个礼拜的。我点头表示感谢,并且希望对方不要告诉李大勇我找过他。
三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我给李大勇打过很多个电话,让他就离婚的事给个说法,但电话都被挂断了。我可以理解为李大勇不愿意离婚。刘美红说了,男人都想红旗彩旗一起飘飘。
周末的时候,刘美红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跨进门,满屋子的熟悉。我突然想起上次走进这里都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和刘美红一起织毛衣,一起吃着零食,我们躺在沙发上,好像生活原本就应该如此。刘美红的丈夫李铁柱总是笑盈盈地看着,还为我们及时清倒垃圾。
李铁柱正在厨房里,餐桌上一片丰盛。刘美红朝厨房里喊,李铁柱,给我们拿双拖鞋。李铁柱就噔噔地跑出来了。刘美红又喊,李铁柱,给我们泡杯茶。李铁柱又噔噔送来热茶。吃饭的时候,李铁柱一直憨憨笑着,围裙还没解开。刘美红说,李铁柱去把围裙解掉。李铁柱就去把围裙解了。刘美红说,李铁柱你这个剁椒鱼头做得真是难吃,你把它吃掉吧。李铁柱就埋头苦干起来。刘美红又说,李铁柱你怎么只顾吃啊,把这个菜去热一下。李铁柱放下筷子就兴冲冲地去了厨房。我顿时有些感慨,这些年来李大勇没有做过一顿饭,也没有洗过一次衣服,常常看到的就是他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休息的两天,他会一直赖在那里,躺着看电视,躺着看报纸,让人觉得他和沙发是合二为一的,或者原本就是从沙发里长出来似的。
我对刘美红说,李大勇要像李铁柱这样就好了。刘美红说,嗨,李铁柱有什么好的,好男人多了去了。刘美红又说,男人就跟那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世界就是个超级市场,挑呗,挑个好的受用一辈子,挑个不好的,也没关系,扔了,再挑。我夹了口菜,看着刘美红,停了片刻,刘美红把身子往前倾着,又说,其实,离婚也算是件好事,离了婚好好挑,眼睛睁大点挑。她瞟了一眼一旁的李铁柱,说,我那时就是挑太急了……
7
从刘美红家回来,李大勇已经坐在客厅沙发上了,很显然,他已经“调离”了。
临睡前,我们没有说一句话,李大勇把被子抱到了沙发上,这是冷战,他擅长的。我把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说签个字吧。他没有搭理,而是把脑袋歪向一边,继续拨弄手中的遥控器。我说赶紧签吧,拖着没意思。
一连几天,离婚协议都纹丝不动地搁在茶几上,李大勇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这让我很恼火,第三天的早晨,我以砸碎一只杯子展开了开场白。我说,李大勇你什么意思,你到底签不签,你还真想红旗彩旗一齐飘飘,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李大勇我要和你离婚,我一天都和你呆不下去了!
对于我连珠炮似的说话,李大勇依然不做回应,他匆匆穿上鞋,像避瘟似的甩门而出。我把一只烟缸砸在门上,狠狠骂道,你他妈给我滚!
李大勇“滚”走后,屋子里一片寂静。只要一想到那根金色头发,就犹如万箭穿心,仿佛那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柄利剑,直狠狠地刺在我的心头。我想象着李大勇和那个女人缠绵的姿势,他怎样地把她抱在怀里,说着怎样的情话,她又怎样挑逗或者迎合,然后那些金发就缠在了他胸前的纽扣上……我坐在地板上哭了,好像是第一次这么伤心,顿时所有的委屈、愤怒、疼痛,填满了我的胸腔,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我要离婚,真的,一刻都不能等。
晚上的时候,刘美红丁小云和王芳一同来看我,说是陪我聊天散散心。她们的到来使我一阵感激,牙齿分外颤抖,不得不感叹友情总是比爱情天长地久,比爱情坚不可摧。我和李大勇吧,刚分开一年,之间就出现了问题,而我的闺蜜们,即使若干年不联系,那份感情永不会变淡。
刘美红在客厅里坐下,看着沙发上的被子突发感慨,说,李大勇睡的吧,男人就这德性,除了冷战还能会点别的什么。丁小云也叮嘱我千万不要妥协,离婚是一场战斗,谁疲惫了谁就输了。只有王芳不说话,看着我们若有所思,等大家都说累了,才告诉我们,李大勇下午找过她,说我和他之间的误会实在是太大了,希望王芳能帮忙一下。我说李大勇他妈的放屁,什么误会,非要我捉奸在床吗。
刘美红似乎和我一般气愤,说李大勇这是什么话,王芳你答应他了?王芳说我能答应什么啊,我对李大勇说,你们之间的冰冻已非一日之寒了。我说,对,我和李大勇之间已经冰冻三尺了,我一刻都和他生活不下去了,我要立马离婚,我要和这个男人立马离婚。
我对刘美红几个说,你们看吧,李大勇就是不签离婚协议。我把那张纸拿在手中,内心愤怒不已,我知道李大勇可能会找我的闺蜜,除了王芳,他绝不敢找刘美红和丁小云,后者一定以一个巴掌回赠他。我转身对王芳说,你真得帮帮忙,帮我劝劝他赶紧把这协议签了。
刘美红说,对,劝劝他,赶紧的,他现在是拒签离婚协议是吧,好吧,那就找他的把柄,只要找到把柄,到时他想不离都难了。丁小云拍手称好,然后提供了几个方法供于参考,比如检查手机信息和通话情况,比如跟踪,比如找关系去公安系统查询开房记录……
我的牙齿已经颤抖不已,离婚这个词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这些天我已经不再为头发的事难过了,好像那是多么久远的事情,而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离婚。我每天刷牙时想着,吃饭时想着,坐车时想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时刻都在提醒我:我要离婚。
8
我用丁小云提供的方法小试了一番,鲜有成效。首先我在李大勇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频繁联系的号码,通话时间分布在每天的晚上,累计时长62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每天都要聊上二十多分钟,聊什么呢?他们会聊什么呢?我几乎没有想,便将号码回拨过去,立即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喂”了几声后就挂了——果真有一个女人。
后来我又悄悄登陆了李大勇的QQ,一个显示为女性的头像发来一则信息: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看了很久,不知道如何回复,好久没见面了!是的,李大勇回来一些日子了,他们好久没见面了,多遗憾啊,多相思啊,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其实又是何等的暧昧。
当然,在我做这些的时候,由于激动或者缺乏经验,所以并没有做到销声匿迹,当我再次打开李大勇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所有的记录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这使我很着急,仿佛刚找到的线索又给弄丢了。我只好采取了跟踪措施,因为李大勇常常很晚才回到家中。跟踪的事,也就两次就被他发现了。某个早上李大勇突然掉转头直逼上来,他把包摔在地上,一副愤然模样,他说,你竟然跟踪我,你他妈竟然跟踪我,你究竟想干嘛?我说我究竟想干嘛,你说我究竟想干嘛,我还能干嘛,我就是要和你离婚。李大勇一脚踢开地上的包,说,我们之间到底谁疯了啊,我们之间到底他妈怎么了啊。我长长舒口气,欲言又止,我本想告诉他从那根头发开始,那根头发把我们逼疯了,但我不想再说,他一定会继续狡辩,男人就是这样。再说,现在那根头发已经不能使我难受了,它让我浑身充满了战斗力,我只想离婚,我必须离婚,离婚才能给我一个新的开始,我似乎看到离婚后的日子正阳光明媚地向我走来。我把目光落在李大勇阴沉的脸上,我说,我就想离婚,要不我会疯了。我看到李大勇咬着牙,又咬了咬嘴唇,停顿了很久,才说,好吧,离婚……
我决定回一趟娘家,这个时候,或许应该向父母汇报一下婚姻状况。结婚时是先斩后奏,这一次我希望能遵循先奏后斩。
父亲出去打麻将了,母亲在屋里择菜。我未作铺设,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李大勇离婚了。母亲放下手中的东西,一脸愁容,问出什么事了?什么事非得离婚不可?于是我就简明扼要地说了头发的事情。我说他和那个金发女郎可能已经如胶似漆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会通很长时间的电话,李大勇刚从北京回来他们就说很久没见面了……母亲颓唐着,不住地自言自语,怎么这个样子,李大勇怎么这个样子——我过去抱住母亲,这个时候,她应该比我更需要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没什么可难过的,与其和这样的人生活,不如和这样的人离婚,离婚不是坏事,离婚是重新开始。母亲皱了皱眉,然后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和李大勇之间的事情。父亲大概牌运正处不顺,对着电话喊道,离就离,果真不是个东西,当初我看那小子就不顺眼——挂了电话后母亲依然一阵瑟缩,说,你爸同意了,可是——我打断她,没有可是,没什么不好的。我告诉她有刘美红,有丁小云,有王芳,有李小强,还有李大勇的爸爸妈妈……也就是说,有一群人,有一支庞大的队伍,站在我的身后。母亲似乎得到了鼓舞,抱着我,瘦弱的手坚定地在我背上拍着。
从娘家回去的路上,接到李大勇的电话,这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没兴趣听其解释,掐了,又响,再掐,再响,接通后,李大勇在电话那头咆哮,对的,我想应该用咆哮这个词,他说,我他妈要和你离婚,你他妈现在在哪里,你他妈赶紧给我到民政局来,——李大勇用五个“他妈”表示了坚定,他说,原来我调离北京的事是你他妈干的,我他妈要和你离婚,我他妈一刻都不想等!
我果真一刻都没让他等,挂了电话就打车去了民政局,一切顺利,是的,相当顺利。甚至比结婚还要删繁就简,我们没有财产分割的矛盾,没有李小强抚养权的矛盾,好像两个人共同完成了一件小事,共同看了一场电影,或是逛了一次街。当我拿着崭新的离婚证书时,竟笑了起来,它在阳光下显得那么明亮,那么煞有介事,仿佛是一本开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
从民政局出来,王芳出乎意料地候在门口。我十分惊喜,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真是谢谢你。
王芳打断我,因为李大勇已经站在一侧了,王芳说,嗨,我的闺蜜,不必谢谢我,我只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你托我帮忙,我的确帮了;第二件,你也看到了。她指着身旁的李大勇说,我只是捡了一个你不要的!
我站在原處,没有说出话来,喉咙处像被堵住了,好长一会儿时间,才抬头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地面,最后看着这两个身影渐渐远去……
我把离婚证书放在胸口的口袋里,然后掏出手机,给李大勇的父母拨了电话,这个时候,我想应该告诉他们——离婚的喜讯。电话里一片嘈杂,我说,妈,我和李大勇离婚了。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又说,我正忙着呢,煤气灶上炖着东西呢,我先挂了啊。
我把电话拨向了丁小云,我希望丁小云能和我一起享受这个结果。离婚了,仿佛跋山涉水了很久,终于平坦大道了。电话一直没人接听,过了很久,才通了,我说,小云,我离婚了——啊,丁小云在电话那头发出感叹,她说,终于离了啊,嗨,终于离了啊,改天帮你庆祝啊。我听到电话那头哧哧啦啦的声音,她应该在厨房里,果然丁小云说,我正在做饭呢。我想丁小云如果此时邀请我过去,我肯定一刻都不耽误,现在我多么渴望听到那种油锅里哧哧啦啦的声音啊。我试着问,什么时候帮我庆祝啊?丁小云说,嗨,改天,改天吧,我现在忙死了,我公公婆婆要来做客呢!
我长长舒了口气,在给刘美红打电话前,甚至祈祷了一番,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没等我开口,刘美红就笑了起来,她的笑声总是那么有感染力,那是一种把牙龈毫无保留地袒露在外的笑容。刘美红说,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我也笑了,学着她把声音放得很大,我说,鬼精,都被你猜到了。刘美红一阵惊愕,说,离了啊,这么快啊。我说是啊,离婚不是要速战速决么?对方在电话那头又是一阵猛笑,说太出乎意料了,这是你这辈子干得最麻利的一件事情。我说,小红,你在哪里呢?过来陪陪我吧。刘美红迟疑了片刻,努力要收住笑容,说,我在海南呢,陪着李铁柱呢……
9
我慢慢往回走,一种虚脱感又汹涌在体内。胸口好像很重,好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解开大衣的纽扣,果真是东西压着——离婚证书。我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在路旁的一个石凳上坐下,像阅读一本杂志那样认真,从它的封面一点点地读到封底——申请离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给予登记,发给此证……合上离婚证书,我仰着脑袋对着天空长长吐一口气,冬天的街头萧瑟很多,银杏光秃的枝头杵在天空,梧桐叶落光了,松叶落光了,木槿花叶落光了,兰草落光了……一切都暴露无遗地显现出来,石凳和我都暴露无遗地显现出来……
我没有回忆过去的任何一个细节,也没有回忆和李大勇登记结婚的那天,好像一切都逃遁了,我突然想起《西西弗神话》,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次快到达山顶的时候,由于重力巨石又会滚下山去。现在我就如同那块巨石,被无数的手充满力量和热情地往山顶推去,可是就在到达山顶的时候,那些手不知了去向,我感到了一种无可抗拒的重力。
回到小区,天已经昏黄了。在门口竟然碰上了马脸女人,这是我第一次平视着这张脸,她的脸很清秀,甚至不算是长,往常我站在阳台上看,那张脸像似被拉长了,显得十分怪异。她的眉毛挑得很高,于是便显得神圣和煞有介事。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和她搭讪一下,我走上前,动了动嘴角,说,嗨,买菜去啊?马脸女人十分惊诧,眼睛往四下找了找,似乎没发现声音的出处。于是我又说了一遍,去菜场买菜啦。马脸女人终于呵呵笑了,说,买菜,是,买菜,每天都去买菜……
和马脸女人分开后,我回到家中。现在,我依然把自己扔在阳台的摇椅上,头顶的那块天空正逐渐暗淡,是的,这个时候,总是会发生点什么:太阳正悄悄落下,远处的钟声敲响五次,马脸女人正走在通往菜场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很多天前的那个日子,我也坐在阳台的摇椅上,为一种无所事事和空虚发愁。这么久过去了,我又坐在了这里,似乎一切都变化了,又好像,这一切从没有变化……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