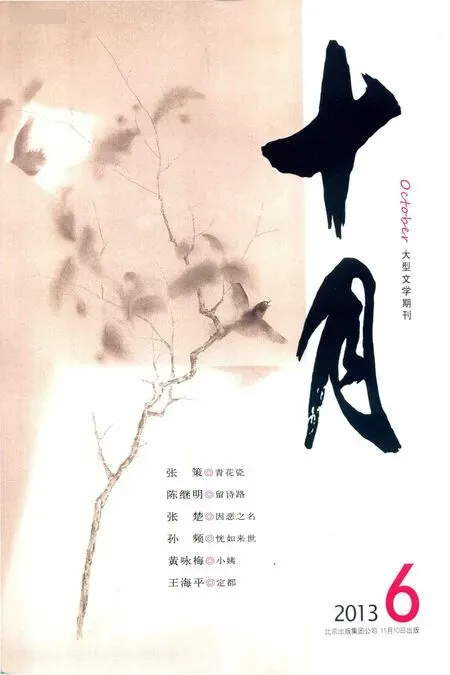雨水集聚这个黄昏
樊子
悲歌
丰子恺在谈他画画时说他画过两只羊,两只羊
的脖子上
都拴上了绳子,其友人批评此种画法不妥
现实中,在羊的世界里
头羊的脖子上只消有一根绳索
就足够了
丰子恺很后悔
我不以为然,丰子恺应该给两只羊画三条绳子
如果他不死得过早
在中国,他应该不停地画绳索
我不喜欢那种把绳索画成血淋淋的样子
中国画家至今没一个人能把血淋淋的样子画成
绳索
真实
老墙斑驳的语录边,
常有狗跷起后腿倚墙撒尿;
这种场景我看不舒服,
偶尔会扔几块砖,通常情况下
砖是砸在老墙上,
砸在白石灰写的汉字上。
广场
我是一个爱国者,数着广场上的人群
雕塑、栅条和铭文也有着同样的喧哗
众多的山巅倒向了河流
众多的河流流向了山巅
这样的时代,诘问总是唯一的弱智
大地上站着癫痫者
他丢失了麦芒与稻穗
他是伟大的乞丐,他说出忠孝
他是我的父亲,有着我儿子一样的血液
雨水集聚这个黄昏
雨水集聚这个黄昏
在一个有墓志铭的山冈
我捡拾药草才能知道昨夜是漆黑的
昨夜很多星光在睡眠中死去
我总要在黄昏时分,爬坡、深呼吸、亮开喉咙
向人群询问他们一天的荣耀
那些漂过河床的死猪和舒卷长天的鹰
都是我询问的对象
这是被雨水淋湿的黄昏,毕剥燃烧的
依旧是树叶、草芥
架起木材,煮陶器中的雨水
被我礼赞的善良
和那些有细微裂痕的信仰
是有波浪的火焰抛弃了我们
冬日的工业园
在这片寒冷的冬季
肩膀扛着一根废木
遇到漫天的沙尘
我在一个命名为工业园的地方坐下来
这片寒冷的土地,众多的树木
面临休克状态
疲惫的火车整日像个奴隶
一节节车皮把煤炭卸下,又
一节节装满再卸下
这些城市依靠煤炭烤火
烤烤僵硬的躯体和虚弱的表情
一些枕木断了,一些钢铁弯曲了
疲惫的火车整日像个伟大的僧人
我肩膀扛着一根废木
在帝国的工业园,看见
银杏树、水杉和烟囱一样挺拔
黎明的白色牛奶
要是放在黑夜里还是白色的
我就相信一些谎言
当废木成为枕木、成为精美的根雕
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我只是一个工匠,一个有手艺的工匠
用锈迹斑斑的工具刀在手臂上刻下:奋斗!
在冬日的工业园,桫椤树塑料模型
挂着一盆吊兰
我只有肩上的一根废木
当卸下这根废木,拿起刨子、铁锤和锯
在废木里找自己的锁骨
喧嚣的工业园向来寂静无声
田畴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高粱能够和向日葵
一起生长,包括
那些赤练蛇、芨芨草
我目睹秋天的田畴变得辽阔而高远
高过不远处的山峰
我在山峰上远眺
辨认村庄的方向
哪颗星辰能够没有炊烟
哪颗星辰能够没有高粱的根须
一节节
蓄满阳光与风的声音
冬
西北风刮起的日子
土地在睡眠
雪落下的时候
睡眠的土地允许田鼠咬破自己的胞衣
还有河流,它们刺骨的
脾气里有阴霾的云朵和丑陋的沙石
还有苦楝树
枝丫压满西北风撕裂云朵的呐喊
我们对冬天的理解变得如此肤浅啊——
云朵的呐喊声还没有止息
村庄四周遍布青青的麦苗,那么多幼小的麦苗
被雪罩着
被西北风粗粝地吹着
抱起
我若神思恍惚,不是我见到了什么不净之物
我在夜晚听到婴孩的啼哭
他还不懂得黑夜用来睡眠
我如果也像婴孩一样在深夜恸哭
谁是我的母亲?
在干燥的土地上,不为悲楚,只想哭一场
一块土地会抱起另一块土地
像尸体一样轻盈
一个人扛起我的下颚,他只能
扛起我的下颚
他在搬运,他是熟练的车工
他有螺丝刀、铁钳、锤子和显微镜
他还有一台锈迹斑斑的苏式车床
在我居住的房子里,他老了
现在他练习焊工,正好停电
他用锤子打开一块灰砖,感觉
真的奇妙,这座房子
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成为门
他不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可能
把自己儿子的颧骨敲碎
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肚子放进自制的炉子里
他喊来四个人,从一个方位抬起我
他自己只扛起我的下颚
他们一起要走很长的夜路
四个人有说有笑
我属于这四个人:心脏、肺部、眼珠
和弯曲的四肢
这四个人朝一个方向走
只有扛着我下颚的人嘴里不停地罵着粗话
他流着鼻涕
黄色的牙齿有过太多的罪孽
我知道他哭了
他偷偷转身走向那座已消失的房子
他忘记带他的螺丝刀、铁钳、锤子和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