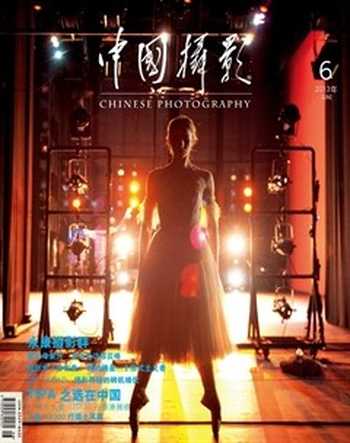我和三江源
郑云峰



一
我和三江源的缘分,要从20多年前说起。
1982年,我还在徐州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一次赴青海出差,让我有机会到三江源地区走了一趟。这次高原之行虽然很短暂,不过是匆匆一瞥,而且到达之地离江河源头还很远,却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我正在摄影之路上苦苦摸索,经常陷于无所适从的困惑——到底应该拍什么?怎么拍?摄影的意义是什么?三江源地区无法穷尽的魅力,深深地震撼了我,再加上我从小生活在黄河故道旁,对黄河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要拿出几年时间,全力拍摄黄河源,进而沿河而下,拍摄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完整历程。当时的目标很单纯,就是通过拍摄,弄清楚这条大河到底怎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这也是我为自己的摄影之路初步定下的基调。
返回徐州不久,我向组织递交了《关于自费拍摄黄河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提出了自己的拍摄计划——用五年的时间,为母亲河留下一份相对完整的影像记录;至于行程,我粗略估算为三万里。
正式出发赶赴黄河源时的心情,至今仍然清晰。我为此行激动不已。 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得知我要去河源,特地为我题字壮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并且谆谆叮嘱我,要“拜牛为师,一步一个脚印,为母亲河写真立传”。我把题字刻在一块石头上,决定将其竖立在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
二
盛夏季节,我开着一辆旧吉普,从骄阳似火的徐州出发,一路奔波,抵达位于曲玛莱县玛多乡的黄河源头。
在玛多,高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气的变幻无常、忽冷忽热、忽晴忽雨自不必说,最让我难受的是强烈的高原反应,一向身体强壮的我,竟然头晕目眩,胸闷气短,夜不能寐,日不能食,嘴唇干裂,一说话就冒血珠子。从玛多到黄河源头,不足160公里的路程,竟然用了整整三天。
我领略到了高原的严酷环境,但也被一种全新的体验所包围。
原本在我的想象中,黄河源头应该是激流奔涌,气势磅礴,没有想到,那竟是一条条冰雪融化后的小溪流!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母亲河就像温顺的少女,一言不发地默默流淌。在日思夜想了无数次的黄河源头,我再也无法忍住内心的激动,趴在地上放声大哭
随后几年,我又费尽周折,去了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如黄河源头一样,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带给我的震撼无法言表,我能做的,只有赞美和膜拜。
从那时到现在,我先后数十次抵达三江源头,除去扎根三峡、抢拍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影像的七年,我基本上每年都会赶赴三江源,对三江源区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宗教文化、民间艺术和风俗民情等进行全方位的采访和拍摄,共计拍摄了20多万张照片。
在拍摄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三江源不仅是三条著名大江河的源头所在,更是中华民族赖以诞生、发展的根基,没有三江源,就没有中华民族,而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坚韧品格,在江河之源就已经显露无疑。
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拍摄时有了一种越来越急迫的感觉,因为三江源的整体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如果不能赶快拍下来,子孙后代们就无法知道,滋养了中华文明生命之根的三江源,曾经是怎样的一副面貌。至此,所谓的“艺术”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回到了摄影最基本的道路上,那就是记录。
如今,将近30年匆匆过去,看着眼前数不胜数的照片,而自己依然感觉需要继续拍下去。我不由地慨叹,当年何其轻狂,竟然如此严重低估了这项事业的艰难程度和时间跨度。而且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段夹杂着喜悦、激动也包含着太多痛苦和焦虑的历程,竟然彻彻底底改变了我的内心,使我对所谓“摄影艺术”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
拍摄三江源的最初几年,给我震撼最多的,是高原上的伟大生灵和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
在三江源,许多地方都是人类的禁区,却是无数野性生命的天堂。它们相互依偎,繁衍生息,与河流、草原、神山、圣湖和谐相处。
在这片高寒之地,生命不仅美丽,而且伟大。无论是在风雨中挺立的的野花、野草,还是在大雪中飞奔的羚羊、野牛,每一种生命都美得惊心动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为生存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磨难。
……
在三江源,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宗教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行走在高原的无数日夜,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我拍摄了很多嘛呢堆的照片。在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新寨村,有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嘛呢石堆,那里堆砌的嘛呢石多达25亿块。这些数量惊人的嘛呢石,是无数僧人、信徒在长达几百年的漫长时光里,用双手一块一块雕刻出来,再一块一块搬运到这里来的。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一切全部出于自愿,出于虔诚的信仰。
嘛呢石上刻着的,是每一个藏族同胞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哞”。你可以在嘛呢石上看见它们,可以在经幡上凝视它们,也可以在转山者的口中听见它们。
我拍摄了很多转山者的照片。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那些络绎不绝的转山者,有的一人独行,有的全家出动,冒着风雪严寒,用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一步一个长头,用身体丈量着神山的周长。他们转山,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祈福消灾,更是为了向这圣洁的神山表达无上的尊崇和敬畏。
三江源深厚的宗教氛围深深吸引了我,从1985年至今,我几乎走遍了三江源区的大小寺院,拍摄了异常丰富的宗教活动及习俗照片,和许多僧人、信徒成了很好的朋友。
……
四
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黄河源头的玛沁县,我碰到了下山采购生活用品的藏民先加。先加请我喝他随身携带的青稞酒,并邀请我去参观他的牧场。我们素昧平生,但先加的热情令我十分感动。
先加的牧场在阿尼玛卿雪山主峰玛卿岗日的脚下,海拔5800米左右,到达那里很不容易。
夏季是是牧民最繁忙的时候,他们赶着牛羊从山下逐步向山上推进,从一个山头搬到另一个山头,寻找最嫩绿的草场;8月底9月初,山上气温下降,逐渐变得寒冷,青草也变黄枯萎,他们又赶着牛羊从山上往山下转场。先加和他的祖辈们一样,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游牧的生活,在雪山和草原上四处辗转。
我曾经跟着先加和他的大儿子一起去放牧,那是一个大雪天,十分寒冷。他们赶着400多只羊和100多头牦牛走在路上,羊的颜色和天地间的白色混在一起,几乎无法分辨清楚。风把雪粒摔打在人的脸上,又冷又疼。我穿得很厚,仍然冻得浑身哆嗦,但先加的穿着却和往常一样,简简单单一件藏袍,谈笑自若。不久,我的靴子里面就被灌进去的雪弄湿了,我一边艰难地行走,一边疑惑:大雪纷飞,牛羊去吃什么呢?
雪渐渐小了,先加一声唿哨,牛羊顿时停住,纷纷用嘴巴拱开积雪,地上露出的湿漉漉的青草便成了它们的美味佳肴。
先加还曾带我去看冰川。我们穿过一条冰河,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崖,钻进一个七八米高的冰洞里。向外望去,一排冰挂从上面垂下来,在洞口形成一道天然的冰帘。透过冰帘,湛蓝的天空中,除了洁白的云朵,不见一丝杂色,阳光照在冰挂上,幻化出五彩的颜色,冰凉的融水滴滴答答,在地上汇成股股细流。
先加告诉我,我所见的冰川不过是阿尼玛卿冰川微不足道的一角。那些古老的冰川,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模样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新的冰川又在不断形成。
从冰川返回时,一个藏民与我们擦肩而过,他的神情十分肃穆,从我们旁边经过竟望也不望我们一眼。先加说,那是前往高处的冰川朝拜山神的信徒。我盯着那人的背影看了很久,直到他走出我的视线。
在先加的帐篷里,我一共住了八天,壮观美丽的阿尼玛卿、巨大的冰川、擦肩而过的信徒、风雪中的放牧、艰辛而又充满乐趣的生活,以及先加待我如兄弟般的热情,都让我永生难忘。
五
将近30年的时间,我几乎走遍了三江源的每一个地方,许多地方都不止一次抵达,但每次去,都会感觉有所不同。一切都改变了,曾经出现在我照片中的那些身影和面孔,儿童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青年变成了壮年,而当年的壮年已成白发苍苍的老者。草原和雪山的容貌也变了,变得认不出来了。不错,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住上了更好的房子,有了电视机、摩托车甚至汽车,但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却变坏了。这种矛盾的感觉,让我的内心越来越沉重。
我曾经带着20年前拍摄的照片去寻找先加。那是2005年8月25日。在阿尼玛卿雪山玛卿岗日主峰下,我一眼认出了先加,先加却有些迟疑,但是很快,他就面露惊喜地伸出了双手。
先加依然放牧,但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也已经结婚生子。我遍视四周,不见先加的妻子才保,先加说:“她背水去了”。上次来时,她背水只需走上几十米,现在却必须走两三里路,因为附近已没有可饮用的水源。
我难过得长久不语。
我拿出20年前的照片,请先加带我再去看一看。先加盯着那些照片,一边看一边叹息:“湿地没了,冰川小了,好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了……”
当年丰美的草场上,现在到处都是鼠洞。先加说:“草没了,沙多了,老鼠出来了”。在先加住宅附近,我特意数了数,一平方米内竟有26个鼠洞。迅速繁殖的鼠兔改变了草原的土壤结构,破坏了深层钙积土,继而破坏植物生长、水土保持,形成“黑土型”草地,最终加速了沙化。
玛卿岗日峰下,白水河混浊不堪,而在20年前,但凡河水漫过处,鱼儿、石头、砂砾皆清晰可见。
我把镜头移向冰川。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角度,我一眼即可看出冰川比20年前小了许多。冰川已经融化,露出了褐色的裸岩。我问先加:“将来冰川没了,你的孙子喝什么?”先加说:“别说将来,现在还不是守着水塔到远处背水喝?”
许多事物都改变了。
也有不变的——先加还是喜欢对着镜子拔胡须。20年前,我看见先加用手拔胡子,就送给他一个剃须刀。20年后,先加仍然在用手拔胡子,他说用不惯剃须刀。
先加还是用酥油将黄蜜腊、红珊瑚、绿松石粘在山石上,向神山表达着他的虔诚。
先加还是不停地告诫外地来的游人:“不要乱丢垃圾,不要弄脏圣水。圣水没了,一切生物就没了。”
……
辞别先加,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鄂陵湖与扎陵湖畔。
两湖间的一些海子已经干涸。鄂陵湖畔,我把镜头对准莫名死亡的湟鱼,欲哭无泪。而在20年前,被我收进镜头的是人们晾晒在湖边的千万条暗红色的湟鱼鱼干,以及远处碧波荡漾的湖水。
新拍出来的照片上,还增添了一种醒目的黄色,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觉得很美,但实际上那是草场沙化的证据,是“美丽的谎言”。
青海湖也是如此。20多年前我拍摄的青海湖照片,画面上的湖水一片青蓝色。如今的青海湖水,有些地方却五彩斑斓,那是成片浮在湖面上的藻类,显然水质变坏了;岸边沙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之相应的是,近20年来,湖面的面积萎缩了一百多平方公里。
有人预测,青海湖的宿命是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我祈祷它仅仅是一个预测,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六
20多年前,我在花石峡候车时遇到一个从外乡回家的藏民,我问他在外面最想念什么?藏民说:“雪山冰川,草原,牛羊,家人。”我又问:“难道雪山比家人还重要吗?”他说:“当然,没有雪山冰川哪来的草原?没有草原哪来的牛羊?没有牛羊哪有人?”
在三江源拍摄的日子,这句话长久地在我心头萦绕,它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三江源,也理解了三江源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生死相依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在照片中表达人与家园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摄影应该负有更深层次的责任和使命,那就是忠实的记录和展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三江源、爱上三江源,为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乃至保护地球家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用前后将近30年的时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用相机记录了三江源的美丽与变迁。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如今我已不再年轻,但我对三江源的热爱丝毫未减,而且越发深沉。从情感上,三江源早已成为我心灵的家园。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把自己炼进了这些照片里,我觉得值了。
……
最后,我要向我的精神家园三江源深鞠一躬,感谢你怀抱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草原和每一个生存其中的生命,是你们让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