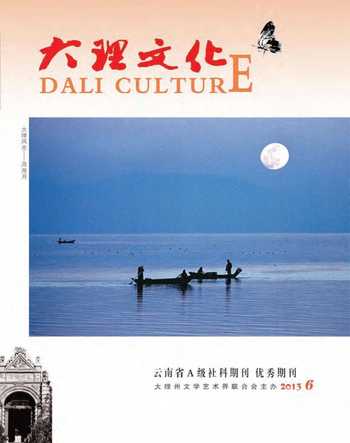母土博南(组诗)
赵振王
木莲花
莲花,被撑天的树
托出一种高度
宝台山。每朵莲花上
都坐着一个佛
莲瓣。像暖暖的冬阳
照着进出不辍的人
我在佛之下缓缓穿行
佛看着我。我却看不见佛
每逢闰年。异常的十三个莲瓣
验证了植物的灵性
莲花开过。就要凋零
佛却永恒地活着
虽然,我看不见佛
佛却活在我心里
山风。在金光寺的屋檐
推着风铃。虔诚念佛
故事在铃声里开始
也在风中结束
百丈冷门庭横开竖劈
一条穷性命东掷西抛
佛看得见一切
一树树莲花绽放
为佛提供一个个打坐的灵台
我的泪水,是佛的汗珠
沿着故事的流向
讲述人间喜怒哀乐
太多弯路。纷嚣的凡尘
在宝台山。却遇到了
属于自己的那尊佛
绕行在洗身池畔
仅仅用了瞬间的功夫
佛就举过手臂
为两手空空的我放行
只要呼吸着。我必行走
绝不放弃……
古道
古道,是汉代
扔过来的一颗石子
留在滇西大地的抛弧线
血汗的颜色和质地
构成弧线的基本元素
这颗石子,飘落在
我的目光前。上千年的马帮
就在视线里来来往往
浩浩荡荡,大声大气地说笑
盖世的勇气。就把粗糙的石板
打磨成一面面铜镜
悠然的马尾。摇来摆去
那是马锅头爷爷,爷爷的爷爷
微笑的一种样式
留给子孙的不动产
在世袭的精神脉道里
均匀地传接
汗水,灰浆状地落入石缝
粘结着石板与石板
至今,丝毫不松动和脱落
石头紧抱着石头
言说古道的坚韧与不朽
我的诗歌,属于马尾巴上
跟随着的一只苍蝇
或者蚊子。之于祖先
与古道无与媲美
仅此一滴汗,一支小曲
一滴鲜血。或是
熟睡中,震天的鼾声
花桥
花桥。在人们的遗忘中
被一面斑驳而立的墙
把高龄的博南县
用缓慢泛香的稻花
留在古驿站,苍老的瓦当上
指点比自己年轻的元梅
博南的县址,活成千岁老翁
以遗址的方式
在南方丝绸之路
打更报晓,让马铃声
具有秩序感
古道。虽然残破不堪了
纵向地端详和品味
却安然无恙
花桥,把史书中
关于博南的那些章节
记录在竹简以外的册子里
写得像诗。更像长长的马队
头骡的头顶上
那个艳丽可以辟邪的花笼
在千年古道上
不甘示弱
马锅头。和他们的马帮
不知疲倦地行走
来来回回走着的路
留下的遗迹,成了耐读的风景
汉代到民国
热气腾腾的古驿站
在花桥。显着人脉力量
古道。断裂过
斑驳得像一块块伤疤
辨认不清哪是刀伤
哪是枪伤,哪是被虎狼撕咬过
已经无法复位的齿痕
古道,有太多的伤痛
让子孙们痛哭流涕
哭声。成为怀念的音符
在花桥回放,任何的模仿
都是蹩脚的作秀行为
万马归槽。才是原唱的歌星
元梅树下,倾听阳光
经久不息地吟诵声
飞跃而来的梅影
标出六百年寿辰的亮度
我在元梅脉脉含情的双眼里
读懂了博南县
千年常胜的骄人业绩
杉阳
杉阳,被千年马蹄子
紧紧拥抱着,透不过气
柔言细语。让人脸红心跳
不知所措之中
闭上双眼,猜想爱的过程
侧耳,聆听古镇的气息
澜沧江的涛声
成为杉阳的呼吸
博南山。挡不住这种气势
势如破竹地前行
可以断言,马尾巴上的苍蝇
是马锅头留下的伏笔
高速发展的运输业
让马们散失了
长途驮运的功能
它们依然活着,三三两两
尽情地吃疯长的青草
古镇的石板
透亮得可以做镜子
遥远的马蹄声,响在镜面上
羞羞答答地微笑着
多像马锅头爷爷的夫人
我奶奶低头掩面时的样子
镜面里,领舞的人
哼着彝族风味的小调
调子的所有元素
被马粪、马尿浸泡过
保留下来,古朴而抒情
杉阳。站在马蹄声前
无言以对。高速公路上
我扔笔潜行,张口结舌
悄悄到达某地,有话想说
可我是晚辈。晚的不是朝夕
晚了好多个年代
银江河
曾经的银龙江
流淌在徐霞客游记里
流域。超不过一百公里
冒了几百年的热气
依依不舍,注入澜沧江
何年、何月,被易名银江河
查不到。不知是谁的主意
很笨。把“龙”削去
这理由,强词夺理
何时的县人大的某次会议
能够为一条龙
恢复名义
从江到河,气势减弱
流水却不枯。我从小的水性
就靠银江河漂洗、打磨
忽隐忽现中。就成一条鱼
在河里,不知深浅地游
顺流或逆流。直线或拐弯
难不住一条或一群鱼
水势。渐次强大
截流了的澜沧江
伸出巨大手掌
堵住银龙江的嘴
不让爽朗地说话。开心地唱歌
银龙江。款款流着
流在徐霞客旷世的游记里
不改奔涌的性格
文字间,从小溪到小河
再到江的样式
一直在汉字的凝固状态里
奔腾了四百多年
曲硐
曲。是形式
硐。是真实存在
曲硐,是一个民族
实际的存在
灵魂的存在
小狮山顶。透亮地写着
有关曲硐的来历
拜塔脚下。暗藏玄机
神秘的洞穴,犹如脐带
连着博南与永平
曲硐,温泉氤氲
一个民族蒸蒸日上
在几度成为县城的边地
不用查籍阅典
徐霞客游记里的曲硐
水雾般弥漫
曲硐。用质地极好的丝绸
缠绕住古道,让博南这个段落
用马铃声,温暖史册里
所有死去活来的文字
汽车喇叭,激活千年驿站
等待火车汽笛
进入永平,抬高由来已久的音阶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