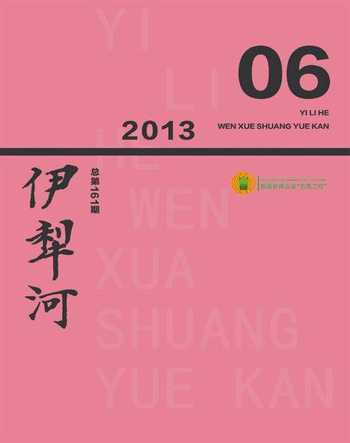新疆大地(外二篇)
黄毅
对于任何一个辽阔的疆域,我们的认知总是从与它相像的形体上找到启迪。
如果有人把新疆比喻成一枚胡杨树叶,那么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便是它的叶脉,所有的养份通过叶脉的传输进入,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就显得丰肥妖娆,郁郁苍苍。
新疆的地貌,被简洁地概括为三山夹两盆,而多少人更喜欢形象的比喻。
诗人说,天山是一只金雕,南疆和北疆是它一双巨大的翅膀。因此在新疆,常常有扶摇九天的感觉。
诗人又说,以天山为书脊,新疆是一部打开的书,南疆和北疆舒展辽阔的页码。因此在新疆,往往有阅读的冲动。
在新疆,只要你不要关闭触觉和感官,就会遭遇截然不同的美。冷峻的冰峰对应着热烈的沙漠;碧绿的草原唱和着苍黄的戈壁;咆哮的河流诱惑着龟裂的河床;茂密的森林遥望着不毛的荒原;丰饶的村镇对视着凄清的故垒;柔美的湖泊反衬着铁硬的山岩;宽容的绿洲拒绝着肆虐的风沙;火洲的太阳辉映着帕米尔的冰雪;浪漫的伊犁回眸着古典的喀什;海拔7435米的托木尔峰俯瞰着低于海平面155米的艾丁湖……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立和统一,这是多么丰富而独特的景观。
新疆把最赤贫的戈壁、荒漠呈现给你,把最富有的石油、煤炭、黄金藏匿起来;最贫瘠的土地里,生长出最甜蜜的瓜果,烈日风沙中出落最漂亮的姑娘;最苦涩的盐碱水让人清醒,最甘醇的马奶酒又让人晕眩;狂烈的沙暴会让人粗糙,柔曼的温泉又让人细腻……新疆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反差的综合体,把它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汇集起来,却找不出更恰当的话来概括她,这是一种大美,超乎寻常的美,而美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简单表述清楚的。
丝绸之路是指在古代交通史上,东起西安、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一直通往希腊、罗马的陆上商贸大道。这条全长七千多公里的亚欧大通道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玉门关、进入新疆境内,然后又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北道从敦煌出发,经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沿伊犁河谷,楚河流域西行,到达东罗马帝国等地;中道沿天山南麓西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在喀什与南道会合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诸国;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若羌、且末、民丰、和田、莎车等到喀什与中道会合。
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线路,仿佛是新疆大地上绵长而柔韧的琴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出时而激越、时而幽怨、时而低回、时而迸发的乐音。
丝绸之路曾是联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家的纽带。在丝绸之路的要冲诞生了至今影响着亿万人思想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古代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发明和思想流派,首先是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了全世界。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丝绸之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和推动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
有人用诗化了的语言赞美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象征着以许多民族的智慧作为梭子,来回往复地交织着这片由东西文化交流而成的、雄伟绚烂的织锦。”
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从来就不是昨天才发现的新世界,众多的文化遗存,黄沙下昔日辉煌的王国,散落在四处的历史遗迹,都足以证明新疆与世界的交往更早于中原,她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融汇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从而派生出自己独有的人文气息。
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甚至祆教、摩尼教等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和中国内地的。佛教从印度传入新疆后,形成了于阗、龟兹和吐鲁番三大佛教中心,并由西域传向敦煌、长安和中原地区。
在尼雅出土的织锦上,我们读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样近似于预言的文辞;在楼兰发现的木简上,我们惊诧于在这个世界已经消失的佉卢文;在龟兹佛国,鸠摩罗什的诵经声仿佛仍在群山中回荡;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飞天伎乐把我们带入佛天佛地……
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内地在新疆获取了精神的食粮,新疆在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传声筒。她融合、杂糅了一切外来的声音,又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质贯穿其中,从而创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大文化。
在亚洲中部这个被高山环峙的大舞台上,历来上演着各民族、各色人种角逐的剧目,真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台。匈奴、柔然、突厥、蒙古、回鹘等这一串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主角。直至今日,新疆仍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共存着47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汉、哈萨克等13个民族为世居民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疆是中亚腹地一个永不谢幕的人种博览会。
众多民族的构成,带来的是绚烂多彩的民族民俗风情,从来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新疆这样,同时让你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得到满足,你会看到无法用言语描绘的色彩,你会听到仿若天籁的乐音,你会品尝到让人垂涎的美食,你会闻到令人窒息的芬芳,你会触摸到远古和现代……这是调动所有感官的一次盛宴,是一种全方位的精神大餐。
从维吾尔人的十二木卡姆,我们看到了喀喇汗王朝的背影;从哈萨克人的阿肯弹唱,我们寻觅着古乌孙人纵马草原的浪漫;从蒙古人那达慕大会上的角力,我们找到了东归英雄的气概;从锡伯人的控弦搭箭,我们体味着箭乡儿女西迁的艰辛;从塔吉克人翩翩的鹰舞,我们追索着太阳部族对自由的向往;从《玛纳斯》英雄史诗的传唱,我们领略了柯尔克孜人对先祖功业的追怀……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新疆的不同凡响,都决定了她具有一种涵盖万物的超级美,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美。
新疆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丰富与独特,就在于她对各种美的因素的综合,就在于她的博大精深和兼容并蓄。
中国,这个美的国度,因为新疆而有了特别的韵味;新疆,这个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大地,它的份量足以使雄鸡的版图高高扬起骄傲的花冠。
生为新疆人
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新疆人是与我们熟知的广东人、河南人、上海人有着完全不同内涵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新疆人基本等同于少数民族。而生于斯、长于斯或已在新疆混迹了若干年的地道新疆人,却有着自己的解读:新疆人就是新疆人,而不仅仅也不应该是某几个少数民族的别称,不管是这里的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只要认定这里是故乡,(不管地下是否埋葬着亲人的骨殖)只要敢于把身家性命交付给这里,只要热爱这块土地并坦然而诗意地栖居,只要舍得把一生中最重要或最漫长的时间都抛掷在这里,都是新疆人这个大的概念里的一员,即使新疆的汉族人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与内地的汉族人有着较大的区别。新疆人的心理、言行、观念、准则甚至人生观有着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属于这个地方所有人群独有的共性。
新疆孤悬关外,是一个远荒遐塞之地,所谓心远地自偏,不仅仅是指一个远离主流社会的遥远带给人的空间隔膜,也是说对人心理上造成的疏离感。有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老新疆人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去了北京,回来后羡慕不已的乡亲们问他北京怎么样?他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显然这个吉木萨尔人说的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关乎空间距离的偏僻,而是在说他在那个完全陌生的情境下一种心理的感受,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生活的地方为圆心为参照,进而来衡量他与这个世界的距离,北京的繁盛,恰恰反证了新疆人内心的荒僻,而说北京偏僻则是一种新疆式的悖论。
新疆占到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那里动辄几百公里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常常让那些第一次来新疆的人张大了嘴,新疆有不少可以号称世界、中国之最的东西,生活在这样一个雄山大水的地方,眼睛能装得下多少,心胸自然也能盛得下。据说作家周涛某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就曾说:我看北京人、上海人未必都见过世面,也不都是大地方的人,连新疆那样的大地方都没去过,怎么能算见过世面呢?
每一个新疆人都应该感谢新疆,是它赋予了我们不同凡响的气质。新疆已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用大大小小的事情,用一切可以感受到的气息,用所有不可捉摸的预兆,用潜移默化的影响,用大美不言的缄默撞入我们的眼瞳,侵入我们的肌肤,流入到我们的血液,植入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呼吸是新疆式的呼吸,我们的心跳是新疆式的心跳,我们的思维是新疆式的思维,我们的行动是新疆式的行动,我们的心胸是被新疆的广袤无际拉扯开的,我们的激情是被新疆的骄阳点燃的,我们的想象是被新疆的瑰丽诱发的,我们的豪迈是被新疆的大山大水激发的,我们的粗犷是被新疆的淳朴民风铸造的,我们的铁血柔情是被新疆的物候所培育的。我们是新疆土著,作为一名新疆土著难道有什么错吗?相信有不少人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诘问:你是哪里人?答:新疆。问者除满眼诧异眼眸里更有许多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我知道你们还没有说出或者还想探问的是什么,在新疆人看来那也算问题吗?简直就是无知甚至是白痴。我们一定要自卑吗?是的,我们有许多不如人的地方,比如楼没有别人高,灯没有别人亮,钱没有别人多,车没有别人靓,可我们有占到中国六分之一版图的辽阔大地,有最长最高的山脉,有最大的沙漠,有最抒情的草原,有最美丽的森林,有最迷人的湖泊,有最奔放的河流,有最多的民族,有最多的传奇,有最丰富的物产……难道我们需要自卑吗?当他们的大奔宝马喝着我们的石油恣意纵横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自卑我们的迟缓吗?当他们穿着我们的棉花织成的流行时装招摇过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土得掉渣呢?当他们用我们的天然气烧出粤菜、湘菜、杭帮菜,吃饱了打出满足的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卑我们的饮食文化吗?
我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但我是一个认真的人。生活在边地的人似乎都有些委屈,而这些委屈多了,时间长了,往往就让人变得坚韧。一个人生在哪长在哪,既是宿命,也是必然,我一向不认为一个美国钉皮鞋的修鞋匠,比新疆沙漠中和田的玉石鉴定家更尊贵更幸运。
一个人对大的偏爱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养成的,比如新疆人在餐桌上的以大盘鸡为代表的大盘系列,表现出的就是对大的追捧,某种程度上是对阔大土地的一种回应,以餐桌上的大昭示那块土地对新疆人性格形成的巨大影响;而新疆人对小的回避,也是一种内心矛盾的外化,新疆人阳光且阳刚,慷慨而大方、干脆而感性,同时极好面子,也有那么一点点虚荣,在看不起一切猥琐宵小的同时,也最怕别人小瞧,用大来掩饰某一方面的小,甚至有用大来吓唬人的嫌疑,所谓的以大壮胆,正是这种写照。
我们是新疆人,新疆人是有理由也可以自豪的。
走进天山
在新疆,能在仰俯间随处可见的,是太阳、月亮,再有就是天山。
只有那种超越了一般形体意义上的庞大之物,才会把超远距离造成的视觉困惑,留给人类。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看一看日月和天山,这时才明白,渺小的我们习惯把那些司空见惯的庞大之物排除在外,或者视而不见,但我们不管身处何方,都逃不出它们的视线,哪怕日月小到只有指甲盖那么一丁点,哪怕天山模糊到只有莫合烟头那么一小节,它们总是在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不离左右,在它们一如既往的注视下,我们从远古走到了现代。
在天山的注视下,张骞的凿空西域有了参照;在天山的注视下,丝路驼队划过的优美曲线有了对应;在天山的注视下,乌孙人、匈奴人、突厥人还有塞种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了时空感;在天山的注视下,开凿克孜尔千佛洞的叮当锤声,就有了苍茫感……
有多少伟大的人物,目光都曾与天山遭遇,他们肯定和我一样,在一刹那间就会被征服,不管他的内心多么强大,也不管他多么自信,因为没有谁能够看透天山,哪怕穷尽一生的时间,而天山只须一下就把我们看个透彻。
那是谁说的,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爱山本身就是一种境界,爱天山可能就不仅仅是境界的问题,爱他还需要勇气和魄力。你看天山是多么厚重,就像一位饱经沧桑、沉默寡言的父亲,对待父亲,谁还能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对他的爱是与生俱来的,用不着刻意去唤醒;对他的爱不是暂短的冲动,而是绵长而经久的,要用一生为代价去完成。
爱天山,就像爱自己一样,无需理由,也无法选择,更是无时无刻。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走近天山的。背上简单的行囊,沿着他的皱褶一步一步走进去,在寂静的深处,你可以听到勃勃的心跳声,它深沉有力,不疾不徐,平缓而有节奏,就像河水搬动河底的石块,或者就像沉雷在云层滚动,那是饱尝了苦难,经受了风雨,才特有的心律,显然不是我的,因为它没有一点浮躁,更没有一点虚妄。
只有在寂静的深处,只有把寂静当成了风景,你才能真真切切听到天山的心律。他的脉动和我是如此不同,把我的心跳与他比照,显而易见就发现了我的缺失,拥有一个有力庄严、健康崇高的心跳是多么令人神往。
现在,我正一步一步贴近他,靠近他父亲般温暖而宽阔的胸膛,我何时能够真正听懂他的心音?我时常有种冲动,想把太多的诉求告诉他,可我不知道我杂乱的心音是否侵扰了他的判断?我的无休无止地叩问,是否紊乱了他的视听?现在,我必须静下来,就像雪杉的一枚针叶,或者像冰川的一滴水,以最原初的姿式,最简单的心态,聆听来自天山的心音。
这世上不因为外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东西愈来愈少。我不知道天山是否也在改变?冰川在萎缩,河流在变浅,绿草日渐稀少,牛羊逐渐壮大,人的家园无处不在,而天山依然保持着静默,庞大的山体绵延成屏障,阻隔着一切来自世俗的纷扰,天山的存在就是对所有浮华的否定。
那是多么伟岸的身躯,面孔刀砍斧凿般地硬朗有力,托木尔峰和博格达峰仿佛是肩头隆起的肱二头肌,而雪杉和塔松就是他根根直立的胡茬,这样一个汉子,能会为什么而轻易改变吗?
他昂首伫立在那里,千百年了,就这样静默地伫立,一任风来云去,日月更替,他的额发飞白,肩头落满秋黄,金雕在他的腰际盘桓不去。这是让我们绝对仰止的姿态,这是让我们无法模仿的静默。
面对这样不会轻易改变的姿态,这样沉静的背影,每个人都会非常踏实。
有人说天山是一道书脊,南疆和北疆就是它打开的书页,一半金黄,一半苍翠,金黄的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苍翠的是北疆无垠的草原,谁把握了天山,谁就把握了新疆,谁捧起了天山,谁就拥有了新疆。
而我觉得天山更像是一条脊梁,一条坚实粗粝充满了张力的脊梁,他不仅是新疆的脊梁,也整个是亚洲的脊梁。我完全有理由自豪,抬起头,挺起胸,因为谁也不会像我一样,依傍着天山宽厚的肩背,体味着他不可撼动的沉稳,感受着与时间同在的尊严,不自觉间,我的脊梁也拉直了,人似乎长高了许多。
天山是踞上云端、直抵天庭的山,还是从天而降、沟通天地的山?
天山的美不是单一的,惟其丰富才难以割舍,惟其多侧面才难以描摹,惟其宏大才难以概括,惟其细微才难以一言以蔽之。
有人喜欢它荡漾的草原,更难忘它浪花四溅的野花;有人陶醉于它雨后的七彩丽虹,更钟情于烈日下的爽冽。
冰雪是天山的艺术收藏,那些水晶的山峰,剔透的沟壑,玲珑的邱谷,无一不是闪烁着艺术灵光的杰作,随便一处风景都会让艺术家自叹弗如,冰雪的神韵在于晶莹的外表下内蕴的光的力量,而那也是最难把握的,谁能让光听命于自己,谁就是神,因为神性的光芒向来都是来自内心,而不是靠谁的照射,或者反射了谁的光芒。
天山之阴生长着丰富的牧草,还有这个世界最了不起的树木——雪岭云杉。这些云杉是最有纪律的部队,挺拔苍翠,排列整齐,就像刚刚接受了新兵训练的士兵,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每每看见他们,都忍不住要举起右手,向他们行一个标准的军礼。
而我似乎更喜欢天山之阳,那些寸草不生的山崖,毕露着山的筋骨,嶙峋而峥嵘,坚硬而真实,天山的风骨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出,山的形状只有在裸露之中方能趋于完美,任何覆盖都会破坏他的造型,大自然的神工鬼斧难道还需要我们去修正吗?
登山家给自己登山找的理由是:因为山在那里。
我给自己画天山也找了个理由:因为山不在那里。
天山是被色彩浸泡的山,每一条山谷的颜色都不尽相同,只要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各自的特点,而大面积的绿色,似乎奠定了他以冷色为基调,一切的斑斓都是碧黛之上的绽放,带着忧郁的调子,一直绿到灵魂的尽头,一直阴凉到骨头的深处。新疆之所以有大片大片的苍黄,我怀疑是因为绿色都集中到了天山,上苍给大地分配的绿色原本应该是均衡的,有的地方用得太多了,有些地方就必然会捉襟见肘。
而我每一次都会被天山的红色震撼。天山的红是独一无二的,那是挣脱了绿色的一厘血性,那是极暖的色调对极冷色调的一次回应,那是绿色重压之下的必然反叛,还有什么比红色更能代表激情与宣泄?
在新疆,我曾有无数次这样的经历,如果是一个黄昏,夕阳就像一个精力过剩的莽汉,燃起冲天的大火把一天的云霞直烧得毕剥作响,而天山也即刻被点燃了,在这样的熊熊火光中,整个天山就像是被刚刚倾倒出冶炼炉的重金属液体,蒸腾着热力,挥洒着激情,那随意凸起的地方,是辉煌的喷薄,那必然的下陷,是灿烂的淤积。在那一刻,我也被点燃了,周身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灼痛,血液在嘶嘶鸣响,耳鼓在轰轰擂响。
其实,天山用不着点燃,它自己就不断燃烧着,火的形骸,风的神韵,被山的节律记录着,大块大块的赭红色,随着天光的改变成为褐、白、黄、绿、青、灰不断交替变幻的地质奇观。而在我看来,那些红色的铺陈和堆积,更像是一位被灵感与激情击中的画家,他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颜料统统挤在调色板上,就在他的疯狂和才华得以尽情施展的时候,却突然找不到画笔了,奇思妙想也不知所踪……那些红色,永远新鲜艳丽的颜料,静静地,东一摊西一摊地堆积在那里,让每一个造访它的人,都有一种作画的强烈冲动。
而那些丰富的红色,谁能说它本身不是一幅无以伦比的画作?其实我明白,我的一生也在等待一位描绘者来完善,不仅只是勾勒轮廓,更需要细节的填充,但他是谁呢?也许只有我自己是最佳人选。
天山是属于我的。我在这样说的时候一点也不气虚,因为我属于天山,天山为什么就不能属于我?我知道所有人都会指责我,天山怎么会是一个人的?就如同太阳、月亮,非私人物品,它们属于任何人,而不能属于某一个人,但我固执地认为:天山就是属于我的。对一个由于太过热爱、近乎疯狂而产生的偏执,相信善良的人们是会原谅我的。
感谢天山。
感谢因为天山而不断有人走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