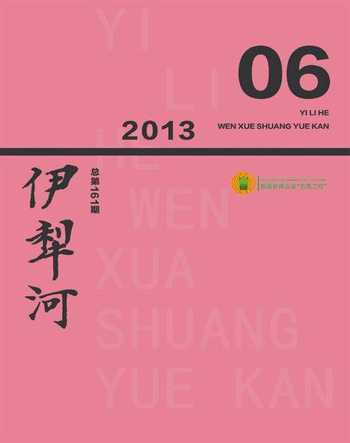最后的马兵
毕化文
在军分区,王老兵是出了名的说话冲,爱抬杠,认死理的家伙。不过没办法,王老兵资格太老了,连他当年带出来的兵都当了连长、营长了,屁股后头的兵呼呼啦啦一大群,连司令员见了他都称呼他“老王”。王老兵一听,不管戴没戴帽子,甚至连脚后跟儿都没有并到一块儿,都赶紧着举手敬礼。司令员见王老兵那个希拉样子,笑了,摆摆手拖着曲里拐弯的川音说,你龟儿子王老兵敬的礼,啷个受得起吆,实在不敢当,不敢当噻!王老兵就少有地面露腼腆,右手一捋毛乍乍的头顶,低下脑袋“嘿嘿”一笑,趁司令员不注意,“刺溜”一下,撂蹶子蹿了。
那一回,王老兵的凶悍我侥幸躲掉了,而是让接我后面一班哨的哨兵遇了个正着。事后我多次设想,如果那天遇上王老兵的是我,接下来的事情将要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确难以预料,只不过阴差阳错地让下一班哨兵赶上了。
接我哨的是我的同年兵,叫孟剑。孟剑上的是晚上的第二班哨,那会儿是整个城市最安静的时候,也是哨兵最容易打盹儿的时候。孟剑把装了子弹的弹夹卡在冲锋枪上,子弹没有推上膛,还关了保险。那会儿分区的大门还比较简陋,高大的“门”字型墙垛,顶端是水泥浇的顶,大门两端是狭窄的耳房,冬天上哨躲避寒冷的时候,穿件皮大衣,在里面转个身都非常困难。
夜色深深,马路两边的米黄色路灯寂寞地亮着,像蒙蒙的细雨,又像惨淡的夜雾。孟剑穿着大头鞋,手上戴着棉手套,将冲锋枪枪托朝上背在身上。忽然,在分区石头围墙的西北角儿,临近公路的林带里,影影绰绰拐过来一个人影,一晃一晃地出现在街道路灯下的地面上,一杵一杵地移动着,随之,似乎是被这长长的影子拽着似的,一个人也跟着出现了。孟剑一看那人走路踉踉跄跄,就知道是个醉汉,他小心而多余地看了看两扇早已关闭的,钢筋焊成的大门,抖了抖精神,将胸前的枪背带用右大拇指绷紧了些,专注地盯着那人一步步走近。
走近了才看清楚,这个人竟也是个当兵的。那会儿我们当兵满打满算才短短的两个月,从新兵连刚下到老连队,连连队里官兵的姓名才勉勉强强记得下一半儿,对于隶属后勤部门的王老兵的情况,自然一点都无从得知。孟剑一看这个兵,没戴帽子不说,还穿了身泥黄色的老式帆布军装,小翻领上的红领章都洗得泛了白,脚上是一双深腰的雨鞋,跟我们心目中的官兵的形象格格不入。离得远的时候还闻不到,等到近前了,一股刺鼻的马厩里的气味儿,让孟剑的鼻梁皱了皱。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些新兵从一入伍就学习条令,对军容风纪已深入骨髓,他一见王老兵那个熊样儿,就认定这不是个好兵,却不知道拿眼前这个希拉兵该怎么样处理,而且,眼前的这个胡子拉碴的兵浑身流露出一股蛮劲儿,足足高出他一头还要多。
孟剑正犹豫间,铁大门就被擂响了,“哐当,哐当”地在夜里传出很远,同时王老兵还怒狮般地狂吼:开门,我要回去!快开门,你个新兵蛋子!
王老兵毕竟熟悉情况,敲了几下大门后,忽然想起一旁的侧门是不关的,供往来大院的人出入,于是他气势汹汹地撞开侧门,逼近孟剑,伸手抓住孟剑的衣前襟,举着攥得紧紧的铁拳,在孟剑眼前晃来晃去,几次险些就要落在孟剑的身上,嘴里喷着浓烈的酒气,还一个劲儿地嚷嚷,说我要替你们连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新兵蛋子,要你学会如何尊重一个老同志!
孟剑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紧张地把枪端在了手中,枪口对着王老兵,黑暗中看不出他的哆嗦,只一句接一句地警告王老兵说:我可是在执勤,你再敢动哨兵,我可要开枪了!
开枪?王老兵说,你开一个给我看看,你个新兵蛋子,我能把你的屎捏出来信不信?还开枪,把你狗日的日能得不行了!
两人纠缠间,不知什么时候孟剑已经拉开了保险,子弹也推上了膛,结果,就在王老兵再次挥舞着拳头要揍孟剑的时候,“砰——”地一声,孟剑扣动了扳机。
子弹呼啸着飞上了天,枪声还在分区大门口的上空盘旋的时候,警备参谋就已经带着纠察乘着吉普扑了过来,他们一看是王老兵,只好哄骗着他上吉普车回去休息,王老兵死活不干,吵着嚷着要警卫连的查连长过来,狗日的不过来他就呆在这儿,哪儿也不去。查连长是王老兵带出来的,他要当面问问这个狗日的,他是怎样带兵的,自己以前是如何教他尊重老同志的。
不一会儿,查连长果然气喘吁吁地来了,他一边高声喝令要关孟剑的禁闭,一面陪着笑脸对王老兵说,老班长,您就别跟一个新兵蛋子一般见识了,都是我带兵无方,还声色俱厉地扭过头去喊:看我回去不好好收拾你!同时给一块儿来的孟剑的班长递眼色,要他赶快把孟剑弄回连队去。
回连队的路上,孟剑的班长说,你惹谁不行,偏偏惹他——也难怪他喝那么多的酒,他心情不好啊!
班长告诉孟剑,不久前,王老兵处了一个对象,是个寡妇,就在分区隔壁的学校里当老师,介绍人是副司令的老婆,在这个学校当校长。寡妇虽然离婚已经好多年了,仍然比王老兵小好几岁。副司令老婆在介绍王老兵的情况时,说王老兵就是因为太爱战马事业了,这才把婚姻大事耽搁下来,这么多年来军功章得了一大堆,可是,副司令的老婆双手一摊,要那么多的军功章有什么用啊,军功再多也替代不了老婆啊!那老师就同意,说先跟王老兵见一面再说。没想到王老兵在接到电话时,正给“赤兔”马清理发炎的左眼,来不及打扮,就一身马厩味儿地赶去赴约,那老师一见面,觉得王老兵太不尊重自己了,就捂着鼻子,连声“再见”都没说,连忙逃也似地跑了。王老兵觉得憋气,就近在一个小酒馆里把自己灌了个烂醉,在回来的时候又遇上一个不懂事儿的新兵,于是就发生了这场动静不小的纠纷。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我就到连部当了文书,这才注意到,王老兵一有空闲,就到连队来,人还没到连部,就一口一个“小查子(我们连长是满族,姓查),小查子”地咋呼开了。以连长为首的连队干部,闻声赶紧迎出营房门口,把王老兵毕恭毕敬地让到连部,王老兵呢,简直像到了自家的地盘一样放浪形骸。每回一到连部,王老兵就一屁股坐在查连长的办公桌上,将连长用铁皮弹盒做成的莫合烟盒往眼前一拉,一根接一根地卷着抽,边抽边跟连长指导员他们谝大拉子(扯闲话)。我忙前忙后地为大家服务,久而久之,就对王老兵的情况掌握了个八九不离十。
原来,王老兵的父亲是先前骑兵团的军医,上世纪五十年代随小分队到昆仑山下剿匪,不料在铁干里克一带,遭遇了土匪的伏击,带队的是骑兵团作战参谋张雷,他一看,小分队的几名同志和胯下战马大部分已经中弹牺牲,自己也负了重伤,只有王医生因为躲在一棵干枯的胡杨树后面,才躲过敌人的子弹。张参谋的坐骑叫“赤兔”,是小分队临行前团长亲自送给他的,是一匹毛色闪亮,体态修长高大,又十分敏捷的枣红色战马,此刻它竟腾挪跳跃地躲避着土匪的枪弹,一边还“咴儿咴儿”地昂首嘶鸣,意思是提醒小分队快撤,眼下情势凶险。张参谋命令王军医骑上“赤兔”,赶快回去通知增援部队。在骑着“赤兔”突围的过程中,一颗流弹飞来,从“赤兔”的左眼穿过,当时王军医根本不知道“赤兔”已经受伤,只是一个劲儿地快马加鞭,催促“赤兔”赶快跑回去搬兵。等到了剿匪部队设立的联络点时,“赤兔”再也坚持不住,终于“噗通”一声,卧爬在尘埃中,左眼的血迹已经结成了雪痂。王军医一看,大放悲声,发誓一定要救回“赤兔”的生命。在剿匪部队和王军医的精心医治和照料下,“赤兔”虽然一只眼睛瞎了,却终于活了下来。
剿匪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撤编,为了让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战马能够善终,军分区在离城市十多公里的草原上建了一个军马场,设立专门的军马饲养员,归分区作训科和后勤部同时管理(不久后又直接隶属后勤部了)。为了工作上的连续性,这位饲养员必须是职业兵,也就是后来的志愿兵。王老兵的父亲在骑兵团撤编后,转业回到甘肃老家,在县医院当了一名医生,但他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在骑兵团的战斗生涯,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以及无言的战友——军马,尤其最思念那匹救了自己性命的“赤兔”。“赤兔”常常在夜里出现在他的梦中,发出“咴儿咴儿”的嘶鸣,似乎对他发出召唤一样。王老兵那会儿虽然才十四、五岁,但个头长得出奇得快,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大小伙子。由于受父亲战斗故事的熏陶,他很小的时候就向往军营生活,一天到晚吵闹着要当兵,于是,在王老兵十六岁那年,思念老部队心切的王军医,带上已经跟成人差不多的王老兵,重返军分区。此刻分区的司令员正是那会儿的骑兵团团长,王军医话一出口,王老兵就留下来当兵了。
当初分区的意思是让王老兵“子承父业”,先送军区医护学校学习,再回到分区卫生科当军医。王军医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非要儿子到军马场当一名牧马兵,尤其是当他听说“赤兔”仍然好好地活着的时候,专门带着儿子来到军马场,将当年的故事完整地给儿子讲了一遍。一边讲一边搂着“赤兔”的脖子哗哗地流泪。在离开分区返回老家前,他一再嘱咐儿子,一定要善待这里的每一匹军马,要像善待自己的父辈一样,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否则就不是他的儿子,王老兵一一应承了下来。为把王老兵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分区先把王老兵送进教导队,跟当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参加训练。王老兵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当兵的料,他不仅处处做到严格要求自己,还在新兵连的训练中,多次拿到训练考核的第一名。
虽然离战火纷飞的年代越去越远,军分区对这些走过烽火硝烟的军马依然是高度重视。除了送王老兵到专业的兽医学校学习专业知识,还为他选配了一个战士作帮手。这样一来,王老兵就可以抽出时间参加分区的新兵训练,连续多次担任新兵班班长。在教导队,王老兵以新兵训练严格而著称。他训练的时候喜欢夹带小动作,急的时候话带脏字。为此教导队多次对他提出批评,但他带出来的兵个个素质过硬,动作规范标准。况且,他的小动作始终拿捏得恰到好处,从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还赢得每一个新兵的尊重。每次训练一结束,他都要立刻回到军马场安心当自己的牧马兵。分区多次给军区打报告,要求给军马场一名干部的编制,这样也好给王老兵一个妥善的安排,却每次都被军区以军马已经不适应于现代战争的需要,要逐步淘汰,因而不适于再编制干部为由拒绝了。分区也曾想过,将王老兵借调到某个机关单位,先解决干部指标再说,也被王老兵以军马场离不开自己而拒绝了。
分区有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科长,老科长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儿。她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就多次组织同学们到军马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她因此被“赤兔”马的事迹深深震撼。同时也被王老兵多次拒绝组织的照顾,立志要当一名合格的牧马兵所感动,从内心喜欢上了王老兵。高中毕业后,科长的这个女儿在某个政府机关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王老兵进教导队当新兵班长的时候,她多次一个人跑到新兵班,趁着王老兵短暂的清闲,打开王老兵的床头柜,取出王老兵抄写的流行歌曲,纠缠着要王老兵教她唱歌。其实,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的嗓子比天上的百灵鸟儿还动听,她还曾经在全市青少年歌咏比赛中获头等奖,哪里需要王老兵粗声破嗓地点拨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了。
可是,条令不允许战士在驻地谈恋爱,王老兵又不是军官,只好将满腔的心事儿压在心底。不久后的一天,科长的女儿在下班回分区大院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迎面撞飞,不治而亡。王老兵极度消沉过一段时间后,再也不提个人问题这档子事儿了。
眼看年龄和军龄都到了极限,提干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分区只好将王老兵转成了志愿兵。
在我当文书这段时间里,渐渐跟王老兵混熟了,也敢在他面前稍稍放肆一点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那回他和那位老师见面,是不是故意穿一身马厩味的工作服跟人家见面的。同时我还提到那位多年前因车祸不幸去世的女子的名字,问他是不是心里仍然放不下这个初恋情人。想不到王老兵竟勃然大怒,骂道:你个没大没小的牛犊子,再敢在老子面前提一次这个名字,小心我把你的屎给捏出来!我吓得一吐舌头,赶忙从他眼前消失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查连长跟他的几个同年兵在背地里说,每年的清明节,王老兵都悄悄地来到东山,到埋着那位夭折女子的山坡上,给早逝的心上人祭祀。因为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确立,王老兵只能背着大家去给她烧纸,默哀,说说心底的话。时间久了,哪能会不被人发现呢,只是大家即使看见了,也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毕竟,这是一段多么令人伤感唏嘘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
分区在驻地有两个农场,一个在北斗星乡,是我们连队的,距离分区有几十公里远。我当班长的时候,曾经几次带领全班弟兄到农场劳动,有时候是跟在大型收割机后边,收割那些因为低矮被收割机遗漏的麦子,或一些死角里收割机无法收割到的麦子,有时候是给几十亩地的油葵间苗,还有一次是给农田打埂子,累得大家东倒西歪的。另一个农场是机关的,其实也就是王老兵所在的军马场,因为跟我们连队联系不多,我从来没有去过,直到当兵的第三个年头,才第一次来到这个只闻其名不见其景的地方。
随着岁月的流逝,骑兵团留下的军马也在逐年减少。到了我们入伍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几匹了。偌大的军马场变成了军分区的饲养场,里面有成群的羊,鸡、鸭、牛和猪,方圆十几公里的练马场,也早就不再有战马驰骋的身影,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荒野草滩。军马场附近有一个乡政府,乡里在军马场附近建有一家相当规模的奶牛场,因陡然间引进了太多的奶牛,以致缺乏当年越冬的草料。该乡和分区是多年的军民共建单位,他们发现练马场荒草满坡,就向分区领导提出,要收割军马场里的荒草做奶牛越冬的草料,分区不仅答应了,还主动提出,由分区官兵收割后,将干草送到奶牛场去。
那天的风很大,因为入秋已久,天气开始变得有些寒冷,风吹到人的脸上,感觉就变得麻木和僵硬。分区组织机关和我们连队一百多官兵,分乘几辆卡车,风驰电掣般驶往军马场。此刻的野草因为时候已到秋末,已经变黄变老,作为奶牛饲料刚刚好,但收割起来却非常费劲儿,我们手中那长长的弯月镰刀,被粗壮结实的野草秸秆别出一个个大口子。那天带队去的是一位副司令员,他要求我们每人收割的草分量不得少于三百公斤,并且由王老兵现场过磅,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所以,大家一直干到太阳偏西,还在草地里挥汗不已。
终于到开饭时间了,后勤为机关官兵送的是抓饭,我们连队送的则是蒸面,蒸面里的菜用的是四季豆和羊肉,虽然我对羊肉很喜欢,可是同年兵中有几位就是受不了羊肉味,说膻得慌,不好吃。其中有一位姓郑的同年兵,端着一碗蒸面,来到我吃饭的一棵沙枣树下,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将一块块羊肉挑出来撂到地上,还不停地发牢骚。王老兵恰好从别处走到他和我的后面,他愣是没有发现,还弄不懂我的眼神儿,说炊事班这帮货物蛋子,知道老家伙不喜欢这膻东西,偏偏往锅里做,真不知道他们一天到晚在干什么。仅仅说这些还没什么,他竟连那匹战功卓著的“赤兔”也没有放过,说什么屁军马场,几匹东倒西歪的瘦破马,连个灰头土脸的驴子都不如,还牛X吹到天上去,说什么是立过赫赫战功的“赤兔”战马,人家三国里吕布胯下的那才叫“赤兔”呢,咱们这个“宝贝儿”算得上什么东西,一匹老得连路都走不成的瞎马。一听他说起那匹老军马,我赶紧摆手制止他,但已经晚了,王老兵早已一个箭步蹿到那同年兵的面前,吼道:你刚才说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给老子说一遍!说时迟那时快,王老兵的话音未落,我同年兵的脸上已经“啪”地一声脆响,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在同年兵愣怔的时候,王老兵接着骂道,在这个世界上,你骂哪个都可以,唯独不能辱骂我的“赤兔”马,它是你能骂的吗?它是顶天立地的功臣,你是什么东西?一个球毛都没有扎全的新兵蛋子!
骂完,王老兵才悻悻地到别处查看草场收割的情况去了。
很快,同年兵回过神来,哭着告到副司令那里,结果,王老兵受到入伍多年来的第一个处分!
一年后,军队进行大规模地精简整编,分区警卫连变成了警卫排,我成了首任警卫排排长。早已名不副实的分区军马场,自然而然地要顺应历史潮流,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历史,退出军队序列,移交到地方政府部门,王老兵呢,也即将随之就地转业,成为一名地方上的职工。
军马场移交前的一个礼拜,上级交给我们警卫排一项公差勤务,乘车随有关部门到军马场清点军产,将那些军队财产,诸如锅炉呀,钢管呀,钢轨呀什么的,装上卡车,拉运回分区大院里来。
临登车之前,已经任教导队队长的查连长专门到警卫排,递给我两条红雪莲烟,他虽然一句话没说,我也知道这烟是带给王老兵的。到军马场后,我根据此次来军马场的意图,将工作给各班布置停当,就胳膊弯儿里夹着两条红雪莲,往王老兵的办公室走去,想最后一次安慰安慰他,因为全分区里谁都知道,王老兵实在不愿离开部队,不愿离开他的军马场。可是,军令如山倒,军马场不在了,他这个兵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这个道理王老兵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是他对军马场倾注的感情太多了,可以说是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甚至透支了他的未来。真的到了割舍的时候,谁都难以做到四两拨千斤,更何况是王老兵。我故作轻松地边走边喊着“老同志”,说这一下老同志变成了水,我们成了鱼儿,今后我们的关系成了鱼水关系,还望水儿不要亏待了我们这些鱼儿呀,说着还哼唱起那支“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的老歌儿来。
我只顾着贫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闯进了王老兵的办公室,却没有适应室内的黑暗,更不可能看清楚,在我唐突地进来之前,王老兵独自一人,对着窗户,在房间里无声地哭泣。等我把两条红雪莲撂到他显得有点凌乱的床铺上时,他才站起身,腾腾腾几步跨出了办公室。我有点惊愕,呆呆地坐在王老兵刚才坐过的床铺沿上,怔怔地朝着窗外看着。就在这时,我再次看见王老兵,只见他牵着那匹瘦得几乎四条腿打架的“赤兔”马,摇摇晃晃地走出院子大门,朝着去年我们收割秋草的草滩上走去,看着骨瘦如柴后背已经微微弯曲的王老兵,一时间,我百感交集,难以控制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低头抹泪之际,发现王老兵放在桌面上的笔记本,显然,他刚才一定还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是我的到来,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钢笔。我打开笔记本的硬皮儿,在本子的首页,发现有一帧精美的骏马图像,乍一看,跟军马场的这匹“赤兔”马一模一样,只是图画上这匹马的双眼是有神的、明亮的、清澈的,而军马场的这匹“赤兔”马,已垂垂老矣,几乎可以说是秋风落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帧图画的旁边,只见王老兵用自己那不太周正的字体写道:
“赤兔”,汗血马,又称“天马”,产于我国新疆伊犁的昭苏等地,一九四九年入伍,多次参加剿匪战斗,立下大功四次……不知为什么,王老兵写到这里却没有再写下去,后面却是一长串的破折号,显得那么意味深长,又是那么无可奈何!
等我再次朝那一人一马的方向看去时,王老兵和“赤兔”几乎快要模糊在时空的深处了。
啊,王老兵,我又敬又畏的王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