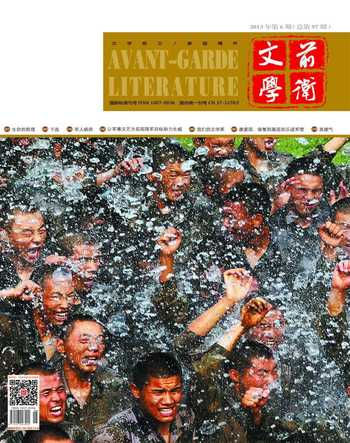朴拙大气展精神
高毅清
当年的学员各有千秋
图为1979年文化部部长王鲁珍等领导接见第四期全区文学创作学习班部分学员合影,当时赵骜因病没有参加。具体说明:前排右起第二人为王海鸰、第四人为严玉树、第六人为王鲁珍、第七人为李虹宇、第八人是本文作者,第九人为李英捷;中排右起第二人为黄国荣、第五人为李荃、第九人为孙晓;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刘灿校、第五人为王义俊。
赵骜将军多彩一生,当过作家,做过领导,担任过科长、处长、局长等许多职务,赢得了很多赞誉。最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位置上定格,我感觉是一个回归。教学育人,他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做了。他的学生、弟子遍布全军,名满天下。
2013年5月26日,是我到北京与赵骜将军作别的日子。意料之中见到了许多久违的同学同事同仁。仪式结束后,崇高研究院院长贺茂之将军——也是赵骜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热情邀请大家到他院里,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思会。追思会上,出于对赵骜将军的感恩戴德,大家决计编纂出版一本怀念他的文集。分题作文,茂之希望我能写一写赵骜在济南军区举办前几期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情况。他说虽然大家师出同门,但相比之下,还是我在济南军区的时间长一些,对那一段历史,了解的自然也多一些。时隔40多年,往事并非如烟。无论我们共同的恩师,还是那一段共同的经历,都需要被纪念。
济南军区的军事文学创作,曾经辉煌一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巅峰,出现了《闪闪的红星》《高山下的花环》《在这片国土上》《最后一个军礼》《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汉家女》等一大批蜚声文坛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李心田、李存葆、李延国、苗长水、周大新等部队本土作家为代表的“前卫作家群”。我说,这与赵骜将军当年在济南军区举办的那几期创作学习班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70年代,赵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文化科副科长,宣文分开后又任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在此期间,他先后领导举办过4期创作学习班。有人称之为“骜头儿的学习班”、有人叫“骜头儿的黄埔四期”。这些称谓,有“赵骜领头儿”的意思,也有“独占鳌头”的褒奖。而更多的学习班学员,特别是那些怀揣大学梦而无缘大学的年轻士兵们,则称之为“我们的文学系”,这就带了大学的意味儿。
“我们的文学系”密集举办于上世纪70年代赵骜在济南任职的七八年间,几乎每年一期。每期都好几个月。第一期是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 1971年9月举办,地址在济南东郊的军区招待二所,那一期规模最大。学员由各单位自行选送,足有100多人。第二期也是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举办于1972年秋天,人员由军区根据各大单位上报作品的作者选定。门槛高了一点,规模自然小了许多,只有30多人。地点在军区展览馆。第三期是文艺创作学习班,时间在1973夏天,约有十几名部队业余演出队的创作人员参加,主要是创作加工文艺演唱作品。地点在军区展览馆和济空小纬九路招待所。第四期还是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时间在1979年秋天,地点在长清高炮部队招待所,有20多人参加。这4期创作学习班,当时看成绩斐然,现在看意义深远。是赵骜将军留在济南军区的一串足迹,也是他给济南军区留下的一笔遗产。
“我们的文学系”集中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编辑了4本短篇小说集:《雨涤松青》《沂蒙山高》《山外青山》《心的音响》和一本文艺演唱作品集《多余的弹孔》。这些作品全部出自部队业余作者之手,具有浓郁的部队生活气息。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打磨,特别是经过赵骜科长字斟句酌,每篇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些作品,先后由人民文学以及山东、上海等地的出版社出版,成为那个时期,除了八个样板戏、《鲁迅全集》和《艳阳天》之外,唯一在全国出版发行的文学书籍,遍布全国各地书店,影响很大。至今,这些书籍作为“文革”时期的出版物已堪称文物,在“淘宝网”还有销售。有些文集中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决心书》(作者何先润),《最后一个军礼》(作者方南江、李荃),《雨涤松青》(作者李德昌),独幕话剧剧本《水桶问题》(作者贺茂之),快板书《三件大衣》(作者李德昌)等,都曾被军内外报刊选发或转载。短篇小说《扬帆千里》(作者陶泰忠)、《红溪松青》(作者刘灿校)还被复刊不久的《中国文艺》(英文版)选入,发往国外。短篇小说《决心书》当年还入选了北大文学系的教材,《最后一个军礼》后来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们的文学系”相继培养了一群优秀的部队作家和文化干部。当初进入学习班的学员,大都是20出头的小战士。如贺茂之、李平分、陶泰忠、黄国荣、王海鸰、苗长水、李荃、刘灿校、桂恒彬、王尚贤、李英捷等等,都是在那4届学习班的培养、教育、熏陶和创作实习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他们后来有的被调入军委总部、军区、军、师、团各级文化部门,成为部队文化工作干部骨干;有的成为声名显赫的诗人、剧作家;有的被调入解放军文艺社、新华社、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院、军区文工团、军区创作室等专业文化部门,成为专业作家。
“我们的文学系”尤其体现了部队特色的文学“生成”方式。中国文学史观念更新换代以来,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提出了军事文学类型是否存在的问题?军事文学的“生成”方式问题日益受到学者关注。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陆文虎组织领导的《解放军艺术史》课题组以“生成主义”的视角,提出新的见解,即不认为“军事文学”的定义是必然的、本质的和客观的,而把它看作是在各种特殊历史情境中,在各种美学传统、审美成规、心理机制等多向度的文学资源中不断“生成”的。简单说,就是军事文学“类型”的存在和地位,在脱离了“题材”至上的“一体化”文学时代之后,正是靠其继承下来的专业作家和机构以及背后的体制和组织生产方式一步步“经营”出来的。由此可见,“军事文学”不应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文学分类,更是一种文学组织和生产方式。这种题材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军队特殊的文学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产物。
“我们的文学系”有力地支持了上述学术观点。首先,它是在部队文化部门职能驱使下举办的。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的文化部门也一度受到冲击,但和地方文化机构不同,体制职能依然存在和发挥作用。赵骜作为新任领导,又是作家,策划这项工作自然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尽职尽责,所以能在全国全军占得先机,赢得“鳌头”称誉。第二,它是为满足部队官兵文化需求定制的。“文革”时期,全国作家都被打倒,作品被封禁。部队广大官兵的阅读需求无法满足。这是当年赵骜举办学习班的一个政治理由。学习班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每期必学。要求创作牢牢把握为部队服务的政治方向。要求作品一定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强调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绝不允许没有主题的无的放矢和脱离生活的瞎编乱造。第二期学习班在创作《沂蒙山高》这部专辑的过程中,为了弥补一些年轻作者对战争年代生活的不足,赵骜还专门安排学员到沂蒙山老区体验生活。1979年南疆战事打响以后,赵骜更是亲自带队到前线采访。第三,不为名,不为利,以军人的情怀书写。“我们的文学系”,时值“文革”,不像后期和现在学习班和笔会,没有著名的专家教授可请,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教材可用。只能“土法上马”,干中学、学中干,“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赵骜以自己和众多部队作家自学成才的成长道路勉励大家,对文学既要有敬畏之心,也不要有迷信思想。他把自己珍藏的文学理论书籍和世界文学名著,拿出来让大家阅读。当时这些书都属于“禁书”,所以立刻成为学员们排着队竞相传阅的读物。那些书不分昼夜地在大家手中流转,最后回到赵骜手中时已面目全非。他多少有些心疼,苦笑着指责:你们这是看书吗?分明在啃书嘛!赵骜除了亲自授课,还邀请了军区文工团的一些专业创作员作辅导。如李心田、李存葆、李允文、李荣德、李延国、张红曙、王颖等,都曾做过我们的辅导员。他们的辅导是面对面、点对点、一对一的,根据每个学员的创作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根据修改意见阐述相应的文学理论。这样的辅导教学生动具体,为每个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学员们之间也相互传看作品,分组进行讨论,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执笔修改,最后还要听取应邀前来审稿选稿的刊物主编和出版社编审们的意见和建议。如此,几乎每一件作品都在学习班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赵骜对所有学员的作品都有修改,有些改动大的作品无异于重写。原作者提出一定要为赵骜署名。赵骜推辞不脱,便起了个“梁念”的笔名。意为“良好的愿望”,希望学员们早日成才。第三期学习班有一个曲艺作品,原作者是26军的徐聿生和李乃高,赵骜让我和空军的刘田增分别改过两遍。出版时署名为“袁叙礼”、“侯德增”。标志原作者是徐聿生和李乃高,后来修改者是李德昌和刘田增。那时的大家没有版权意识,也没有名利思想。我想,如果后人以文本研究“我们的文学系”,肯定会遇到许多不解之谜。 “我们的文学系”是一个军人团体。也是一个战斗集体。赵骜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4期学习班,他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讨论、同写作。在远离机关的招待所是这样,在离家近在咫尺的军区展览馆也是这样。1973年的第二期学习班,他住在展览馆那间背阴的小库房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天。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展览馆没有暖气。他夜以继日地在冷藏室似的屋子里看稿子,改稿子,和每一个学员谈意见。眼睛熬得通红,嘴里冒着白气。说得口干舌燥,端起水杯,才发现保温杯的水已经冻成了冰。1973年盛夏。济南气温达到40℃,我们住在小纬九路的空军招待所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大家光着膀子,头顶湿毛巾,两脚泡在冷水盆里伏案写作。但是我们眼中的赵骜,军装依然穿得齐齐整整。他仿佛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怕冷,也不怕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的言谈举止对学员们产生的影响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学习班的集体性格。
这便是我们的文学系。它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当然也带有赵骜的印记。无论从业绩上讲,还是从品格上看,如此厚德载物的大好事,为什么会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我翻阅济南军区的大事记,没有关于它的记载;查看赵骜自己撰写的个人业绩资料,也没有关于这节往事的片言只字。在赵骜将军悼词提及此事的唯一几行字,还是贺茂之在审看时最后加进去的。我不解,到底是赵骜本人太低调?还是历史太高超?抑或是天地太浩渺?现在,赵骜将军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否还能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2004年军事文学的处境已很窘困。我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短期培训,集体讨论办班方式时我曾经介绍过济南军区办班的经验。很多人不以为意,认为赵骜的学习班实际上是不可复制的,包括他自己。即使成为军艺的训练部长、副院长(当时已离休),也不可能再办当年济南军区式的学习班了。我想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旧事难追。办那样的学习班,毕竟需要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以及那样的人。往事不再,祝君一路走好!
标题手书 虞晓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