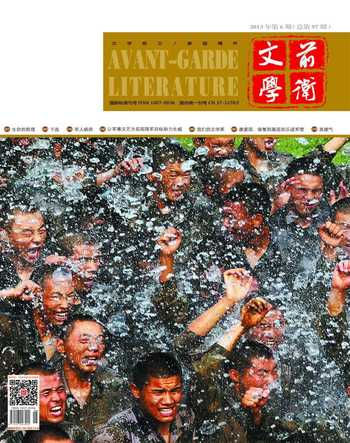说书人
刘树波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位说大鼓书的盲人,是从异乡来的,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管他叫老侯,说书人老侯。
老侯并不老,光光的头,30来岁,五大三粗,长得十分魁梧;老侯嗓门宏亮,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很有诱惑力。老侯往台上一坐,腰杆挺得绷直,稳如泰山,没等开口,就有了一番英雄气概,让我们打心眼儿里敬畏。
老侯每年都来我们村两三次,每一次到来,对我们那个僻静的小村来讲,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老侯说书的场面是很红火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的秋后。秋忙完了,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用木头扎起了一个高高的小戏台,戏台上一桌一椅一老侯。戏台两头挂着两盏马蹄灯。台下,夜幕下黑压压的人群。老侯一开口,台下吵嚷的人群顿时静下来,大眼小眼都聚焦到老侯身上。老侯边说边唱边动作,声情并茂,非常投入。他的头晃过来摆过去,仿佛能看到台下被他引入另一个世界的人们。
他最得意的是这几部书:《岳家军》《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呼延庆上坟》《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等。老侯在讲说的过程中,每当正义一方抬头得势,他就离开桌椅扬眉吐气手舞足蹈,时而鼓声急骤如雨,时而铜板铿锵作响,台下男女老少群情激昂叫好声不绝!遇有阴险坏人作恶,好人遭到挫折陷害时,他便声音低沉,悲壮激愤,如泣如诉,眼里仿佛要掉下泪来,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
台下,特别是我们少年人便等得不耐烦,“坏人怎么还没有被斧砍死,被枪挑死?”我们望星、望月,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互相吵闹着到庄稼地里大小便。
我的家乡在黄河入海口。那时,村落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赶年集又不爱看那些唱来唱去就那老腔调熟套子没味道的大戏,唯一像盼过年一样企盼的,就是盼老侯到来,听他说书。老侯家住在哪里,我们一直不知道。关于他的眼睛,大人们说老些年闹鬼子时叫日本鬼子伤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老侯分外喜欢我们这些野孩子,在一块儿混得不错,听声音他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他不仅为我们说书,而且还帮我们放猪、割草、拾柴火,还和我们一块摸鱼。他摸鱼很拿手,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岸上的“小不点儿”都拾不过来。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小伙伴让水里的一条蛇咬了一口,吓得“哇哇”大哭,老侯抓到了那条蛇,一口就咬断了,我吓得不行。那是我唯一对老侯不满的地方,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我们常常争着叫老侯到家里吃饭,老侯能到谁家谁家就感到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打酒,做好吃的,分外开心。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长大后,我到外面求学,很少再得到老侯的消息。
前年我回家过年,大年初二的时候,老侯又顶着风雪来了,住到了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里。很少再有人请他吃饭了,连同昔时我那些已长大的伙伴,也没有人再听他说书,家家户户有录音机,也有电视机,谁还会稀罕他的书啊!父亲对我说:“去叫你侯伯来家吃顿饭吧!大过年的,一个盲人不容易。”我点点头,我去叫老侯的时候,他一个人沉默地坐在椅子上。十几年不见了,他还是光光的头,只不过清瘦了,衰老了,行动缓慢了,手里一根拐杖,脸上还戴了墨镜。
一番交谈,他记起我来了,谈到陈年旧事,我的心里又欢喜又悲伤!我叫他去我家吃饭,他说什么也不肯,只说了一句:“你们都长大了。”一句话,叫我差点掉了泪。
老侯第二天就走了。老侯走的时候,我约几个儿时玩伴去送他。天下了大雪,一片白茫茫的,我一直望到老侯黑色的背影在雪地上消失。说走就走了,老侯走到哪儿了?还会回来吗?
儿时的伙伴一一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雪地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沉思默想……
当今,说书的人,大都走到电视上去了,黄金时间来上一段儿。一杯冒着热气的茶,一把潇洒飘逸的扇子。
每每看到,我的心就起一阵波澜,心慌得不行。我忘不了儿时说书的老侯,英武善良,慷慨激昂;忘不了他风雪凄迷中踽踽独行的黑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