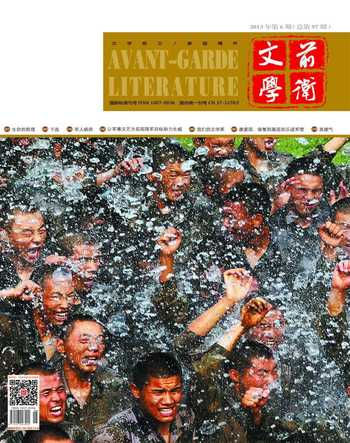蒙山娘和她的八路儿子(短篇小说)
作者名片:
有令峻,1951年3月生于济南,祖籍青州;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原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当代都市三部曲《夜风》《夜雨》《夜雾》,长篇纪实文学《状元卷失窃案大追捕》、纪实文学集《神圣使命》,散文集《雪天夜行》《寻找故园》《感受寂寞》《心诚则灵》等专著25部,计700万字;获奖80多次,《夜风》获山东省第七届(2002—2003年度)精品工程奖、《夜雨》获山东省第八届(2004—2006年度)精品工程奖、2008年被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评为“阅读中国——建国以来长篇小说500部”,《夜雾》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2007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少儿纯美长篇小说“东湾村系列”《田野上的风》《东湾村的小伙伴们》《初一四班那些事》2013年4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出版。
在山东的南部,有一片红色的土地,叫沂蒙山区。沂蒙山在中国地图上没有这个名字,但沂水和蒙山可以找到。沂蒙山区也由此得名。
以沂蒙山区的革命斗争故事创作的文艺作品有京剧《红嫂》、《红云岗》、舞剧《沂蒙颂》、长篇小说和电影《红日》,还有电影《沂蒙六姐妹》等。歌曲则是《沂蒙山小调》。还有一支《谁不说俺家乡好》,是电影《红日》的插曲。
在雄奇巍峨的蒙山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蒙山娘和她的八路儿子。
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6月。那是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村东头两间低矮的石头屋子里,住了一位孤苦伶仃的大娘。5年前,大娘的丈夫被汉奸队抓了壮丁,逃跑的时候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17岁的儿子半夜里抓起斧子前去报仇,也让鬼子兵用刺刀捅死了。
一天午后,村外的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枪声不是太密,但却接连不断,还有男人叽哩哇啦地喊叫。大娘一听那叫声,就不是中国人的声儿。大娘趴在石墙上往响枪的地方看去,只见几个穿黄皮的军人,刺刀上挑着一面药膏旗子,从村东边的山路上跑过去了。枪声也渐渐地停止了。
大娘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一些感觉。鬼子在追谁呢?一定是在追八路军或者抗日的民兵或村干部。想到这里,老人用手拢了拢灰白的头发,定了定神儿,拄了根推磨的枣木棍子,出了自家的小院。
大娘在山路上一边走一边东看西看,走出去了一里多路,也没发现一个人。大娘双手扶着棍子,往四周又看了看,太阳已经快落下西山了,天空一片彤红彤红的火烧云。大娘叹了口气,转身往回走。
来到村头上的那棵大核桃树下,只见从村里跑出来3个穿便衣拿着长短枪的人。大娘认得他们,是汉奸特务队的二鬼子。一个二鬼子头儿走上来,问:“老太婆,看没看见一个小伙子跑过去了?”大娘斜了他们一眼,说:“没看见!”二鬼子们就朝东边跑去了。
连着两天,特务队来村里和山头上找人。估计就是搜那个八路军或民兵。
大娘连着两天,挎了个篮子,装作挖野菜、抓蚂蚱、抓蝎子,也在山坡上转。她也在找人。
第二天傍晚,当大娘来到一道高高的石堰下边时,看到了一簇茂密的荆棵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斜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大娘不觉吃了一惊。小伙子见了大娘,本能地抓起了身边的一块石头,警惕地望着老人。
小伙子的脸又黑又黄,两只黑黑的眼睛陷在深深的眼窝里,张大了嘴,费力地喘着气。看得出极度地疲惫。
大娘毕竟是经历过几十年风雨的人了。她定睛看了看小伙子,穿一身农家的旧衣裳,个子不高,瘦瘦的,留着短短的头发。从脸面上看,也就十五六岁。小伙子的一只手,把一个长方形的布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大娘走近他,弯下腰,低声问:“孩子,鬼子和汉奸找的是你?”
小伙子看了看大娘,点点头。
大娘又问:“你是个干啥的?”
小伙子又看了看大娘,用嘶哑的嗓子很费劲儿地说:“大娘,俺、俺是去走亲戚的,路上碰上了巡逻的鬼子。”
大娘看了看他怀里紧抱着的那个包,说:“说实话吧,是不是八路军?大娘不会对外人说的。”
小伙子这才扔了手里的石头,说:“俺是八路军的卫生员,到王家峪三营送药品的。俺倒没让鬼子打伤,俺是饿坏了,快饿死了,渴死了!地里的庄稼还没结粒儿,这两天在这里,俺光吃草了!还吃生蚂蚱。”
大娘看他嘴上起了好几个泡,还裂开了血口子,忙从篮子里取出一个盛水的葫芦,递给小战士。小战士接过去,咕咚咕咚,只几口就把葫芦里的水喝了一大半。
大娘又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麸子和榆树皮做的野菜团子,递给小战士。小战士接过去,吭哧咬了一大口,接着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大娘嗔怪地说:“慢点儿!别噎着了!”
小战士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边嚼边说:“谢大娘!”又说:“俺怕村里有敌人,不敢上村里去。今天下午没看见敌人,俺想上山,赶路,可俺快饿死了,走不了了。”
大娘叹了一口气:“孩子,你先在这躲一会儿。到天黑了的工夫,你上俺家来,俺给你烧点儿菜汤喝。你放心,晚上二鬼子不来。”又问,“自己能走了去不?”
小战士说:“能!喝了水,吃了团子,有劲儿了!”
大娘指了指山下边:“就是庄最东头的那个小院。大核桃树下边的那个院。去的工夫别让人看见。”又问:“你没有枪吗?”小战士说:“没有。队长让俺穿便衣去送药,没让带枪。”大娘就把水葫芦和枣木棍子留给了小战士。
天黑下来了。大娘在厨房里的灶前烧火,小战士悄悄地进来了。大娘忙去把门闩上。去端来一瓦盆水,让小战士洗了脸洗了脚。又做了一锅榆叶汤,汤中放了大娘一直舍不得吃的一把棒子面。再拿来一叠用地瓜面、橡子面和糠摊的黑乎乎的煎饼,一碟子胡萝卜咸菜。小战士又大口大口地吃喝了起来。
大娘看小战士吃着,叹了口气,问他:“孩子,十几了?”
“十六。”
“当兵多长时间了?”
“一年三个月。”
“老家是哪里的?”
“青州的。”
“啊,离这不太远啊,也就三四百里路。”大娘又问:“家里还有啥人啊?”
“有娘和妹妹。”
“爹呢?”
“前年,俺爹让鬼子抓了去修炮楼。他受了凉,发高烧,干着干着活,晕倒了。鬼子硬说他装病,使棍子打他的头,把他活活地给打死了!”
“唉!”
“俺发誓为爹报仇,瞒着俺娘到南山里参加了八路军。首长看俺年龄不大,让俺当了卫生员。”
“你娘知道你当了八路吗?”
“后来,过了半年多,俺让一个老乡捎了个口信回去,俺娘才知道的。”
小战士吃饱了,大娘说:“你去炕上躺一会儿吧。”
小战士说:“大娘,俺吃饱了,有劲儿了。俺得找三营去。他们那里,有十几个伤病员,可需要这些药了。俺已经耽误了两天多了!”
大娘说:“那你,可千万小心着点儿。你知道路不?”
小战士说:“知道。这条路俺走过好几回了。”
大娘说:“那就走吧!一定小心着点儿。”就把家里的几个煎饼、几块咸菜全都用块笼布包上,交给了小战士。
小战士把笼布包贴在胸口上,说:“大娘,您把干粮都给了俺,您怎么办呢?”
大娘“唉”了一声说:“你就别管我了!”她看看小战士那让树枝子刮破了的褂子和裤子,露出脚趾头的布鞋,又找出洗得干干净净放了好几年的儿子的衣服和鞋子,让小战士换上。
小战士说:“大娘,您救了俺的命,等抗战胜利以后,俺一定来看您老人家的。”
大娘点点头,又责怪地说:“儿啊,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娘吗?”
小战士“扑通”一声跪下了,流着泪说:“娘!娘!刚才俺就老想叫娘呢。”
大娘拉起了小战士,说:“儿啊,走吧!别忘了娘就行啊!”
大娘先出去看了看,又回来,领着小战士出了门,把他一直送到了大核桃树下,指着一边的山坡,说:“从小路上去。”小战士走出去了十几步,又转回身来,抬起右手,向大娘行了一个八路军的军礼。
一年之后,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娘每天傍晚都到坡上的那棵大核桃树下去,往东边看。乡亲们说,她这是在等她的八路儿子呢。
枪炮声又响起来了,一响就是两年多。大娘还是每天傍晚到山坡上去,站在那棵大核桃树下,往东边看。但八路儿子一直没回来。
村里有去支前的民工,大娘托他们打听一下自己的八路儿子。人家问:那个卫生员叫啥名字,是哪个部队的?大娘愣住了。当时,竟连儿子的名字都没问。人家说,那俺上哪个部队去找啊!
乡亲们对她说:“你那个儿子,可能是打台湾去了,台湾还没解放呢。”也有的乡亲私下里嘀嘀咕咕,那个小八路卫生员,很可能是牺牲了。要不,怎么连封信也不打回来呢?也有的说,人家可能是当了官了,早把这个蒙山娘给忘了。
又是一年过去了,大娘的头发更白了。老人弯着腰,拄着枣木棍子,站在大核桃树下,山风吹动着她的白发、她的旧大襟褂子。她那削瘦的身子,就像要倒似的。村里的人说,大娘可能等不到她的八路儿子了。
但,就在秋季的一个傍晚,当大娘弯着腰,双手拄着棍子,在山坡上的大核桃树下站了一阵子,准备往回走时,她突然看见,山路上走来了一个穿黄军装的人,背上还背了一个背包。穿黄军装的人越走越近。哎,这是谁呀?这莫不是俺的八路儿子吗?可俺儿没这么高呀?穿黄军装的人走着走着,突然跑了起来,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娘!娘!娘啊!”
军人跑上来,一条腿跪下,就抱住了娘的腿。娘抚摸着儿子的头,拍打着儿子的肩膀,泪水一滴一滴,掉在了儿子的军帽上。
“儿啊,你可想煞娘了!”
儿子站了起来,娘这才发现,儿子左边的袖子是空的。娘用粗糙的手抚摸着那只空袖管:“儿啊,你这个子长了有一头,可你的这条胳膊呢?”
儿子说:“打上海的工夫,我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敌人的一发炮弹落下来,我趴在了伤员身上,伤员没再受伤,可自己的这条胳膊给炸掉了。不过,捡了一条命。要不,就见不着娘了。”儿子笑笑说。
娘“嗨”了一声,又问:“儿啊,你走了这5年多,怎么就不给娘写封信来呢?”
儿子说:“俺写过呀,写过七八封呢。”
娘长叹了一口气:“俺可是一封也没收到啊!”
儿子搀着娘回到了家,打开挎包,取出了给娘买的衣服、鞋子,还有点心、糖、南方的茶叶。又给娘看自己得的6枚军功章,有淮海战役的,渡江战役的,还有打大嶝岛得的。
“儿啊,大嶝岛在哪里呀?”
“在福建那边的海上,离金门不远了。”
“哎哟,俺儿打了多少仗啊!”娘笑了起来。
本以为儿子是来看看娘,住两天就走的。可儿子说:“娘,俺退伍了。俺不走了。俺就住下了,俺要伺候您,给您养老。”
娘愣住了,说:“儿啊,这可不行。你来看看娘,娘死了也就合上眼了。你还是回你的老家去吧,去伺候你的亲娘。”
儿子说:“俺娘有俺妹妹照顾呢,没事儿。”
“那也不行。”
儿子住了几天,娘又撵儿子走,但儿子就是不走。
儿子就这样住下了。他用一只手给娘种地,给娘打水挑水,给娘养了几只山羊。又用复员费给娘翻盖了房子,重修了院墙,还给娘治好了胃病和腿病。娘渐渐地壮实多了,走路也不拄棍子了。忙前忙后,浑身是劲。头发也变黑了许多。
村里人知道了这个转业八路军医会看病,也都来找他看病。八路军医给好多男女老少治好了病。后来,邻村的许多人也来找八路军医看病。尽管他再三纠正,说自己在部队只是个卫生员,可乡亲们还是叫他八路军医。
过了一年,一个扎两条大辫子的红脸蛋沂蒙山女孩走进了这个小院,成了八路军医的妻子。八路军医曾给女孩的爷爷治好了腿伤。
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当了奶奶的老人乐得合不拢嘴。她一只手揽着一个,给孙子孙女唱民歌《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说哎嗨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嗨哎,好风光……”
又过了20多年,孙子孙女又给老人生了重孙子重外孙女。老人更是乐得哈哈大笑。
老人活到98岁,无疾而终。临走时,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子媳妇外孙女外孙女婿重孙子重外孙女围在她的身旁。她一只手拉着八路儿子,一只手拉着儿媳妇,满是皱纹的脸上是无比幸福的微笑。
已是满头白发的独臂八路儿子和儿媳带儿孙们,把老人的骨灰盒埋在了当年老人救了八路儿子的那个山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