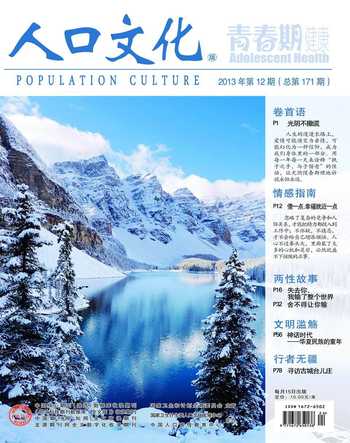爱在沉默岁月里开花
周华
她嫁给他的那一天,哭得死去活来,好像生活从此一片黑暗。
她很漂亮,大眼睛、小嘴巴,皮肤白净光洁,身材苗条,长发如瀑,走起路来像一朵花儿在风中摇曳。他是村小学的老师,长得又胖又黑,还比她矮半个头。
那时,她已经有了心上人,是省城来的地质勘探员。勘探员在离村子不远的河边搭起帐篷,长得高大威猛,有着古铜色的肌肤。她和地质勘探员一见钟情,她给他纳鞋底,给他挑手掌上的刺,给他洗衣服。勘探员给她讲城里的新鲜事,把她带到树林深处吻她,用滚烫的声音对她说:“我爱你。”
地质勘探员回省城时,对她说一年后一定来娶她。可还没有过一年,她就被父母强迫嫁给他。这一年,是1970年。
婚后,她很痛苦。他是一个本分到近乎迂腐的男人,不会说甜言蜜语,只是不声不响地为她做这做那。他上山摘野果,到田里捉泥鳅,拿到城里卖钱,扯来花布给她做衣服。可她对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感觉,在抱怨和无奈中,她生下三个孩子。对她来说,生活是一片毫无生机的泥沼,她深陷其中,无力自拨。
他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们懂事后,他带着他们去县城看电影,看的全是武侠片,他觉得这样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看完电影回家,天已经黑了。煤油灯下,孩子们一边吃饭,一边叽叽喳喳地给她讲电影里的故事,大女儿给她描述人物的穿着打扮,二女儿给她背有趣的台词,调皮的小儿子干脆拿起墙角的扁担,像电影里的侠客那样挥舞起来。他坐在一旁,当她有不明白的地方,赶紧讲解。这一刻,她觉得生活不再是毫无生机,而是开满鲜花。
1979年夏天,勘探员忽然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省城。她的心依然跳得像擂鼓一样,她回家胡乱收拾几件衣服,就冲出家门。汽车在公路上飞驰,她突然感觉到惶惶不安。她向车外望去,天色已经昏暗,到了为孩子和丈夫做晚饭的时间了。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大声冲司机喊道:“我要下车。”司机停下车,她冲下去,往家的方向跑。
远远地,他站在村口,一脸焦急地张望。她迎上去,“我们回家吧。”他哽咽着,“我们回家。”那一夜,她偎在他的怀里,睡得很安稳。
1985年,他因为工作出色,调到附近的煤矿子弟学校当老师,一家人从村里搬到矿区。全家只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自然很艰辛。孩子们正在长身体,每天都喊饿。为了补贴家用,她给建筑工地挑水泥担沙子,赚钱贴补家用。因为营养跟不上,她几次昏倒在工地上。
看着妻子瘦弱的样子,他心里就痛。矿工每个月的工资比教师要多30元,为了让一家老小过得好些,他下井做了矿工。他下井挖矿的第二十天,矿井发生倒塌。他醒来的时候,躺在医院里,全家人都围在他的床边。他紧紧抓住她的手,泪水止不住从眼角流出,他说自己差点就永远见不到她了。她把他搂进怀里,像搂着失而复得的珍宝。她坚决不同意他再去挖矿,他听了她的话,重新回学校做老师。
光阴似箭,两个女儿相继考上大学。为了供两个孩子读大学,她白天操持家务,晚上做棉鞋卖。他总是陪在她旁边,给她讲《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榜》里的故事。她听得入神,不知不觉间一双棉鞋就做好了。
两个女儿终于读完大学,参加工作,每月都会给老两口寄一些生活费。小儿子虽然连高中都没考上,但也还争气,在矿区开了一家夜宵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她渐渐变得啰嗦起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她很想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可惜走不动了。但他自有办法,他买来地图,带着她在地图上旅游,从西安到兰州,经天水,过嘉峪关,直达梦中的敦煌;他还带着她凭吊赤壁,登岳阳楼。每次看到地图,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鸟,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变成了花蕾,当他的手指指向它们时,它们就像花一样开放了。
她56岁生日,儿女们齐聚一堂为她贺寿,她喝了一些酒,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霞。调皮的二女儿向她打趣:“父亲跟你说过‘我爱你吗?”她忽然想起,他从没有对她说过这三个字。
她要他说。他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说道:“都老夫老妻了,说那肉麻话干吗啊?”她不依,一定要他说。他还是说不出口,摸着她的脸说:“你这张老脸,我咋就怎么也看不够呢?”“这个死老头。”她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向他的胸膛,落下去的时候却很轻。
他从没向她说过“我爱你”,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后来,她经常在儿女面前感慨:“幸亏嫁给了你们的父亲。”
(编辑 高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