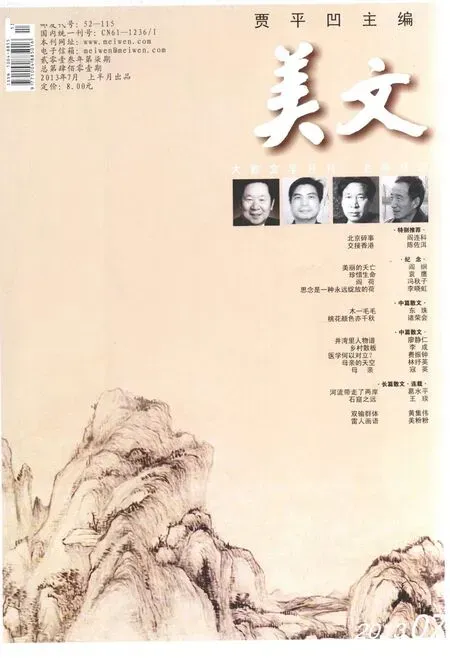宿命的阅读
高晖

“我是从哪里来的?”记得从5岁起,我就开始向身边的大人征求答案,但他们给我的说法不一,如:桥头捡来的、亮中集市买来的、用小黄牛与老郑家换来的。当时,我自然不晓得哪个答案正确,但还是觉得他们没说清我的真正来源。于是,接着问“我第一回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母亲拒答:“你这死孩子就愿意刨根问底!”说着,扔过一本书,可能是想以此作为武器攻击我。飞来的这本书就是著名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拿起这本书,当时我并不能连贯地读下来——里面陌生的字太多,也不知道里面有我的问题的标准答案,就没有啃下去。不过,我还是决定慢慢地看完,当时没有什么读物。后来,肯定是有了更好的念头,这本书被我读完一点就放在一边了。不过,我因此学会很多字。这就是我阅读生活的序曲。
我的阅读生活真正开始,是与避孕套有关。在我上学的前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村西头儿突然冒出一卡车,装满一摞摞纸箱,车上有一女,手拿胡萝卜,叽里呱啦地讲,我们这些孩子听不清也听不懂。当时,全村大人都在。然后,讲话女开始组织拆、分箱子,里面的东西一下子掉出来,花花绿绿的小包,随便拿。那东西呈透明装,且黏乎乎,我的伙伴小六子首先发现能吹成气球。于是,全村孩子,都吹疯了。顷刻,我村被白气球覆盖。成年人说这东西叫“炮皮子”,矿里装炸药用的。至此,避孕套在我村首次成为爆破用语。只要有的吹,孩子也接受这个命名及功用。但我还是有些疑问:也没炸药,弄这多“炮皮子”干吗?单是让我们吹气球?不会的,成年人从来没有对我们这样好过。晚上,我开始研读说明书,其中有一个词不懂——“快感”。突然,我想起来,就在那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里有过这个词语,我开始逐行查找。没过几天,这本书被我读完了,其实并没有完,只是后边的部分被大人当做抽烟纸了——这本书消失在286页——我清晰地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刻,就是那个秋天的夜晚,我跑出去望着星空,心里空落落的:原来人是这个样子啊!我有很多委屈。现在想来,我的真正的童年生活在那一刻已经结束。
我开始贪恋书,是从发现书的味道开始的。那时,上小学一年级第6天才发课本。班主任挨桌发课本,我在后排,这样便有了几分钟的期待,我猜想她从前往后依次发放的那种东西一定是非同寻常的物件。放在我眼前的是两本书,语文和数学。我绝对是先拿的语文课本,翻开书页的瞬间,首先感觉到的不是颜色、文字和拼音,而是气味。一种浓烈的特别气味钻进我的鼻子里,香甜、苦涩、绵长,是那样特别,总之,那是我现在仍然能完全记清的气味。那是平生第一次触及这样的气味,当时我的鼻翼肯定是富于节奏地吸动着,那里面柔静的绒毛也会蠕动若干下,手也随之颤动着,两腮红润。这样美妙的气味就在我并不十分在意的时候出现了。后来才知道,人们把这种味道定义为墨香。当我发现这种愚蠢的定义应该遭到反对的时候,早就来不及了,大家很早以前就这么叫了。
在我读小学的大半时间里,我都无法逃离这种味道的诱惑。每当新书发到手上的那些日子,我甚至舍不得去看它,只是闻。书一般在没有翻阅的时候才有这种味道,用久了,夹在书页之间的味道就淡了,最后的结局是散尽。一写到“书”字,首先感到的是关于那种味道的记忆,然后才是书的实体。这使我想到,某些神秘的东西是先从气味开始的。这种开始是一种先兆,一种灵光,然后,那实物便隐隐约约地出现了。那种东西消失的时候,气味也是最后离开的,实物走了很远,淡淡的气味仍然滞留着。味道是一件事情的开始时刻和结束时刻。
接着,我开始寻找家里一切能阅读的东西。我开始完整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在1977年冬天。有一天早上,家里没人。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常常是我一个人躺在炕上,早上阳光从窗子透过来,照在炕席上:有我,还有一只老猫,黑的或花的。的确,那时我和猫身上也常常是有阳光的。那天,还多了一个物件,就是那本书。一定是爸爸临走时落下的。我从炕席上拿起那本书,发现里面有图片,就开始一页一页地翻,先挑图片看。图片上有吉普车、有各种枪械,更让我心驰神往的是,那辆吉普车是水陆两用的,开到水里就是船。此后,我一直梦想自己能驾驶那样一辆车,车里放的是那堆各式各样的枪。我在地上飞也似的跑,后边得有敌人追,当然敌人是越多越好,然后是,他们刚要追上我,我一下子把车开到水里。图片毕竟在那本书里有限,不一会儿就看完了,这时,我才考虑到看一看图片以外的东西。书上说,那辆美妙的车是林彪那个著名的儿子林立果的,有一堆上边带电台的枪也是这家伙的;而另一堆长枪,也叫猎枪是王洪文的。为搞清楚他们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我准备从头开看。就这样,我大约花两天空闲时间看完了那本书。这本书比一般的书大许多,没皮儿,只是几个鲜红的大字“中共中央文件”。
我这次阅读经历是疲惫的,几乎因此丧失了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记忆。看过几行还会遇到几个我不认识的字,只能硬着头皮念下去。那次,我是带着问题阅读的,所以十分在意车和枪这样的字眼儿,似乎从头到尾只是那几幅照片的周围有这样的字眼儿,其他的话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让我无法理解。我只能获得一些单纯的印象,比如说:江青写的连笔字比我们老师写得还好呢!张春桥看起来就像坏人。王洪文长得挺好。林彪的眼眉特别黑。就是这些人,想把毛主席整死吗?
那几天,我的情绪相当复杂,晚上的时候,老半天睡不着,想着书里的片言只语。这本书给我提供的刺激以及设下的疑问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自拔。它给我的童年平添了许多抽象的概念,比如阴谋、迫害、斗争……“571工程纪要”。后来有一天,爸爸回家急匆匆地找那本书,我在一边看着:“我没看见,真没看见。”就这样,这本书没有被缴上去。因为藏错了地方,直到我15岁那年搬家时才在仓库里找到它,已经被老鼠吃得差不多了。
我的第一本完整读物竟是中央文件,这是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读物中最深奥难读的一种,别说当时,就是现在我也很难读懂。不过,这种超前行为让我养成了读各种文件的癖好,关于执政党的一切我能见到的文件资料以及政治教材、领袖传记之类读物,我都能读下去并能留下印象。比如,北京开了什么会,我就找报纸上的讲话看,记不住也看,喜欢受那种抽象词语的刺激。我常常只是从文体意义上产生一些想法。我觉得,现在的文风时常被人们忽略,官样文章写得太愚蠢缺少应有的力量,像我这样有较好阅读训练的人看着都费劲,很难让更多人读懂。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报告是玩不得现代派的。我读过一遍《毛泽东选集》,话说得明白,有劲。真正的口语方式必须得有节奏,有适度的停顿。
随后,我开始读第二本。那是本小说,当时称之为“大书”。封面是胖墩墩的一个男孩的半身像,我记得是穿着蓝衣裳。书的名字叫《新来的小石柱》,谁写的我早就记不清了。讲的是一个体操队员小石柱的故事。一个乡下孩子,一个会翻筋斗的乡下孩子,偶尔被教练选中,来到少年体操队。这孩子是新来的,功课、生活还有专业都跟不上,于是他就刻苦适应,赢得了小伙伴的佩服和教师的夸奖,最后在一次大型比赛中拿了冠军。似乎还有一个孩子,被安排成有些资产阶级生活习惯的孩子,爱吃一些小食品,后来他没比过小石柱。
就是这么一本普通的故事书,很多人也许记不得书名和情节。我记得这本书在我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里举足轻重。当小石柱在集体中孤独的时候,常常到一片小树林里,在这小树林里想家、练功,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始终难忘:这片小树林里有一棵笔直的小树,小石柱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上面划一道痕,盼望自己能快些长高。这成长的愿望让我迷恋了许久。其实,这是多么普通的愿望,对于我却成了某种象征,它象征着我童年和少年积极向上的那一部分生活。想来,这本书不过是极普通的一本文学儿童读物,一定不是深沉博大的那种书。不过,这没关系,这本书诱导了我对自己生活中向上那部分东西的理解,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特别是我当时那个年龄。小石柱成了我那一时期生活中的一个榜样,单纯、善良而勤劳的榜样,特别是能自己默默地承受一些东西的榜样。总之,《新来的小石柱》给我带来了丰富而温暖的阅读感受,小石柱在练功之前对树的默想,上单杠前对奶奶的思念,这里面就包含了梦想、祈祷和信仰。其实,这类书籍对人的启示常常在于诱引,诱引出与自己当时精神契合的一种场物质,这种场物质会笼罩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的个人心灵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临摹般的人格仿真,这样的仿真久了,也就逼向了心灵深处。
后来,我开始享受阅读给我带来的荣耀。如果没有记错,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早上,在我的家乡——康家村小学。那时的学校是两栋并排的土房,靠大门一侧的两面房山有两块黑板报,用水泥抹成的。那个早上,我发现了它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花了很长时间读完了上面的字。日记。一个女生的日记,主要是谈及黄帅对她的影响。日记的主人是我上两个年级的同学,盛爱玲。看那些字的时候,我生出了一个念头,我也要写日记,并要把他们写在黑板报上。一年以后,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写了学习杨滢的体会。放学的时候,我躲在一旁,偷偷地看教画画的老师一笔一画地往黑板报上抄我的日记,一直抄到天黑。那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同学都会发现我的日记写在上面了,我兴奋极了。后来,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夜里下了一场雨,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黑板报上是一条一条的白茬儿,难看死了。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就这样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我难过极了。怎么那样巧?那雨怎么偏偏冲我的方向下过来?我开始贪恋叙述的力量,它可以把我和那些不叙述的人区分开。
初中时,我的作文又有几次作为范文写在黑板报上,趁没有人的时候,我从头到尾地看完,心里砰砰直跳,然后在有同学们表示羡慕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这有什么,我才不在乎呢。”其实,整个小学和初中,我读的一些书都是随机的,没有什么选择性和系统性,那期间我甚至没有去过书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妈妈成为公社文化站的图书管理员,全站除马恩列斯、毛泽东选集等政治书籍没有看全,其他的文学类书籍我几乎都看过。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初中二年级时,我想参加春风杂志的文学青年函授,需要6元钱。在一个黄昏,我向姥姥说了这件事,她为给不给我“投资”整整决策了一个下午。最后,她说:“就当丢了。”结果是那些用“巨资”买来的书籍,我无法看懂——我不敢和姥姥说这些。那时的6元钱现在值多少,我不知道,但我记得:那几乎是姥姥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一。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去县城书店,我惊奇地发现,那里面零零落落堆着一些书,几乎都是我读过的东西。
1987年秋天,当时在煤城读中专,我和一些同学去了一趟叫塔子沟的山,来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便不想再上去了,我决定在底下给他们看衣服。我躺在那里吸烟,想着我的青春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挺入神,入神的后果是我烧着了身边的杂草,若不是我扑救的及时,恐怕那座野山早就草木皆无。我用自己的衣服扑灭了周围的火苗。我独自一人重新躺下来,闻着草木余灰浓烈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实实在在地活着,特别开心;我投入一种并不盲目的冲动中:我想就这样活下去,就这样活下去。我当时认为,这样想并没有什么错。又有一些东西离我远了,同时也又有一些东西离我近了。值得庆幸的是,那时,我又记起了少年时的黄昏。我想感谢那块荒墟刚劫的土地,它支持我躺下来,这是一种可以看见天的姿态。其实,读书就是一种看天的姿势。后来,我在看书的时候,常常在书页上出现这样的场景。
其实,我前半生最重要的阅读生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曾经在《煤城往事》里面写过:“煤城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书店。”煤城有一家四层楼的新华书店,里面的文学、哲学整整占了两层,那时已经有人开始大面积阅读,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找到这些家伙都藏在什么地方。我清晰地记得,那次我买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的《词语》、欧文·斯通的《心灵的激情》,还有一本旧书《渴望生活》——也是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记》,上面还载着一个蓝色的戳记:镇江市水产养殖场工会图书室。那时候,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的手头总是要有几本这样的书,否则根本没脸见人。第一本,我根本没有看懂,至今也没有再看;第二本,我看了一些,然后就放下,这样的书根本就不是给人看的,只能是翻阅,信息量庞大、密集,而且让人头疼;第三本,我可以断断续续地看下去;第四本,写弗洛伊德故事的《心灵的激情》——后来,我庆幸自己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与这样一本书相遇;至于《渴望生活》,那本旧书,我甚至不敢立即读完——每当遇到特别的书都是这样——我不敢读完——读完这本书以后的生活该怎样继续下去呢?即使是现在,像这样随意说出一本震动过我灵魂的书,自己都有些后悔,就像轻易地说出自己的隐私一样。断断续续写作的这些年,我始终不喜欢作家推荐书目这样的文章,都是瞎掰,好书,对于那些特定的写作者,就像情人一样属于隐私。我永远都能背诵梵高的一些话,比如这句:“真正的画家是受心灵(即所谓热烈的感情)指导的;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画笔的奴隶,而是画笔要听从头脑的指挥”。
那时,还有一本书异常重要,就是《金蔷薇》,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俄罗斯散文。我记得那是一个午夜,我在自己的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这又是一本买后没看的书,因为刚读到一个外国大师谈到了这本书,我就找出了看。翻开正文的第一页,我的心开始激烈地跳动。舍不得看,有些书我们真的舍不得马上看完,只是担心看完以后的日子怎样打法。这是一本有香气、有旋律的书。我真高兴,在自己开始写作不久遇见了它,感谢这个苏联人,感谢我们的译者。刘晓枫说,60年代出生的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坚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但是,就是这本小册子,导致我开始怀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里面的激情,觉得为保尔而流下的泪水是那样幼稚。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重新配置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诗句。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代人曾误解过奇迹,听信过伪造的奇迹。实际上,奇迹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字架受难中所显示的奇迹。于是,我们开始学习关于怕和爱的生活。就像刘晓枫所说,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
我常常是这样:用整整一个晚上或者更多的时间来收拾书,我那一排排地摆在书架上的书。程序大体上是,先一摞摞地将书从架子上抱下来,放在写字台上,一本本地翻。这时,我能集中几乎全部的精力盯着书上面的字。字几乎都看不大清,心在忽闪忽闪地动,只有一个念头:这本是什么时候买的?当时是什么情景?我看过没有?我喜欢这样的时刻,这种时刻我呼吸的声音与书页的稀疏声混合在一起,让我感受着一种难得的踏实。
拿下来的书多了,架子上的书就少了。直到我差不多被书埋在里边了,才慢慢地站起来,生怕弄倒四周耸立着的书,然后一本一本地往架上放。放的时候没有什么规矩,都是随手之间的事,偶尔会突然蹦出一本想看的时候找不见的书。或者,发现了一本别人没有的,也没有谈论过的书。这时,我会在心中涌起一阵不应该的兴奋,像守财奴私藏了什么宝贝未被人发现那样。我一遍遍地抚摸书皮和书背,想法变得单纯明朗:有这些书读,还要别的干什么?甚至,写作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读书原本是和写作没什么直接联系的事。我知道,有些书的高度,我是永远无法企及的,这不是单靠勤劳就可以弄懂的,这需要造化和天分,在好书面前,我无数次地脱帽致敬。也只能这样。其实,对于一些书,用几十年时间能读懂就不错了。这样想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绝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然而,充满希望的是我发现并且读到了一些真正的好书。
我有些疑惑,对那许许多多个没有读书的日子;那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我只能这样解释,那些时候,我并不需要读书,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什么是需要呢?就像人对于水、阳光和空气。更确切地说,我当时没有能力发现这种需要。最简单的道理往往都是最后才认清的。
书读得渐渐多了一些,就不免写些读后感类的东西,我倒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什么评论。我的想法大都是感性的。直到有一天,我被一些人称为是评论家的时候,才看看以往自己写的那些东西。那的确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尽管有些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刊物上。我几乎看不完现在市面上的评论文章,有的文章看了几眼之后,就发现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细看人家的原作,在那里“自成体系”地瞎蒙,直写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的时候,才肯停笔。由于没有自己的感受,才制造一些高难的理论,用概念推倒概念,最终呈现出高高在上的面貌,将个人应有的审美鉴赏力模式化了,就是这些程式化的东西将巨大的概念变得神秘莫测。我真的想推倒那些艰涩的概念,把一些东西向每个有一般理解力的、20岁左右的文学青年解释清楚。我终使认为,所谓的评论,必须对单个的文本下一个单个的定义,否则就会远离这个文本本身——所有的思想系统都应该建立在个体读者的感受之上。我还认为,理想的读者就是野蛮的读者,是那些没有“预设概念”的读者,把文本当作一个封闭的世界阅读,又把它放在开放的同类整体中去“系统”。
兰德尔·贾雷尔,这个英国诗人,在1853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读者,真正的读者,几乎同作家一样是野蛮民族,而大多数批评家则属于——似乎建立了种种制度的驯顺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相信自己是野蛮的读者,努力与自己所关注的每一位作家相和而又保持双方的个性。我始终喜欢那些野蛮而理智的批评。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已经成了朋友间的窃窃私语,到底是评论缺少了什么,还是读评论的人缺少了什么?喜欢读书的人根本不用读什么评论,然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肯定会写一些读后感的。评论和读后感不是一档子事儿。也许,好的评论就出现在读后感里呢。
现在,我想说的是,一本书你能读下去,就对你重要。一个人是否适应某些书,这很重要。读好书就是剥离自己的过程,就是把自己内心被层层包裹的东西剥离出来,显露出内心最柔软、最丰富、最具想象力的东西。读书能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个作家为什么读书呢?我认为有这么4个目的:一是模仿。其实,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在模仿一些你喜欢的作家的手法,甚至是后来这种模仿也不能幸免,最后才是隐退了形式追究其内容。我曾经说过,新时期文学的30年,就是中国作家模仿外国作家的30年。我甚至可以说出新时期每部重要作品的背后是什么。二是思考方式。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一个人内心成长的过程和你强烈的表达愿望是成反比的。三是形成内在的语言系统。感受自己内心的真实需要是形成稳定的内语言系统的根基。语言问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是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作家形成了什么样的语言系统和模式,与读什么样的书关联很大。四是感悟。读书无论怎么重要,与写作本身相比都显得逊色。写作就是写作,它是上帝安排给人类中一小部分人的特殊任务,是以作家内在生命的感悟作为支撑的,作家的生命仅仅是一块试验田地、试验器皿,本来无需用自身生命以外的东西做相关支撑,但是书籍可以诱引,诱引出形式感甚至内容。比如,我在一本1973年出版的科普读物《怎样养兔》中读出另外一种东西,于是写出中篇小说《杀人犯吴玉刚印象记》。当时,我写小说,找不到特别的形式感就没有话说。很多书籍让我看到了小说的形式感。于是,有了第一句就有了第二句。
我想起一个故事,应该是美国小说家辛格写的,除了他谁还能有这样的方式呢?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美国小镇。一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妈妈让他去买调味品,他把钱丢了,就没敢回家。然而,伪装过的孩子就在家附近。一直过了好多年。好多年以后,他看着家里发生的变化。直到有一天,他回家,大喊:“东西买回来了。”这个出色的短篇,很多年前,我就看到了,记住了。也许这里面有沧桑和震撼。对了,震撼应该有时间长度,那就是沧桑。沧桑如果有惊人的细部就会震撼。
6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的阅读经历和生活经历大体相同,但每个作家呈现出状态大不相同。虽然时间会让与文学相关的审美法则发生些许变化,但文学还是根基于传统。无论怎样,任何文学的审美法则都不能作为创作的依赖,好的作家从来不跟随思潮来创作。文学作品要想恒久就得抛弃当下的世俗价值和所谓的主流价值,比如,张贤亮的作品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它们在80年代中国的人性启蒙过程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应该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子,他当时的作品无异于原子弹爆炸。余华的创作呈现出60年代作家的特征,个体生命的感受开始浓郁,个体对世界的惊恐、残酷的尖锐体验构成了余华小说的重要因素。还有,就是他会很朴素的说话。仔细想想,与国外一流大师相比,余华还是缺少某种东西。是什么呢?忏悔感、沧桑感。我们常常提起的苏童,苏童的长篇创作一般,但他堪称短篇小说的大师,他能写出短篇的色彩、旋律、节奏。当我们读了乔伊斯、辛格和卡佛的一些短篇后,会更加觉得苏童真的了不起。还有韩东,抛开创作指向不说,单说他可以让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感——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状态,阅读这类小说,就会发现读者需要智力、心性方面的准备。还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寥寥两万字的作品,我们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梦想、生死、祈祷、忏悔、宿命,几乎什么因素都有了。作为自然人,史铁生是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同时他又是这个世界上精神最为健全的人。作为作家,他又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没有人可以复制他。
阅读经验告诉我,近百年来,中国作家从来不缺“贴着地面行走”的东西,缺少的恰恰是幻想性的元素、浪漫的元素和丰富的人性因素,总之,是需要精神提升。我们这个民族在先秦,在唐宋,精神领域曾经达到过无与伦比的高度。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达到了一个高点。事实上,新时期以来,哲学、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已经出现了经典,只是因为时空的原因,我们不愿轻率地将经典和大师的桂冠给那些优异的作品和制造它们的艺术家。
其实,从童年开始的阅读生活,并没有教会我什么有力量的东西,倒是让我养成了按照书上描述的办法处理感情生活的不良习惯,特别是一牵扯到细节更是如此。这样,我的青春期的真实焦灼——再掺杂上小说里主人公的心灵磨难,就使我那段生活感受变本加厉,甚至一时无法分清那种状况更加真实。阅读变得艰难的时候,往往是对这世界感受零乱的时候;这种状态往往不如写作艰难表现得尖锐。捧了一本书,刚看过几页,就被迫停滞了:脑袋里大都是想着与书里相反的事情;然后是拿起另一本,状况依然。这样,在一个晚上要拿起放下十来本书。起先并不大在意,后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了,就开始问自己: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不能集中地进入一本书里?无法进入写作的时候脑子和纸都是空白的,很容易让人急躁,像跑在路上的车子,一下子没油了。无法进入阅读的时候似乎比这好一些,虽然眼睛不能一行行地走下去,脑子里却是满满的。都是些书和纸之外的想法,当然就是这时现实世界里各种细微的事情也便乘虚而入了。现实世界强烈地干扰着我顺着一个思路想下去。我首先想到的是阅读内部出现了异常。其实也应该这样,在停顿的时候想想这件事情本身或许也是某种持续。
准备阅读的时候,我当然期待着能一本本连续地读下去,次序和完整是我关心的两个基本内容。现在,不但这两方面都因受到阻力而扭转了方向,而且出现了一拿起书就想放下的情况。当我的眼睛对书以外的物件的兴趣大大减弱的时候,一些丧失也随之凸现出来。我由一个行为敏锐的人变得步履迟缓,这肯定是阅读导致的一个结果。读书给我制造的慵懒使我失掉了伸入现实生活的若干次机会,这是事实而且是我没有心情抱怨的事实。我的大部分快乐和悲伤注定要围绕阅读而发生。那么,让我们把话题集中在阅读本身,这样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阅读艰难时常常让人想起初衷。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顺手翻翻,最多只是被故事吸引;时间一长,连自己也控制不住局面了,成了一种习惯和需要。这样,需要被阻碍的时候受到挫伤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读书使我能沿着一个思路想下去,就像顺风而行的帆船。我真不情愿承认,我其实是个既没勇气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又不想睁开眼看世界的人,开始时肯定不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眼睛一盯着现实世界里不直观存在的事,心里就舒服。阅读的时候,我蜕变成了一个梦中人,也许就在这时开始改变初衷了。阅读变成了某种对抗,无言无语的对抗。在人声嘈杂的地方,你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本,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读书成了停顿,上面的说法还能继续吗?如果说有序的部分逐渐增大是这个世界进步的根本标志之一,那么个人的进步可不可以这样呢?有时,我们就像乘坐在一艘颠颠倒倒的大船上,失重恶心这些震荡大都是由这艘船带来的,然而作用于每位乘客身上肯定会有些细微的差别。我知道差别的根源,不是说我能忘记正在进行的斜倾和下沉,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自己再制造一艘小船?我应该有这个愿望。读书就是一种睡眠了,睡眠是一种假死状态,那么读书也是这样的状态吗?是想把自己冷冻起来,在适合自己活命的时候再活过来吗?这些设问和阅读有什么本真的联系吗?
在我还没有学会读书的时候,甚至在没有学会集中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贪恋水了。整个童年几乎都潜在水里。我学会了扎猛子,就是试图在水中呆尽可能多的时间:先吸一口气,然后把头扎在水中憋气,刚开始的时候在水中什么也来不及想,后来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逼迫自己在水中想一件事,想出结果来,再伸出脑袋,再了一口气。那都是些简单的事,甚至只能说是场景,不是什么事。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常常是胸闷气短,两颊绯红,这时的呼出和吸入是贪婪而致命的。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吸进的是氧气,书里这样说。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呼吸这般科学,然而我却体会到严重了。那时的水是污浊的水,甚至应该是有害的,我当时没能力留意这些,童年的眼里什么东西都是干净的。那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能在水中“换气”,据大人说,有人能做到在水中呆一天一夜而不必呼吸,都是些我无法看见的人,不是死了就是不在我的家乡。后来,看到书里说的潜水衣,我神往了很久,虽说也是衣服,但那毕竟是能在水里换气的衣服啊?
现在,我知道——阅读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宿命。那么,什么时候,我不需要读书,不必为阅读艰难担心了呢?那时,我心中肯定会有一部无需删改的大书了。这又是一个梦想,是我成年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