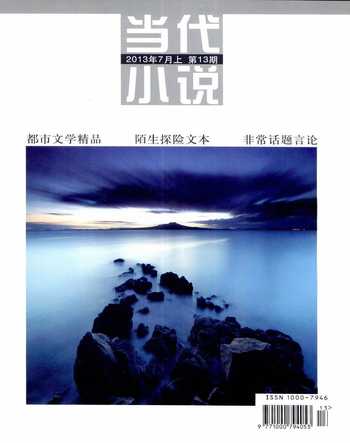做暖
马卫巍
王兰菊想给女儿林小琼做暖是在一年前。想起崭新的暖裹在身上,她的心头突然荡起一片阳光,照得通身暖暖的透着舒泰。暖就是被子,雪白的棉花,绵绵的丝布,细密的针脚儿。加上自然的温度,摸在手里觉得像水、像鱼,更像天上飘着的一团白云。
王兰菊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五年前老伴去世,娘俩相依为命。她把林小琼捧在手心藏在心窝,生怕她有个什么闪失。日子像手中一正一反串起来的针脚,在手指的缝隙里悄悄溜走了。林小琼长大成熟,变成了一只朝气蓬勃、通身含香的水蜜桃,掐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会流出一汪甜丝丝的蜜水。王兰菊当年就是这么水灵来着,凸凹有致,落落大方。女人到了这个年纪。身体中筑起了一道宽阔的闸口。外表风平浪静,心底深处却风起云涌。所以,十八岁的王兰菊被小羊倌放倒在吐着碧绿嫩草的田野上时,她身体里的水突然奔泻而下,波涛汹涌,好像在汪洋里畅游,激荡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地成了王兰菊的暖,她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把自己彻底暴露在阳光下。那是一种跌宕心扉的暖意,通透全身,令人终生难忘。几年之后,王兰菊嫁给林旺太时,还会记得自己第一次的那种感觉:有些痛,痛得沁骨噬心,有些酥,酥得化骨出神。林旺太在王兰菊身上折腾了半天,浑身的大汗润湿了半床被子才心满意足地躺了下来。他摸着两只跳跃的小太阳说,你的身子真像一床温柔的暖。
那时候。王兰菊和林旺太还在农村,家里四亩多地,其中有两亩梨园。另外两亩,王兰菊有时种玉米、小麦,有时栽种棉花。入了秋的阳光贴在脸上,整个人都溢满了精气神,一朵朵盛开如雪的棉花闪烁在颤巍巍的秋风里,荡漾着一份暖意。采摘棉花之后,王兰菊会到弓房弹成一床床被子的模型。在铺满深秋暖阳的院子里,一针一线地缝着。线是自己纺的,棉布是自己织的,用起来得心应手。王兰菊做暖的时候,林旺太会悄悄搂住她的腰肢。像搂着一株摇荡在春风里的棉花苗。一只手顺着蔓延的枝子向上,一只手顺着柔软如丝的腰身向下。王兰菊打了个激灵,身体即刻荡满了晶莹的水珠,两个人滚在雪白的棉花堆里,变成了两只野兔。天空成了暖被,地面成了花床,两个人的身上渗出温热的潮气,沾满了白花花的棉絮。王兰菊觉得自己飘上了云朵——一朵用棉花做暖的白云。
林旺太去世后,王兰菊还会想起两个人在棉花上飞跃的情景,她的心底会冷不丁地揪起来,身体绷得很紧,细密的汗珠滚滚而下,心里荡漾起三月的春潮。有时王兰菊会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将近五十岁了还对男女之间的缠绵难以忘怀。但这事儿又由不得自己,它突然而来,毫无征兆,是埋在心底的一粒种子。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林小琼工作之后,王兰菊随着她搬进了城市。对于城市,王兰菊并不陌生。林旺太活着的时候,曾带她到济南、北京等地旅游过。那时林旺太在镇上的供销社任职,分管采购,有时出去十天半月,风尘仆仆行程匆忙。王兰菊便说,你应该带我出去一趟,跟着你这些年,我连城市是啥样子都没见过。林旺太满口答应,两个人准备好简单的换洗衣物。买了车票出了村子。白天林旺太出去采购、洽谈,把王兰菊留在宾馆里,任她到街上或者商店里闲逛。晚上两个人吃点简单的饭菜,便在宾馆里翻云覆雨,享受人生之乐。男女之事,因地方不同感觉也不一样,王兰菊起初有些不好意思,但随着林旺太的逐步深入,也就放开了手脚,刺激得大呼小叫。采购完毕,林旺太领着王兰菊去了一些著名景点,还坐着公交车在城市里转了一圈。
王兰菊随着女儿来到的这座城市。显然没有济南和北京大,也没有太多的繁华。但城市总归城市,城市里没有土地,没有矮小的土屋,到处是宽敞的公路和耸立的高楼。她住在女儿分配的单位宿舍里,做饭、洗衣,或者到广场上看老太太们跳舞聊天。一旦融入到这些人群之中,王兰菊才觉得孤立起来,她放不开。有时和别人聊天,聊着聊着,她的话题就往老家跑,往梨园里跑,往田野里跑,往做暖上跑。她说,这里的暖被没有老家的暖被舒服,硌楞楞的。裹在身上四处冒风。家里的暖是棉花做的,又细又密、又软又绵,暖和着呢!王兰菊不愿往人群里扎堆。老太太们在音乐中扭捏着肥大的屁股蛋子,晃荡着吊下来的乳房,半闭着眼,浑身松弛下来,像一只只衰老的大马猴。她没这个胆量,都多大岁数了。丢不起这人。但事实却又不是如此,王兰菊的格格不入使她成了广场上的另类,她喜欢穿粗布衣服、厚底布鞋,有风时还扎一条浅黄色的围巾。人们对她议论纷纷指手画脚。有一位老太太顶着一团爆炸式的头发,抹着血红色的嘴唇,打着哈哈说,王兰菊,你原生态啊!
王兰菊不知道原生态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她气呼呼地回到家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呜呜哭了一阵。要不是老家的房子拆了,土地被卖了盖了工厂,老娘才不会到城市来生活。这个地方的空气不新鲜,人们不热情。别看道路两边是碧油油的梧桐、冬青或是叫不上名来的草木,叶子上都挂着一层油腻腻的灰尘。别看都在广场上摇头晃脑扭屁股,背过身来就像谁都不认识一样,连话都懒得说上几句。
林小琼的家住在五楼,视野倒算开阔,站在阳台上,整个家属院尽收眼底。没事时。王兰菊爱在阳台上出神,且一坐就是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只有林小琼下班回来,娘俩才会说上会儿话。林小琼不同意她老在家呆着,时间久了必会产生孤僻自闭。王兰菊点头同意,但白天女儿上班后依然我行我素。
王兰菊和邹大成认识其实蛮有意思的。那天,王兰菊从市场买菜回来,掏出钥匙刚要开门。楼道里跑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一身洗得花白的旧军装,脚上蹬着一双有些旧的胶鞋,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包袱,像是收破烂儿的。男子放下包袱,咚的一声响。他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请问这是不是职苑小区东楼道五楼?王兰菊一脸疑惑,见来人还算实诚,便说,这是东楼道五楼,你找谁?
中年男子嘿嘿笑道,我来寻邹可奇。他是我儿子。儿媳生了娃在娘家坐月子,这就快回来了,我是来伺候孙子的。我来之后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只好上上下下跑了好几趟。还以为走错门了呢。
王兰菊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家里当然没人。要不这样,你先到我家来等一会儿,应该快回来了。邹大成有些不好意思,接着搓手跺脚。给你添麻烦了,我从农村来,城里的规矩还不懂呢。王兰菊就笑,农村来的咋啦?我也是从农村来的。在这里陪着闺女住了都快两年了。
进了门,王兰菊给邹大成泡了一杯茶,两个人便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王兰菊问,伺候孙子该是女人干的活,你个大老爷们笨手笨脚的咋能成?
哎,说来话长。邹大成叹了口气,老伴去世啦,老家的几亩地也被收回去划成了开发区。儿子和媳妇都上班,伺候孙子的活只能我来。大妹子,你也从农村来,咋会住在闺女家?王兰菊说。咱俩一个命,孩子她爹死了五年,家里房子没了地也没了,只好来这里陪着闺女。
说实话,王兰菊并不喜欢邹大成。那天傍晚,邹大成竟然穿了他儿子替下来的运动服来到广场上。那身灰中透黄的衣服穿在身上像套了一层兔子皮,有些突兀,大有鹤立鸡群之势。邹大成顶着一团有些灰白的头发,跟在老头老太太屁股后边,模仿着他们的样子,跳着动作简单却也浑身打颤的广场舞。邹大成的动作太不协调了,往往抬起左胳膊,右胳膊也不自然地翘起来,右腿刚刚迈出去左腿不由自由地往前弓,不伦不类,像一只横行霸道的大螃蟹。邹大成跳得热火朝天,跳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神态自然。邹大成看见王兰菊,哈哈一笑,跑过来打招呼。来来来,咱俩跳一曲。我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惯了,跳起舞来不习惯,正好你好好教教我。
不等王兰菊回答,一双肉乎乎的大手便把她揽了过来。邹大成的力道有些大,把王兰菊弄得有些痛,但双手的厚度一下子把王兰菊的小手给包裹了,温热传递过来。打消了王兰菊拒绝他的念头。
王兰菊的动作比邹大成的还要笨拙,左晃右晃。除了两只乳房上下左右不断地跳跃,身体其他部位都在那儿紧紧地绷着,像一截硬邦邦的高粱秆。邹大成笑着说,大妹子,你咋比我还笨呢?王兰菊有些嗔怒,气呼呼地说,我的脸皮比你薄!说着说着,她的一只脚极其准确地踩到了邹大成的脚面上。邹大成尖叫一声,大妹子,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心里放开就好了!
两个人把一段舞蹈跳了三圈,王兰菊才渐渐找到了感觉。她的身体协调力还是可以的,随着音乐起伏身体慢慢起舞,身体缓缓地松弛下来,脸上涌上了热气,有些红润。邹大成已经大汗淋漓了,周身冒着热气,他的脸上滴下豆大的汗珠,五官差点变形,要不是有夜色和五彩的灯光,他早变成了索命小鬼。
哎呀,不行了,跳个舞咋比侍弄庄稼还累呢?邹大成甩掉王兰菊,坐在广场一角的水泥板凳上呼哧呼哧喘气。王兰菊笑着说。什么叫自作自受?这就叫自作自受!
王兰菊慢慢喜欢上了跳舞。本来她是绕不开脸面的,但邹大成不一样,他对其他人的动作和表情无动于衷,音乐一响,直接拉着王兰菊往人群里钻,仿佛是一位虔诚的教会分子。他总说心里放开就好了。王兰菊听着他的话,放下脑袋里的包袱,果然跳得顺畅。广场上的人黑压压一片,各自跳着又仿佛各怀心事,动作有些不整齐。但他们都不会睁眼去瞧哪个人,或者,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别人的存在。这就是城里人,自以为了不起!王兰菊心中曾多次这样的讥讽。有些刻薄。别人无视她的存在。她也就无视了别人的存在。那个说她是原生态的胖老太太见这些天王兰菊跳舞跳得起劲,心里疑惑不已,她哈哈笑着说,王兰菊,你精神焕发啊!
王兰菊冷冷地回了她一句:这叫精神焕发?这叫青春不减当年!
邹大成的儿媳妇休完产假带着孙子回来了。邹大成每天的任务是照顾孙子。喂奶洗衣侍弄尿布。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尽管忙,但儿子儿媳下了班回家。他又会跑到广场上来,张牙舞爪跳个不停。王兰菊笑他,你这个人的精神头怎么这么大?天天如此,你也不腻得慌。邹大成擦擦额头上的汗,边甩着胳膊边说。在家孙子吵得厉害,出来算是透气。住在城里真他娘憋得慌!邹大成虽然跳舞不好,人缘却行。他属于自来熟,见了谁都能说几句话套个近乎。有一天王兰菊不舒服。坐在一旁休息,一眨眼工夫,邹大成竟然和那个胖老太太跳在了一起,边跳边说,惹得老太太一惊一乍笑个不停。从老太太的面色上看,邹大成一定用非常顺耳的语言夸奖了她。比如精神焕发、风采奕奕;比如虽然胖,但应以胖为美,这身材,杨贵妃转世啊!
胖老太太屁颠颠地笑着走了,邹大成回来邀请王兰菊。王兰菊推开他说,找你的杨贵妃去!邹大成咧着嘴笑,看看,吃醋了不是?
吃醋?王兰菊气得转身走了。
有一天吃了午饭,王兰菊想在家里打个盹,没等躺下,邹大成跑过来敲门。邹大成扒着门缝说。妹子,你会做暖么?我带来的几床小褥子都被孙子尿湿了,这不,前几天我让人捎来几斤弹好的棉花,好给孙子做几床小褥子,可我手笨,总弄不好。
王兰菊看见邹大成手里的针、针上的线。看见他手里的被面和露出来的棉花,觉得眼前一花浑身一震。做暖,做暖,自己做了半辈子暖,区区一个包裹孩子的褥子还不会做?王兰菊关了门进了邹大成家。家中一片狼藉,凡是能晾东西的地方。全部挂着花花绿绿的小孩尿布及小衣服、小被褥,整间屋子里飘散着一股酸酸的尿臊味。小孙子睡得正香,粉嘟嘟的脸蛋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王兰菊皱了皱眉说,邹大成,我还以为你真会看孩子呢!说着,她先不去做暖,而是慢慢地给孩子松了松身上的小被子,然后麻利地收拾起屋子来。王兰菊的动作麻利而又熟悉,仿佛对这里很了解。她有点恨恨地说。邹大成,你把家里弄成了狗窝!
邹大成有点尴尬地笑着,他跟在王兰菊身后说。就这。比起老家强多了,强多了……
王兰菊做的暖很仔细,闪闪的钢针在手中活了起来,手里的布面柔软得如同一条润滑的鲇鱼,她把钢针插在发丝里。就像一朵静静开放的棉花,细密的针脚像马路上的斑马线,整齐而又错落有致。邹大成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直线,有些陶醉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王兰菊细微的动作。王兰菊呼吸均匀,胸脯随着呼吸上下起伏,她的脸颊滑润洁白,像一截莲藕顺着脖子没在衣领之中。他猛地坐得笔直,喘息有些粗重。
王兰菊看了邹大成一眼,看了看他紧绷的身体,脸面突然有些发热,她想,她的脸一定红了。
这时候邹大成的小孙子哇的一声醒了,手脚并用,在婴儿车里哭个不停。王兰菊放下手中的暖,把小孙子抱起来。小孙子在王兰菊身上蹭着,一个劲地往她的怀里拱。王兰菊有些不好意思,背过身来说,你个小兔崽子,你瞎拱什么,拱也是白拱。孩子哭个不停,王兰菊只好解开扣子。掏出一只乳房塞进孩子的嘴里。王兰菊笑着说。吃吧吃吧,看你能吃到啥!
邹大成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下,目光如炬火焰汹涌。在那儿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王兰菊扭过头来说:邹大成你看啥?真没出息!说着说着,王兰菊笑了。她摸着孩子热乎乎的脸蛋说,你个小色鬼。乱吃奶乱认亲!
邹大成搓着手说。吃了晚饭去跳舞吧。
王兰菊说,你不是有个胖老太太吗,找她陪你!
邹大成说,她老踩我脚,还是你吧。
林小琼回家时把刚谈的男朋友也带回了家。王兰菊仔细打量了一番,除了他把头发烫得焦黄和一只耳朵上挂了一串明晃晃的耳环之外,其他的都还可以。王兰菊说,你们在家里聊,我到广场上去。林小琼笑着说,听说隔壁的邹伯伯喜欢请您跳舞,我看他精气神十足,你可要小心哦!王兰菊有些不好意思,飞快地出门。林小琼在后边说,妈,邹伯伯很好的!说着,还飞了一个鬼脸。
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解决,倒关心起老娘来了!王兰菊心里想。林旺太去世之后,有人跟王兰菊说过媒,但她一口拒绝了。林小琼刚刚工作还没结婚,老娘却先嫁了人。说出去不好听。虽然林小琼支持自己找个老伴,但不管怎么说,王兰菊心里装着的、藏着的,还是林旺太。林旺太尸骨未寒啊!
想到这,王兰菊觉得心头一颤鼻子一酸,眼泪便在眼窝里打着转转。王兰菊只跳了一圈舞蹈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林小琼是她的心事,等哪天把她嫁出去才算了却一桩心愿。可林小琼嫁出去之后,自己会不会觉得空虚?一个人呆在偌大的房间里,连个伴儿都没有,不把人闷死才怪。
邹大成拍了拍王兰菊的肩膀说,你气色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没事,就是有点累……
那就休息休息。邹大成把王兰菊扶到广场一角。他的手指粗短,手背很厚,红润似血,温暖如炭。这股热流透过衣服,传到身上,王兰菊竟觉得周身如电激荡身心。
王兰菊有些脸红,她推开邹大成,整了整衣角道,我先回家休息,你继续在这几跳吧。不等邹大成回答,她已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快步走了。王兰菊心里直骂自己,自己都觉得脸红,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她刚才突然想到了暖,想到林旺太把自己掀翻在棉花堆里的情景。
林小琼和男朋友出去了。这俩孩子,准是出去练摊了。林小琼每次谈男朋友,总喜欢黏住人家请客吃饭,好像家里的饭菜不可口似的。王兰菊叹了口气,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家里有些凌乱,她慢慢起身收拾。林小琼的房间里贴满了一些男明星的画片。琳琅满目,他们的眼神萎靡却又故作阳光,每一个都很猥琐。王兰菊闻到一股淡淡的柠檬味道。氤氲了整个房间。林小琼的暖撒乱在床上,上面有一团湿气,像一朵盛开娇艳的水牡丹。王兰菊心头一热,突然想到了自己临出门时林小琼狡黠的微笑。她胡乱地收拾着,更像胡乱地寻找。被子暖暖的,似乎还有温存之感,冒着女儿柔顺的体温。王兰菊喜欢抚摸被子,喜欢被暖覆盖。在林小琼床头的垃圾桶里,她找到了一片湿巾和那个散发着淡淡柠檬气息的避孕套。
王兰菊觉得,自己被一汪溪流淹没了,淹没了。
这暖真好!邹大成夸奖人的时候,表情夸张,显得有些作假。他摸着王兰菊给小孙子做好的暖,嘿嘿傻笑。
想当年在老家做暖,我的针线活数一数二。王兰菊说,有一年胡同里的老姐姐比赛,我一天做了三床大暖呢!
小孙子嘎嘎笑着,拍着手,蹬着腿,似乎听懂了王兰菊和邹大成的对话。邹大成抱起小孙子,用自己的胡子擦着孩子粉嘟嘟的脸蛋,孩子仿佛扎疼了。哇的哭了。
王兰菊接过来哄着,一边哄一边埋怨,你干嘛,胡子拉茬,刺痛孩子了!邹大成也没想到孩子会哭,站在那儿手足无措。王兰菊抱着孩子满屋子跑,孩子哭了一路。王兰菊说,这孩子,精得很,忒难哄了!
王兰菊解开衣领,但孩子依然大哭。王兰菊的乳房还算圆润,白中透着浅浅的红色,它在跳跃着,好像一弯明月,闪耀着一股淡雅的清香,孩子用手拍打着它,有些不情愿地含了一口,然后摇着头挣脱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邹大成跑过来说,好啦好啦小祖宗。你咋哭起来没完?你看看,多好的奶啊,你咋不馋呢?你要不吃,爷爷我可要吃啦!说着,邹大成有些颤抖的手在王兰菊的乳房上摸了一下。一团雪白的棉花跳跃着,富有弹性,闪烁的光亮弥漫了整间屋子。
小孙子突然笑了。
王兰菊有些吃惊,她放下小孙子,盯着邹大成的眼睛,如同一把刀子,闪闪发光。
邹大成,你若真的想对我好,那就等着,等我把女儿嫁出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家里住不下,咱就住到楼下储藏室里。那里宽敞着呢,也不用爬楼。王兰菊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们经不起折腾。
邹大成搓着手,有些尴尬,他吞吞吐吐地说,好,好,好……
王兰菊扑哧笑道,看你胆子挺大的,喜欢动手动脚的,咋到了嘴上功夫就不行了呢!
邹大成说,我是老实人,这些事儿还是儿子教的。奶奶的,这小子净让我干这种羞人的事!
哎,现在的孩子都疯啦!王兰菊叹口气道。
林小琼终于要结婚了,这个消息让王兰菊等了好几年,她决定给林小琼做一床宽大的暖。林小琼说男朋友会给她买宽大的床,买柔软似水的蚕丝被,她不需要暖。王兰菊有些赌气地说,不就是一床暖吗,你不要我要!林小琼咯咯笑了,她伸开双臂搂着王兰菊说,妈呀,要不女儿的这床暖送给你吧,算是给您的嫁妆。王兰菊的脸有些发烧,急忙说,你瞎说啥,老娘可没工夫和你闲闹!林小琼一本正经地说,别的我不敢说,论起谈恋爱的经验,我比您强。邹伯伯挺实在的,我看行。王兰菊低下头,拍着林小琼的手,像是责备,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个丫头片子,懂啥?
林小琼喜欢把男朋友带回家,她的房间成了两个人欢乐的天堂。王兰菊在客厅里闲坐或者打扫卫生的时候,能够听到他们的动静,起初是微澜的湖水,紧接着便是奔腾的浪花,再后来则变成汹涌的波涛,林小琼笑着。叫着,慢慢地变成了呻吟。
王兰菊手脚忙乱,她觉得林小琼变成了一只猫,而她,也正在蜕变。仿佛也要变成一只猫。这俩孩子,毫无忌惮!王兰菊心里说道。她想起年轻时,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她想起了小羊倌,想起了林旺太,甚至想起了邹大成。年轻时,王兰菊也是一朵花,一汪水,一团白云。
王兰菊做暖的时候。邹大成会抱着小孙子过来,他喜欢凑热闹,喜欢看王兰菊滑下来的刘海。阳光透过窗子照下来,一缕阳光映在她的额头。整个人显得安详极了。雪白的棉花闪着轻柔的光泽,温润如水,似婴孩暖洋洋的肌肤。做暖的时候,手里的钢针有了生命,它在一团白云里起伏。像一条鱼浮在水面,跳跃着优美的弧线。
邹大成放下睡熟的孙子,有点蹑手蹑脚地跑到王兰菊身后。看着那条鱼,看着那团云,看着阳光里的王兰菊,他从身后搂住了她。
王兰菊的心忽地跳跃,一下子燃起了明晃晃的火苗。她觉得自己在颤抖,身上涌上的一股热潮迅速将她淹没。手里的钢针跳得更快了,仿佛长了翅膀在飞翔。银光闪闪,银线穿梭,手里的暖在两个人身下无限的延伸,弥漫了整间屋子。
哎呀!王兰菊惊叫一声,一滴鲜血在左手的食指上涌了上来,像一粒晶莹透彻的红色珍珠。钢针极其稳准地扎在上面,毫无征兆,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邹大成捧起王兰菊的手指,猛地放到嘴里。他缓缓地吸着,用力地吸着,温存地吸着,野蛮地吸着。王兰菊笑了,笑成了一朵秋天田野里开得旺盛的棉花,她说,邹大成,你是不是想把我的血给吸干啊!
邹大成吐出手指。将她捂在胸口。他的嘴顺着胳膊向上。慢慢地触到了暖暖的脸颊。王兰菊感觉到,一股烟酒的味道塞满了整个心胸,它们化作一条蛇在胸口横冲直撞。这正是男人的味道。
邹大成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但王兰菊听得明白,她把他的头揽在怀里,感觉到了他的炙热。王兰菊想到了林小琼,想起了她美丽的脸蛋和狡黠的微笑。
这床暖还是自己留着吧!王兰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是一床暖,她把自己深深地埋到里面。
邹大成把王兰菊放在暖上的时候,那床暖还没有做完,但还是接纳了他们。暖是一朵盛开的花朵,他们便是两只采花的蜜蜂。
但是,王兰菊突然把邹大成推开了。她飞快地整了整凌乱的头发。扣上了胸前已经解开三颗的扣子,她拿起钢针,在阳光下冲着邹大成闪了闪,一抹光亮耀得两个人眯起了眼睛。
熟睡中的小孙子醒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