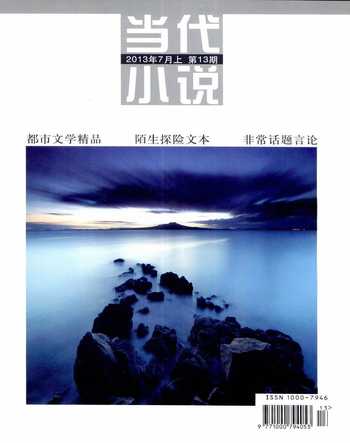绝刀
周才彬
1
根叔勾着头,想了半天,还是没想起自己是七十四了,还是七十五了。他绿着脸,去问启德。启德的脸比他还绿。启德说:你要是去年七十四,今年咋说也是七十五噻。根叔就哑了,叹口气,在心里说:真是个二傻。
根叔是不太在意自己几十几的。人活几十几都得两腿一蹬到那边去,记不记得都清淡寡淡。但根叔到底还是想起来了,还忍不住问了,是因为有人才问过他:根叔哎,你硬是行哦,你都多大年纪啦?
问话的人是启发,根叔的远房侄子。
启发这么问,是因为根叔给他家劁猪,劁得好一个艰难。还没尺把长的猪娃,细腿一蹬,不是差点儿爬起跑了,就是差点儿把根叔掀个四仰八叉。根叔眼神也不是一般地差,一刀子下去,不是偏了,就是歪了,活活把猪娃折腾得只差断气儿。只差妈妈娘娘地骂人。
根叔不傻,别看启发把话说得轻烟儿似的,可他还是听出来了:根叔,你哪是劁猪,分明就是杀猪!你老了,实在是老了。
老了?我老了?我有多老了?根叔就想自己究竟几十几了,头一回很当事地想。
根叔弄不清自己几十几不要紧,却弄得清自己还能干个啥,不能干些啥。封刀,是得封刀。根叔对自己说,还大着嗓子说出了口。
根叔拿出刀囊——一个他揣了半辈子,揣得就像面团子一样软和的牛皮袋子。袋子里装着他东跑西跑劁猪的刀子。还有一只号,牛角做的。他也揣了半辈子,吹了半辈子,上面的纹路金黄油亮的。
捧了两样东西。根叔在屋子里左一瞅,右一瞧。他在找一个地方,一个适合摆两样东西的地方。把两样东西摆好了,他就要恭恭敬敬地行封刀大礼,从今往后再不劁猪。
根叔很失望,他没找到那样的地方。按规矩,迎门的那面墙根儿上是要摆一个柜子的。还得是四楞方正的,漆成纯黑的。因为那是神柜,是用来给老辈子们奠酒,给神仙爷们上香的。现在要封刀,行大礼,给附了神仙灵气儿的刀囊和号烧香磕头,给保佑自己的天老爷烧香磕头,没个神柜,说啥都不成,说啥也不能干。但根叔在墙那里没瞧见神柜,瞧见的是一面大电视。
根叔心里不爽,对电视犯起嘀咕,对小儿子启华犯起嘀咕。电视是启华买的,放这儿放那儿他都死活不干。硬说那里才是正位。
这下好了!电视是有了正位,可神柜呢?老辈子们呢?神仙爷们呢?根叔忽地觉得启华太“王仗”了,简直就是“王仗巴嗤”。
“王仗”,就是霸道。可是启华再霸道,根叔也觉得拿他没法儿。谁叫他在外面干事,还是在大世面里干事,谁叫这又高又宽的大电视是他买的,就连这又高又大的房子也是他盖的。
说起房子,根叔更觉得该他启华王仗。他根本没想到启华会跑回来盖房子,更没想到启华把房子盖得这么戳人眼睛。他听近跟前有文化的人说,这叫别墅。启华自己也一脸神气地说,当然是别墅,乡村别墅。
根叔起先不知道是别墅,以为是“白薯”。根叔却一开始就知道启华可是花了钱,还不是三两个小钱。根叔是记得的。十年都没回过家的启华,冷不丁回来了。一见面啥都没顾得说,直接就是:爹,咱们把老房子一家伙掀了,整它一栋新的起来。根叔想说,盖个新的使得,可钱呢?钱还在瓢底上。没想启华忽地就把一个大袋子拖了过来,忽地一下撕开,一捆一捆的票子滚了满满一地。根叔还没回过神来,就见老房子轰的一声,叫挖机一爪子抓趴,变成一堆七七八八的破烂儿。又没等根叔回过神来。那房子忽地就起来了,比那个啥啥的还起得猛。
更让根叔回不过神的是,启华想把房子摆置成啥样就摆置成啥样。柱子不用它来支房梁。硬是耸在了大门口。顶上还弄出几个精光赤溜的石头人儿;堂屋也不叫堂屋,叫成了大厅。好好的地面硬是把一半垫出几尺高,边上砌成一溜坎子;茅厕也进到了屋里头,拉屎的地方不叫茅坑,叫啥啥“器”,让人蹲着拉惯了陡然改成坐着拉,死活使不上劲。
2
王仗就等他王仗,哪个叫他启华有那个能耐。根叔把心里的不爽,一点一点咽了回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不找了。这封刀大礼先搁一搁算了,先搁一搁再说。
根叔把刀囊和号放回原处——他的枕头底下。刚要从屋里出来,忽地听到大厅里咋呼起来。起先是一个女的,炒米花一样:你个二货,还想捡我便宜?你就再投几次胎吧!你就是再投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照样没门儿,没门儿!接着是启德的声音,瓮声瓮气的:启华说了。启华说你要是再来,就让我把你睡了,嘿嘿,把你睡了。
根叔脑皮子一爹,赶紧朝外跑,踉踉跄跄的。畜一一畜生,再敢胡来。看我不把你的爪子一刀剁了。根叔匀匀气。转头对女人说:小朱,你又来了?启——启华不是跟你说好了,不——不让你来了?女人横着眉,冷着脸,说:只说好他一半,我这一半永远说不好,永远,知道不?狠狠甩一下头,又说:管好你这个傻儿子。不然我就报警,报警!又一甩头,咚咚地上了大厅的坎子,咚咚地上了大厅一边的楼梯。她这硬是赖上启华了,嘻嘻!启德笑得更二更傻了。
根叔拣把椅子坐了,望着空空的楼梯,心里也说:她这真是赖上启华了。又说:启华呀启华,你不光王仗,你还老爱扯巴。
根叔说的扯巴,就是自打别墅,这“乡村别墅”盖起后,启华就一次一次往回带女人,一个比一个好看。根叔问过启华,启华是这样塞他的:爹,你老都老了,管这些事干啥?你儿子又没强迫人家。还说:现在都这样儿,除非你儿子还跟原来一样,穷得舔灰,穷得裤衩都没得穿。根叔拿眼看启华,没想启华竟恼了,粗着气说:你原来的儿媳不就是嫌你儿子穷,才把人偷得黑天黑地的,你儿子才把教得好好的书辞了,去到外面没头没脑地闯,一直闯到今天。根叔连眼也不敢抬了,小心了又小心地说:爹还不是怕你弄出个事来。
果然就出了事,启华又带着一个女人嘿呀嘿呀回来时,上回的那个女人就不声不吭地撵过来了。这个女人就是小朱。小朱一来,就把人吓坏了。她不光把启华抓得满脸开花,还举着一把火,说要把整个楼化成一堆灰。她指着启华的鼻子尖,牙咬得咯咯响,说:汪启华,你这哪儿是乡村别墅,简直就是魔窟,就是地狱!还有你自己。整个就是恶棍!但你休想把我甩了,休想!你就是一泡狗屎,我也吃定了,这辈子都吃定了!启华昂着头。是这样说的:你薅住我这个恶棍,薅得死死的,你在想啥呢?你在图啥呢?难道我不清楚?难道我给你的还少?你咋就是一个填不满的天坑?启华让小朱开价,随便开。小朱也昂了头,说:所有!一切!统统!你给吗?给吗?
启华不给。启华赶紧走人。启华一走,就再不回来。
启华不回来,小朱却来,三番五次的。
3
饭扑哧扑哧煮好了。根叔叫启德,让他喊小朱下楼吃饭。启德一撇嘴,说:爹,咋小朱一来你就急着煮饭,你是不是怕把小朱饿着了?根叔黑了脸,说:再乱说,看我不把你的舌头揪下来。启德把舌头一下伸出来,咕哝:你揪噻,你揪噻。收了舌头,嘻嘻地要去喊小朱,根叔却一把拦住了。根叔说:还是我自己去。启德把嘻嘻变成了嘿嘿,说:爹,你是不是也想把她睡了?根叔把巴掌扬了起来,启德把脸伸过去,嘿嘿得更起劲,说:爹,我妈死几十年了。你扯直都不想女人?扯直没和女人睡过?根叔的巴掌无力地垂了下来,剜一眼启德,躬着腰上楼去了。
小朱,赶快起来哦,饭怕是要冷了。根叔把头插在门缝里喊。根叔没看见小朱,看到的是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影子。根叔整个人从门缝里钻了进去。小朱,小朱,你听见没?影子还是不出声,还是一动也不动。根叔抬起手,慢慢伸过去,快挨上影子最鼓起的地方时,忽地烙着似的缩了回来。
小朱,我不睡你了,你起来吃饭噻。启德不知啥时候跑进来了。影子动了,动得大有声势,床都一颤一颤的。你们这是要干啥?干啥?我真的报警了,报警了!她的手在床上捶着。根叔的脸又一下绿了,赶紧说:是来喊你吃饭的,喊你吃饭的。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小朱把床捶得更起劲。
嘿嘿,不出去,启华真的说了,说你再来了,就叫我把你睡了。启德往前躜着,头伸得鸭子找食似的。小朱抓起了手机,看起来真要报警了。根叔急了,推着启德就往外走。启德挣着,还在说:不信你打电话问启华,问启华噻。
爹,你也不相信哦,启华真的说过噻。到了门外,启德嘀咕着,一脸委屈。根叔瞧瞧他,说:启华啥时说的?我咋不晓得?启德说:有时间了噻,启华打电话说的,他说他换手机号了,叫我们不要对小朱说噻,我就说你跑得远远的,人家就朝我们家里跑噻,启华就叫我赶,我说她不怕我噻,启华就叫我想办法让她怕,我说我想不到办法,又不能打人家噻,启华就说你睡她噻,硬睡,你看她怕不怕——就是这样噻。根叔的脸绿得就不是脸了。
爹,你说启华不要的女人。我能不能要啊?根叔不说话。根叔的身子一下一下地晃,像是突然在发晕。启德又嘿嘿笑起来,说:爹,我说个事你听,你莫打我,也莫吵噻。根叔止住晃,说:启德呀启德,你还能有啥事?启德说:你天天叫我放羊,天天叫我放羊,你晓得我最不喜欢哪种羊哦?根叔懒得接话,启德就自己说:最不喜欢骚虎子噻。
“骚虎子”就是公羊。根叔接话了,逼着启德问:那些掉到崖下去的,还有发急症的,都是你整死的?成心整死的?启德说:嘿嘿,是的噻。根叔说:为啥呢,为啥你要整死它们?它们犯着你哪儿了?启德说:嘿嘿,它们动不动都朝母羊身上骑,把个红赤赤的东西伸多长,又喷鼻子,又噘嘴皮子,我见不得噻。一见就受不了噻,就恨死骚虎子噻。
根叔好长时间没说话。后来说了:启德,你几十几了?启德说:咋说也有四十几噻。根叔说:启德,再过两个月你就整满四十七。启德说:过了四十七,咋说也是四十八噻。
4
小朱服毒了。根叔见她把一把丸子塞进嘴里。根叔吓坏了,火上房子似的叫启德:快把启发找来,快把启发找来!
启发平时管水管电,遇上哪家娶亲老人,还大呼小叫地给人家理事。
不大工夫,启德就带着启发一路飞脚地来了。咋个样了?咋个样了?启发老远就开始咋呼。根叔紧跑几步,说:不晓得,不晓得咋个样了。人呢?人呢?启发还在咋呼。在楼上呢,门都闩死了,闩死了。根叔说。
门是闩死了,启发用手推不开,就用肩膀顶,还是不开。启发咚咚跑下了楼,一会儿就把一根又粗又重的木头扛上来。三个人一起抬了木头,嗨地向门撞去。咣地一声响过,三个人连同木头一齐倒在了里屋。
一骨碌爬起后,启发赶紧去掀被子。他看到一张脸,卡白卡白的,没一丁点动静。启发赶紧把手伸到鼻子底下,来回试,没觉出一丝儿气进出。启发掏出手机就拨,就喊:这里是汪家沟,赶快赶快派救护车来,有人服毒啦!启发还想说具体些,没想手机叭地掉在了地上。启发赶紧去抢,忽地觉出是被人打落的,一抬眼,却看见小朱早站在了面前。
哪个叫你打120了,哪个叫你打120了?小朱的脸有动静了,鼻子眉头都拧到一起了。你不是服毒了吗?启发的鼻子眉毛也拧到一起,一个字一字地数着说。哪个咒我啊?哪个说我服毒啊?小朱把一个药瓶儿举到启发眼皮子底下。是安定,安定!我想安安静静睡会儿觉,不成吗?不成吗?说着,两腿一跷,又上了床,变成一个影子。
三个人怏怏地退了出来。启发摇摇头,说:叔呃,你听见了吧?人家只是想睡个好觉。你硬是把人家多好的一个梦搅黄了。根叔脸绿了一阵,又红了一阵,说:那她咋把药吃得一把一把的?眼泪哗哗的?启发又摇头,说:叔呃,你硬是老了哦,脑筋转不过弯了,人家那是苦肉计哦。根叔咧咧嘴,说:你是说她在吓我们?启发说:是噻。转转眼,又说:叔呃,你可要当心哦。根叔赶紧说:咋个当心呢?启发,你快说。启发把嘴抵着了根叔的耳朵,声音却大得出奇:当心人家使你美人计。根叔一下跳了起来,脸红到脖根儿,声音一抖一抖地说:你个死启发,只会拿你叔开心,只会拿你叔开心。
启发收了坏笑,想一想,说:叔,你是得小心哦,安定吃多了,也会死人的,睡着睡着就过去了。根叔说:那咋个办呢,咋个办呢?启发又想想,说:启华不能再这么躲了,得叫他回来。根叔说:他咋肯回来,他把手机号都换了。那也得叫他回来,真要是出了人命,叔,你咋收得了场,收得了场哦?启发说。他咋会听我的,他王仗着呢。根叔说。再王仗,他自己拉的屎,总不能叫别人给他擦屁股,别人也擦不了。启发说。这下,轮到根叔想了。根叔想一想,说:启发,还是你跟启华说,你能说清水儿,你叔咋也说不清。启发又摇起了头,还撇起了嘴。摇罢,撇罢,还是掏出了手机。
启发一遍一遍地拨,一遍一遍地拨,就是不通。占线,一直占线。启发说:汪总在用电话煲粥呢。根叔不晓得啥叫煲粥,说:启华硬是王仗呢。你当哥的电话他都不接了,是想一辈子都不回了?启发就对他说:是启华在和别人说话呢。等会儿再打,等会儿就打得通了。
等了好一会儿,也还是打不通。倒是把呜哇呜哇的救护车等来了,把一群火烧屁股的白褂子白帽子等来了,把一副扯得直直的担架等来了。启发惶了,说:我日,咋就找到了,咋就来得日快日快。
根叔也惶了,直往后退。启德看不出惶,却也往后退。启发就被顶在了前面,炮灰似的。启发就主动当炮灰了。启发说:误会,误会。启发说:让你们放空了,抱歉,抱歉!启发说:不是捣乱,不是捣乱,是有人真喝药了,是真有人喝药了,啊不不。是失眠了,催瞌睡的。
5
只隔一天,启华回来了。
启华苦着脸,不像是回到家,像是上到沙场。启华说:哪个叫你们管了?你们这不是多管闲事?根叔说:她喝药,一大把一大把的,咋能看着不管?你们就只消看着,看着她喝,喝多少是多少,她要睡就等她睡,睡过去了也不消给我打电话。直接打110。启华的脸一抽一抽的。根叔不晓得110。根叔说:那不晚了,没得救了,好好的一个人咋能看着她那样?启华竟笑了。启华说:晚什么晚,一点也不晚,等警察一到,拍个照,填个单,再拉到医院动个刀,啥事都干净了,都太平清静了。
启华把启德叫过来。启华说:哥,你真是个二傻,我叫你赶她走,你咋就不赶呢?你长张嘴,长双手,咋不晓得使?启德耷着眼,噘着嘴,说:我咋没赶?来一回赶一回,来一回赶一回,人家就是不走嘛,自己走了,过不了几天还是来嘛。我不是让你吓她吗?吓她你都不会?启华做出挥拳头的样子。启德说:我不敢打人嘛,也没打过人嘛。启华懒理启德了。启德却偏和他说,是这样说的:你盖个这么大的屋子,就我和爹两个人。有个女人咋不行噻?每次小朱一来,爹把饭都煮得勤些。还对我有说有笑,我放羊呢,我放羊就不怕骚虎子喷鼻子了。噘嘴皮子了噻。
丢下启德,启华就上楼了。上得有气无力的。两只脚半天挪一下,半天挪一下。
挪到床跟前,启华就一把扯了被子。玩自杀游戏是吧?装死卖活吓唬人是吧?启华咬着牙说。我不玩游戏了,我真他妈自杀,自杀!小朱躺着没动,小朱这样说。你自杀呀,自杀呀,我就在这儿看着,眼睛都不眨一下。眨一下就是畜生!启华的脸抽得厉害。汪启华,你他妈说对了,你就是畜生,猪狗不如的畜生!小朱忽地跳起来。扑向启华。
小朱的手掐住了启华的脖子,膝盖头顶住了启华的肚子,一下一下地撞。启华不干了,一扭身子,一甩肩膀,小朱就飞了出去,咚地又落回到床上。床使劲颠了一下,又颠了一下。你还真想赖上我不是?你还真想拿我爹和哥当人质不是?你真是太有理想了,太有雄心壮志了!启华笑了,一咯一咯的。我就赖上你了,你不是躲吗?东跑西跑地躲吗?你咋就屁颠屁颠地回来了?你就莫回来噻!小朱也笑了,也一咯一咯的。启华说:你咋就这么不给自己脸呢?三番五次朝这里跑。是不是这屋里住两个单条条的大男人?小朱忽地把一个东西扔过去,启华闪得快,掉在地上看清是一个花枕头。启华用脚把枕头一踏,说:还想在上面寻找久违的气味不是?不是久违,是早飘走了,飘得一星星儿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霉味,一股一股的霉味。又一咯一咯地笑。小朱呸了一口。说:汪启华,你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居然唆使你傻子哥,对我动手动脚,对我不轨。还有你爹。看起来人跟个饿死鬼似的。一看也不是个好东西。启华咧一咧嘴。说:我哥他真是个傻子,一次一次送上门的肥肉,硬是一次也不吃,他是不是也晓得这肉又腥又膻。你让他来吃呀,来吃呀!小朱先是哈哈地笑,接着是哇哇地哭。
启华来回走了几步,换个脸色,说:朱小虹,你这样是没用的,我不可能一直和你在一起,你一开始就应该清楚。小朱原来叫朱小虹。朱小虹说:我不清楚,我只记得一开始你对我说的话,说永远和我在一起。启华一嗤鼻子,说:干着那事说的话,你也捡个棒槌当个针?我就要当真,就要当真!朱小虹又叫喊了。启华说:你再怎么叫,再怎么喊,统统没用,我就没打算这辈子再结婚,我要让那些放荡的女人该哭哭,该喊喊,该上吊上吊,该喝药喝药。朱小虹又想扔枕头,可怜手边没枕头了。朱小虹就舞手,说:你个畜生才放荡,仗你有几个臭钱,仗你有一个下流东西。启华又笑,腰都弯下去。他说:我要是没几个臭钱,没那个下流东西,你肯跟我到处跑,跑到这乡下来?朱小虹呜的一声哭,说:你真是个恶棍,流氓,你爹不是有刀吗?咋不给你一刀?启华又笑弯了腰。
直腰起来。启华又换个脸色,说:朱小虹,咱说正经的,你到底怎样才肯罢休?朱小虹说:你应该知道,你是知道的。启华说:还是那句话,你开个价,随便开。朱小虹说:我也还那句话,除非你所有的,统统的。启华说:那是做梦,我可以不清楚萝卜白菜是个啥价,却不能不清楚某个人的价钱。启华还想往下说,不想朱小虹又一下扑过来。启华记着呢,早防着呢,不仅没让朱小虹掐住脖子,撞着肚子,还把朱小虹的胳膊一下别到了背后,别得朱小虹妈呀妈呀地喊。
朱小虹,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滚,马上滚,滚得远远的!启华架着朱小虹往外推,就像小时候玩游戏——“架飞机”。朱小虹呢?朱小虹除了妈呀妈呀地喊。就是使劲往后拖。拖不住,就改了词儿:救命啊,救命!
这救命一喊,立马就有了效果。根叔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启德也跑过来了。根叔一脸的惊,连着声说:启华,你这是要干啥,要干啥呀?启德也说:启华,你这是要干啥嘛?小朱又没跟我睡,你莫打噻,莫打噻。
启华哪个的都不听,架着朱小虹直向前冲。很快就冲下楼,冲出门,冲到有树,有花,有草的大场子。根叔一溜小跑地撵了过来,启德一溜小跑地撵了过来。启德说:启华,小朱长得多白净啊,多嫩欢啊,多好看啊,你咋下得了手,咋下得了手噻。说着,就去掰启华的手。
这下坏了,朱小虹一下挣脱出来。挣脱出来的朱小虹,一把抱住了启华,又打又咬。结果是,启华更急,更恼,甩开巴掌就打,叭叭地全落在朱小虹身上,没一下落空。根叔也急了,也甩开了巴掌,每一下都落在空气上。启德更急,不甩巴掌,甩拳头,咚咚地每一下都擂在启华背上,也没一下落空。
启华就蒙了,就愣了。启华一蒙一愣。启德就把自己插到了两人中间,母鸡护雏似的护着朱小虹。一下子就没了动静,几个人都点穴似的。就一个字:静。
忽地,一个声音传了过:咩——咩——
咔!启德的穴先一步解开。跳起来大喊:骚虎子!骚虎子!根叔的穴跟着也解开了,摇晃着身子,看到一个人走了过来,一只羊走了过来,一点一点地走到他跟前。
堂弟哟,堂哥好几天都想找你呢。根叔不吭声,听着这个人说:你看这畜生,越来越大了吧?可骚劲也出来了,越来越大了,你根本就不敢把它放出门。一出门,死畜生就把耳朵竖得直直的,嘴皮子翘得高高的,闻到一丝丝气儿,就撒蹄子跑得不见影儿。这不,这回就跑出去好几天,害得你哥翻了几架山才找见。根叔还是不吭声,还是听着人家说:找见时,堂弟你猜咋个样?死畜生正腆着一副下流坏子相,围着人家母羊屁股转。你哥去牵它,你猜它又咋个样?死畜生不认你哥了,拿角死命地抵你哥。这不,你哥的腿还疼着,走路都显跛。根叔还只是听着:堂弟呃,你说你哥都这把年纪了,哪跟得上啊,哪管得了啊?不能再由着它了,非得把它劁了!
把它劁了,把它劁了!启德使劲咋呼起来。
根叔望望堂哥,望望堂哥手上的羊,半天不说话。羊却自顾地咩,一声高一声低的,还把耳朵竖起来了,扭前扭后的,嘴皮子也噘起来了。一伸一缩的。根叔慢慢扭过头,慢慢将目光落到启华脸上。停了停。用小得快听不见的声音说:启德,去把刀给我请来!
启德好像早就候着这句话,根叔音儿还没落定,就噌地蹿了出去,转眼就又蹿了回来。
根叔从启德手上拿过号,在手上掂一掂,慢慢插进嘴里,拼足力气扯出一串呜呜的声音。软软地撂了号,再从启德手上拿过刀囊。慢慢地打开。慢慢地抽出一支刀子,把刀囊也软软地撂了。捏着刀子,根叔忽地阖了眼,忽地又睁了眼,忽地大了声:把畜生请过来!
没等堂哥挪步,根叔一踪腿,几个大步跨了过去。只见他把刀子一横,叼在嘴上。一条腿猛地一跷。就把公羊夹在了胯下。接着便是猛一弯腰,公羊后腿根儿的那个东西——那个袋子样的东西,就稳稳地攥到了手里。一道白光闪过,那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眨眼就变成一张皮囊。
劁完喽,劁完喽!启德咋呼一声。蹿到根叔跟前,一弯腰从地上抓起两个东西——滚圆的,奇大的,粉嫩的,像两个诡怪的肉蛋,就是两个肉蛋。启德嘿嘿着,把肉蛋托在手上,喊:快看哦,快看哦。
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滚圆的奇大的粉嫩的肉蛋,还挂着一丝血,冒着一丝气,上面的根根须须,筋筋络络,好像还在一闪一闪地跳,一闪一闪地跳。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