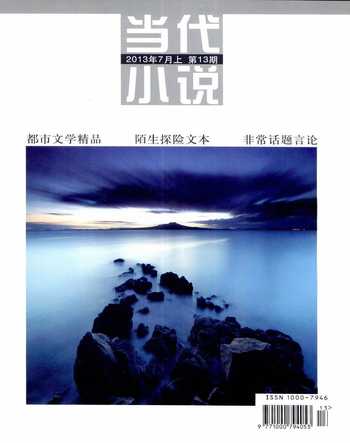空间
莫飞
桂花开的第二拨。香气已经散了架,气若游丝般缓慢地飘向老旧的居民楼,轻轻拂过墙面上,一条条开裂又被柏油涂抹过的疤痕。
鲁慧在二楼厨房的窗口,处理一只中秋过季后的酱鸭。先把鸭腿卸下,这是給儿子留的,再切一盘零零碎碎的送到一楼经常帮忙照看儿子的老人云那里。
桂花香微弱的香气从楼下飘上来,她放下了刀,鼻子往窗户口嗅了一下,结果嗅了一鼻子油烟和尘土的味道。纱窗经年不洗,已辨不清颜色,上面还留着蚊虫僵硬着的身体。鲁慧又踮起了脚,想探一下是哪里的桂花又开了,可楼下只有两棵矮墩墩的杜鹃。
鲁慧去卫生间洗手。卫生间狭长,是被厨房和卧室过分挤压的后果。为了不显得逼仄,墙壁上镶了一块很大的镜子,镜子把卫生间浓缩成一幅画:一只没有坐垫圈的老旧白色抽水马桶,釉面已经发黄。三根不锈钢管制成的毛巾架,钢管簇新。这是夏天到来时鲁慧央求装空调的师傅,帮忙打洞新装的,师傅说,这些所谓的不锈钢以后都会生锈。在画的上方的孤角,淋浴的花洒悬在上空,殷勤地为画面做冲刷工。成年累月的水渍进入了画面,画面上起先是一条条曲曲折折细黑的脉路,越延伸越粗壮起来,像充盈的血管,却在某处突然爆裂,画面上便开出乌黑的花来。
又有微弱的香气勾引了一下鲁慧的某根灵敏的神经,她把粘着滑腻的香皂冲洗一下放回原处。单膝搁在马桶盖上,用另一只脚作支撑,身子往外伸,探到窗口。是那棵围墙内的桂花树,这是它的第二茬花,鲁慧好像最终确认了这个事实,这瘦弱的丹桂在早秋的时候曾热闹地开过一茬。
住在三楼上的老太太银,在树下铺了一层薄膜纸,拉住枝叶不依不饶。丹桂金屑般不情不愿地掉落下来,住在四楼两年前走了老伴的坤一副形销骨立的样子,戴着眼镜,背着手,一声不吭地站在旁边看着。
干燥的秋天,鲁慧在楼梯上碰到手拎着薄膜袋子的银。她冲银点点头,银的眼睛很大,眼下方塌陷得厉害,露出无数鲜红的毛细血管,让人不忍细看。银会在每个人跟她打招呼时停下来,睁大着眼睛,嘴唇一直蠕动着,没有声音。她会在原地一直注视着,直到打招呼的人逐渐消失在视野尽头。银才会吐出一句,去上班了啊。
一声古怪的叫声。鲁慧把搁在马桶上的膝盖放下。站直。这个叫声总是在她专注于某一时刻时突然响起。叫声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了。是一只鸭子?又好像是鹅发出的叫声?鸟的叫声不是这样,鸡的声音也不是这样,狗猫的叫声更不应该是这样。鲁慧无法判断。它的叫声显然不是嘎嘎那么简单,没那么聒噪,也不是什么高亢、洪亮,而且每一次都只发出一声。也许,是一只鲁慧从没见过的什么宠物鹅。声音像是长久地闷在细长的脖子里,突然迸发出来的,不尖锐。等你还想再听一遍,细辨一下声音的归属时,它又哑然无声了。在下一刻,在你全神贯注而且毫无防备的时候,它又来了。深夜,在空空荡荡的楼道里,戛然而止的叫声,好像是一个长途跋涉者郁积于胸的呼唤,这种呼唤在长长的间隙里却又得不到回应。
楼上楼下有关于这个叫声的种种猜测。
楼上楼下总共住了6个人,这中间还包括从未见过面、长期躺在床上的一个老太太。
楼,孤立在城市外,霓虹灯照不到它,出租车不愿意经过它。它曾经是某个单位的宿舍楼。城市的重心不断向远处延伸,没有年轻人再愿意守着它,它围着半截残败的围墙,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越来越佝偻起来。
鲁慧一年前带着6岁的儿子搬来了这里。于是。空荡寂寥的楼里有了些热闹。他们的消息集散地,是在楼梯的入口。两棵矮墩墩的杜鹃,蹲在水泥地面与围墙空隙里,听着坤与云的对话。一口浓浊的痰吐在杜鹃细绒毛的枝叶上。鲁慧盯着两张叶片上粘连着颤动着的痰。老头坤断言,那叫声肯定是一只鸭。云说,也可能是只八哥什么的,她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心想,要是八哥那你也弄点好听点的声音出来,这作对的叫声总是在她迷迷糊糊的时候出现。银的观点又有点特别,她说,这声音一点也不吓人,好像是公园里猴子的叫声,就是只猴子。
他们曾到这个声音的发源地查看过。这是一片狭长的草地,在楼的一侧,围墙与楼房之间,用钢丝栅栏圈起的一片草地,仅留一条细窄的水泥过道。那棵百无聊赖的丹桂被摒除在了栅栏之外。栅栏内疯长的紫苏和狗尾巴草把中间蓝顶的铝板小房子隐蔽起来,露出蓝蓝的屋顶。这是一间漂亮的房子,像鲁慧儿子图画书的童话屋子,有着白色拱形的门,还有漆成红色的屋身。在这个漂亮屋子的前面还有一盏白色的路灯,三个灯盏像秋天落日前的牵牛花,委婉地低垂着头,虽然灯盏上面没有一只亮的灯泡。
高过腰部的钢丝栅栏,阻挡了窥探的欲望。这像平日里的一块禁地。坤和那个戴着深度眼镜的退休女教师英子曾鼓励他们中间惟一年轻力壮的鲁慧翻过去,去看一下那个蓝顶的铝板小房子里关的究竟是什么。
鲁慧靠近那个钢丝栅栏,试着抬了几次腿,这样的高度跨越,让她觉得不安,在跨越进去的第一步,茂密的杂草里有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如果真要爬过去,她必须找个凳子才能翻进去,她这样对坤和女教师说。可是后来两人站在栅栏前聊天,谁也没有再提翻进去看看的事情。
不过,坤有一次还是说起了在草丛里的那间蓝顶小屋的历史。他知道围着钢丝栅栏的地方,是很多年前这幢楼里一家住户为养狗而圈起的地方,蓝顶的铝板屋养着一条叫金毛的狗。金毛长得壮实。舌头一伸,口水滴滴答答下来了。那个时候楼里住满了人,听说这小狗买来的时候就得好几千元,吃过饭的人们都会站在那条细窄的水泥过道上,隔着栅栏逗身价不菲的金毛玩。金毛就在栅栏里生气,跳跃。后来那户人家搬走了,金毛也走了,可栅栏一直在那,没人想着拆除。当然没人想着进去,里面的野草就开始疯长起来,各种杂草相互掺杂,狗尾巴草、连钱草、紫苏,都以各自的方式快速成长。只有丹桂很寂寞,它俯视着栅栏里的草草叶叶相互攀爬,自己没有竞争对手。
坤背着手,还是坚持观点跟鲁慧说,“这里面养的是只鸭,白色的毛,脖子有些长,而且只有这样的鸭子才会这么叫。”
英子对鲁慧说,“鸭子很可能是躺在床上从不露面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养的,有天中午她在卫生间的窗口看见老太太的儿子曾翻进栅栏。在小房子前面放了碗水,还撒了一些谷子。”
鲁慧问:“为什么养只鸭在里面?”
坤断言,这是有人送給老太太在法院工作的儿子的,一定是吃不完,暂时养在这里。
英子接茬:“老太太儿子給她拿东西,吃不光,堆在房间,过段时间,就扔垃圾筒了。”英子瓶底厚的左眼镜镜片上有一条竖着的裂纹,说话的时候她就把那只眼睛睁得老大,这样看起来就像眼球被裂纹切割了。鲁慧每次跟她说话都尽量把视线放在她的眼镜下方,那个被眼镜压塌的鼻梁。
鲁慧曾碰到过老太太的儿子,他通常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车,在午后过来。穿着白色的衬衫,藏青色的裤子,皮带系在微腆着的肚子上。他通常来母亲这里午睡,在上班时间离开。他一直是行色匆匆,拎着黑色的公文包,低头,像在匆忙思索某个案例,永远也思索不完似的。鲁慧曾想过他一定是带长的什么官,她在每次与他碰见时。都会微微抿起上下嘴唇,拉开嘴角的弧度,等待他思索完毕抬起头的一刹那,那个弧度就变成微笑了。可至今为止,鲁慧从来没让那个弧度变成过微笑。
鲁慧经常会把这个一本正经低头的人和老太太长时期足不出户联系在一起。儿子为什么不叫个保姆长期侍候她老人家呢?这个男人一定非常细心。鲁慧想,要不然为什么不放心请一人侍候他老母亲?还是个孝子!他常来母亲这里午睡,好像是怀旧吧?还有,他常常低头走路,就说明他没有跟左邻右舍沟通的愿望。鲁慧曾问过坤,这个足不出户的老太太你们以前见过没有?坤说。怎么没见过?就是老太太的行为常常很怪异,好像怕邻里们会托她儿子经办什么案子似的,坤说完,嘿嘿笑起来。
银很慢地从楼梯上下来,她常常会默默盯着老太太的儿子。她踱步,踱到了栅栏旁边,老太太儿子的汽车发动的声音传来,银则长久地站在栅栏前注视着蓝色的小房子。茂盛的紫苏有跃跃欲试探出栅栏的冲动,银的两片蜷缩在一起的嘴唇一直蠕动着,像在蚕食着紫苏的叶子。
鲁慧在附近服装厂打零工。离家近,活不多的时候,中午她可以回家一趟,准备一下晚上的饭菜。路过栅栏时,蓝顶屋里那个家伙叫唤了一声。鲁慧的脚步停顿了一下,她现在越来越相信,这里面关着一只鸭,一只雪白的鸭。可是鸭的脖子里怎么会发出这么奇特的声音?这小屋子里为什么要长期囚禁一只鸭子呢?鲁慧向小屋张望,鸭又一次沉默了,在一片静谧的草丛里,一切都恢复了安静。
围墙围起来的五层楼没有铁门,其实有门,它只是以一种散架倒地的姿势伏在旁边的荒草地上,一枝黄花在它发锈的身体旁以昂扬的姿态生长着。在庆幸还没倒地的围墙上歪斜着订了几个报箱。只有坤的报箱还隔三岔五斜插着一份老年健康报。鲁慧在下班的时候发现,在坤报箱旁边,插着一个白色信封。这个报箱鲁慧没有钥匙,202,是她住的屋子,理所当然,这个白色信封是她家的。她还是有一点犹豫地抽出了信封,写的是她的名字。信封右下角有落款,二区人民法院。
坤的两只手里都拎着东西,两根黄瓜和三个土豆,还有几个馒头,从老远的水杉树下走来。他尽量睁大镜片后面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报箱旁边站着的人,不自觉地脚步迟缓起来,布鞋底接触着粗糙的水泥地面发出磨擦的声音。
鲁慧朝坤的方向张望了一眼,把信封攥紧塞进了口袋。确切地说,这不是一封信,是通知。鲁慧盯着二区法院关于涉嫌诈骗的开庭通知。这张两页的纸上,列着几条法律条款,列着一个人的涉嫌的罪行。而这纸上所陈述的人鲁慧已经一年多未曾谋面,虽然此人是儿子的爸爸。这个人告诉她,不要联系他,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他欠了很多钱,也欺骗了很多人,他很快就会被抓进去。鲁慧带着儿子搬到了远离城市,远离街道的这一幢破落的楼里。过后不久,她給他发了一个短信,告诉他地址。如今,他給了她这样的一个回复。
鲁慧又听到栅栏里的东西发出的声音,像是多日未进食的样子,叫声有气无力,这样的叫声越来越稀疏,有时一天也听不到一声。
鲁慧去云家里接回儿子。云坐在角落,儿子在靠窗的桌子上画画。太阳西斜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的叶片,射在碗柜上的两个描蓝线瓷碗上。
鲁慧问云,是不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没回来,关在那里的鸭没人喂,饿得没力气吓人了?
云说也不全是这样,这鸭凌晨会叫,只是叫得少了。云说话语调缓慢,声线很虚,像光束中的尘埃,缓缓地漂浮在空气里。
儿子在门口跟云道再见,云送娘俩走到门口。娘俩在楼道里手捏着手,云默默站在门口看了他们一阵,随后关上了门。
鲁慧很想在这个时候儿子能叫她两声妈妈,可儿子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回到家里,鲁慧觉得从来没有如此的寂寞。房间里仅存的一点点光线仿佛越来越黯淡,鲁慧害怕失去这仅有的一点点光线。
很多个晚上,儿子会紧紧搂住鲁慧的脖子,问爸爸去了哪里。鲁慧摸着他的脑袋,说爸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做生意。儿子又问,妈妈,你们是不是离婚了。因为云是这样问他的。
鲁慧问儿子,你怎样回答云奶奶?
儿子说,我问云奶奶什么叫离婚?
云奶奶说,离婚就是爸爸和妈妈像陌生人一样生活。
鲁慧的儿子有时也学云说话,把一句话拖成长腔,鲁慧就会轻轻打一下儿子的屁股。鲁慧感激云,在自己晚回家的时候帮着带儿子,可心里总像压着块乌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长久以来,她总是坐立不安,这种坐立不安随着小屋里那谁也报不上名来的叫声持久不散,更是让她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但她并不希望有谁注意到自己的惊恐。
周末和节假日,她把自己和儿子关在家里,开着电视,教儿子识字或做各种游戏,碰撞桌椅的声音,儿子的笑声,这样的响动把楼上楼下吵着了,可他们从来不找上门,似乎还很高兴。英子和坤有时还有银,就站在矮墩墩的杜鹃旁,朝二楼张望,虽然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鸭子的叫声已经很少听到了。鲁慧又去问坤是不是这样。坤说是这样,不过他前天好像还看见它黄色的长嘴,在拱形门上方的一条宽缝里伸了出来。
鲁慧开始想念那只鸭。觉得鸭把嘴伸出来一定是里面太逼仄了,或许是饿或者渴。
怪了,现在鲁慧反而有些焦急地等待着它的叫声。
它可能快死了!鲁慧有一天突然想。
它会死吗?我能否帮它下忙?鲁慧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只要她打开蓝色铝板房的小门,那它就能出来,鸭可以用翅膀奔跑的。它不仅能飞出这栅栏,还能飞出围墙。那么,它就自由了。
鲁慧选择在午饭后去做这一件事。
这座楼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午睡了,鲁慧开始了行动。她搬了个凳子,小心翼翼地从二楼下来,不让一个凳子的脚擦到楼梯的扶手。凳子在栅栏外放平稳,她轻而易举便翻进了栅栏,踏进那一丛丛茂密的连钱草里,草地很柔软,没有什么响声,她已经忘记万一有蛇出没的安全感。
那些遮盖住蓝色铝板房的紫苏被刀砍伐过,露出枝子的斜切面,锋利地刺向天空。鲁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扇拱形的门,里面却没有一丝的动静。她从旁拿了一截紫苏僵硬的枝条棒,往里试探地戳了一下,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在移动。它不肯出来,是突然的光亮让它不适应?鲁慧学着它的样子从嗓子眼里咕咕地喊了几声,鼓励它出来。它终于动了,鲁慧也看明白。它并不是一只鸭子,而是天鹅,是一只灰色的、有着长长脖颈的天鹅。它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灰天鹅开始慢慢向外走动,它翅膀的颜色比周身更深一些,并且开始暴露在正午的阳光下,屁股上的毛被自己的粪便粘成了一坨。现在。光线把它的毛色和茎状部分都一一罗列出来,像一块由浅到深的调色板。
鲁慧突然想起,这个地方有吃天鹅的习惯,只是不知为什么那个在法院工作的孝子没有把它給他母亲吃掉!鲁慧又看了看天鹅,再看看天空,天鹅并没有看她,只是惘然地站在门口。
鲁慧用棒去拨它的屁股,对它说,逃呀,你不是天鹅吗?你能飞啊,难道天天关在这黑屋子里,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好么?
天鹅只是扭动了一下屁股,朝鲁慧轻轻叫唤了一声,继续站在门口。鲁慧又气又急,扔掉了棒子,用脚踢了一下它的胸脯,它却慢慢地又想钻进屋子。
鲁慧的心情被这只天鹅搞得复杂起来,她在茂密的草丛里走了几步,踏出了一条软软的草径。她又走到栅栏边缘。靠近丹桂,看到还开着几簇桂花,便有些粗鲁地揪下一撮桂花放在鼻子下,却发现一股看不见的尘土味道钻进了鼻孔。她丢掉了桂花爬出了栅栏。
爬出栅栏的鲁慧发现,小房子的门依然开着,那只灰色的天鹅又一次出现在它的拱形门口。鲁慧瞪着看它,在心里刚说了一句:你真的飞不起来了吗?这时,灰天鹅的翅膀展动了一下,接着开始扑楞,它试了两次。终于,摇摇晃晃飞了起来。
鲁慧轻轻舒了口气,你还是会飞起来!你快飞吧。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急匆匆的,是在法院工作的那个孝子。
鲁慧突然想起,是不是可以找他说两句。说两旬什么呢?鲁慧来不及思考便迎了上去,嘴角的弧度列好了阵,可这时,她却发现自己手里还拎着刚刚用来爬栅栏的板凳,鲁慧不知道是放下凳子还是继续拿着,可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了……
而那只灰天鹅,早已上了蓝天,向着远处飞去……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