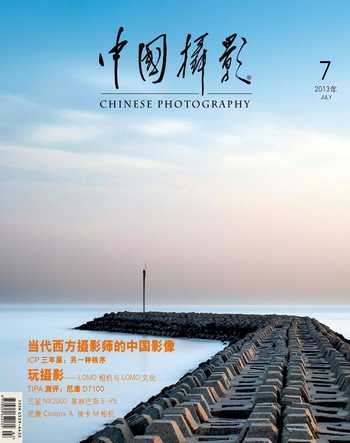东行路上的西方摄影师
沈怡



1844年,法国海关官员阿方斯·尤金·于勒·埃及尔(Alphonse Eugène Jules Itier)来中国成功拍摄了第一张照片,从此,中国这片土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摄影师。近170年来,西方摄影师对于中国的人文景观进行的记录和传播,对西方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国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作品和创作形态又对中国摄影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影像见证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
1844年埃及尔的第一批银版照片标志了摄影在中国传播的开端,较1839年摄影在法国发明发明仅晚了5年1。当我们庆幸摄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及早地获得滋养,却无法忽略的它的到来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国家对于原材料和新兴市场的渴望把早在十五六世纪就萌发的殖民主义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对于欧洲以外的国土、财富和文明的好奇伴随着他们强烈的占有欲席卷大半个地球。1939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一个接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这些摄影师当中有以全景照著称的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 以人像著称的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享有商业成功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以及大游客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他们各自的工作方式和地域有所不同,但他们记录的影像都见证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
作为随军攝影师的比托拍摄的天津塘沽炮台和沦陷后的北京等照片最直接地体现了当时的西方摄影师炫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武装胜利的心态。他受雇于英国军队,是唯一一位真正记录了鸦片战争尾声的摄影师。除此之外,包括埃及尔、汤姆逊、华生少校(Major J.C. Watson)、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保罗·尚皮翁(Paul Champion)、方苏雅(Auguste Fran?ois)等在内的多数摄影师以外交官、商人、贸易官、探险家等身份来到中国,从作品和日记等相关文字中不难看出他们的个人好奇心和游客的心态。1867-1872年,汤姆逊的足迹遍布中国南北,他拍摄的长江巫峡被他称为一路上看到的最美丽的景色2。他还用不少时间纪录和整理各种人物、风光、建筑、物件,留下了宝贵的摄影资料。20世纪初,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杜帖特(Alfred Dutertre)和斯提芬·帕瑟(Stephane Passet)受雇于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到中国拍摄。1909年杜帖特带着一套奥托科洛姆微粒彩屏干版的设备来到中国拍摄了第一张彩色照片。更多描绘中国的奥托科洛姆彩色照片是由斯提芬·帕瑟在1912年和1913年之间拍摄的,除了北京、张家口,帕瑟还到了山东曲阜、泰山,东北的沈阳、哈尔滨和内蒙古等地。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彩色照相技术的接触比欧洲仅晚了6年。这些游历广泛的西方摄影师对于中国的了解也相对深入一些。
当然更多的西方摄影师的活动范围相对固定。那个年代摄影师们从国外进口各种拍摄、显影和定影等材料和化学药剂,这些材料非常昂贵,所以不少早期到中国的业余摄影师开始销售自己的照片和底片,更有不少人把摄影作为一种职业,开起了照相馆为沿海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拍摄肖像照。中国摄影师有不少在西方摄影师的照相馆工作,或从他们手中购得相机,先后开设自己的照相馆。
对于中国人物和山川的定式早在摄影发明之前就由少量的版画和书籍在西方社会流传,以至于摄影出现后却仍然遵循这样的定式来迎合西方观众的期待。在这过程中早期西方摄影师的作品也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巫鸿教授在《丹青与快门》中的文章《早期摄影创立中国试的肖像风格》(Inventing a“Chinese” Portrait Style in Early Photography)以米勒的在广东拍摄的一系列肖像为例,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肖像和中国传统的祖宗画像之间的相似。双脚着地,正面直视相机,满格的构图等特点都是不同于同时代西方对于肖像照的要求。
而且,这些标有各种头衔的身份的肖像照其实是米勒请的演员穿着各种服饰进行的摆拍。这样的做法在那个年代比较常见,比如桑德斯也雇佣群众演员摆拍中国的各种职业以及婚礼、葬礼等场景。这些照片作为纪念品出售给西方人被称为人物“类型照”。“类型照”的拍摄,很快被同时代的中国照相馆吸取而且大量的模仿。这种中西方摄影师互相借鉴使得19世纪中西照相馆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摄影成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最重要的表述方式之一,拍摄中国成为一些西方摄影师的生存之道。他们所留下的影像大多被带回或销往欧洲,从而幸免于之后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客观上成为当下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记录战乱中的中国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在求变图强中挣扎,但已成了日本和西方国家争夺的猎物。 这一时期,19世纪就存在的西方照相馆仍然延续。澳籍女摄影师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就是在与位于北京的阿东照相馆的合同期满后,作为一位自由摄影师继续留在中国。 1933年至1946年期间她拍摄了上万张有关中国的珍贵影像。但这期间更多的来华的西方摄影师是新闻摄影记者,其中最有名的是匈牙利犹太裔美籍记者、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37年,日本发动了对华的侵略,卡帕是抗战时期唯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他在上海等地拍摄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新闻照片,体现了对于同盟军的同情和鼓励。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的照片也因为电影《1942》近来颇受关注,他在1942年对国民党辖区河南省的大饥荒的采访报道发表在美国的《时代》周刊,曾一度激怒国民党。
1930-1950年代被称为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重要的杂志和周刊依赖摄影获得了大量的读者群。诸如《时代》《生活》这样的新闻杂志在中国和西方的信息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1947年成立的马格南图片社,其创办者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卡帕都是拍摄中国的最重要的西方摄影师。
卡蒂埃-布勒松在1948年末被《生活》杂志派遣到中国,对政权更替前后的中国进行拍摄和报道。他在北京呆到了解放军进城前的几天,然后辗转来到南京,随后到达重庆。之后在上海等地逗留,最终从香港离开中国返回法国。他对于北京的记录恰好是一个转择点之前的景象。且不说摄影师自身的意图,西方社会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恐惧使得卡蒂埃-布勒松的这批照片后来频频出现在展览上,配合文字和他当年的旅行路线,来体现某种逃离中国的表象。其实这并非他的本意,1955年他的摄影集以《两个中国》为名,照片的时间跨度为国民党垮台前六个月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六个月,记录了当时中国在变革中的历史瞬间。
如果说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两次世界大战则把中国逐渐拉入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但也是历史上中国与西方有大量的信息沟通的时期。 直到1980年代很多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还停留在1930 和1940年代。
冷战时期的影像定式
二战之后整个西方社会对于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恐惧,随后而至的是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为首的长达40多年的美苏争霸,又称“冷战”。在这个阶段,中国经历了建国、“文革”、改革开放等许多不同时期,但是总体来说,西方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戒备心态贯穿了整整40多年,中国也用一种相对封闭的态度对待西方思想和事物。
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处于封闭的状态,西方对于中国的报道较少。年轻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受雇于马格南图片社,在1955-1958年几次来到中国进行拍摄,他被称为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他的风格延续了卡蒂埃-布勒松的传统。1958年卡蒂埃-布勒松再次来华记录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与当时中国本土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体的摄影不同,他们的照片力图捕捉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气息,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刻意的封闭状态,他们都无法真正深入中国社会。他们的作品流传到西方后,西方社会反而无法摆脱这些照片带来的某种西方社会优越感的提示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定式的想象。到了“文革”时期,中国的对外封闭更是有增无减。此时少数能够来到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们大多是所谓“左派”,对于共产主义和“文革”抱有某种浪漫情怀。所以他们照片中渲染的是封闭中国的单纯和秩序感,雷尼·布里(Rene Burri)拍摄的1960年代的延安,和布鲁诺·巴比(Buruno Barbey)拍摄的1970年代的文革青年的淳朴形象,都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当时的中国对西方摄影师的中国影像并不认同。1973年,意大利现代主义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纪录片《中国》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的影片让西方社会看到了中国更现实的一面。安东尼奥尼被允许来到中国拍摄本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同情,然而,这位现实主义大师在短短的六个月中窥探到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另一面。他的《中国》激怒了中国,当年中国的各大报纸曾一个接一个的批判这部电影,连周恩来也因为给拍摄组提供了自己的红旗轿车而招来各方的打击。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从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非正常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也使得西方社会不再把中国列为他们的正面敌对国家。很快,更多的西方摄影师、记者、学者来到中国,迎来了1980年代。这个时期摄影师所描绘和体现的多是对于“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定式的一种延续,也是对封闭多年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好奇。
中国题材在当代的多元化呈现
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苏联的瓦解,确定了冷战的结束,也标志了另一个时代的到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推行和邓小平南巡等一系列形势,展现给西方社会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经济发展逐渐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形象,中国被隔绝后的神秘感在逐渐消退。
法国摄影师帕特里克·扎克曼(Patrick Zachman),通常被称为马格南的第三代关注中国的摄影师,到中国进行拍摄始于1980年代,一直持续到当下。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对于中国的印象首先来自上个世纪30和40年代的上海,所以他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拍摄的都是带有异域风情的中国,也曾出版《大鼻子眼中的中国》。但是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和态度的变化,他关注的事物也有了变化,他也是那个年代少数进入到中国人的私人空间进行拍摄的西方纪实摄影师,对于中国人的兴趣把他带到国外的华侨社区和唐人街进行拍摄,他进而开始追踪中国在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比如民工和劳务迁徙。
在当代拍摄中国的西方人中,尽管新闻和纪实摄影师仍然占主流,然而更多的当代西方摄影师的作品开始呈多元化趋势,图片社和杂志的角色逐渐被削弱。摄影师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发表自己的作品。在1990年代德国摄影师托马斯·施特鲁斯(Thomas Struth)也在中国拍摄了一批城市的照片,然而施特鲁斯对于中国的兴趣始于1970年代,他对中国“文革”时期特别有兴趣,1972年第一次来中国,而后曾在1980年代多次到中国学习道教和佛教,而直到1995年他才开始在中国拍摄,这种在充分了解之后再开始创作的态度是值得关注的。
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 拍摄的工业化风景和德国摄影师安德亚·古斯基(Andrea Gursky)、彼得·比阿罗贝泽斯基(Peter Bialobrzeski) 、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所关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的景观多以中国为背景。然而,他们关注的问题都不局限于中国,他们感兴趣的是全球经济形势下,城市化、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出现在他们的相机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少不了中国这个章节,当下的西方摄影师无法忽略中国。
摄影师的创作受自身的风格和关注点影响,而他们的作品也是建立在自己熟知的价值体系中的。但是他们对待拍摄对象的态度和拍摄过程已经从早期的“游客”和后来的“记者”视角,逐渐变为思考影像背后的社会问题。不少西方摄影师们,干脆長期生活在中国,观察和搜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阿兰·戴勒姆(Alain Delorme) 的《人造的图腾》和贝恩德·哈格曼(Bernd Hagemann)的《打盹》从表面看是延续了街头纪实摄影的传统,然而他们敏锐地涉及到了当下中国社会这种超负荷的现状,以及中国人在超负荷的生活节奏下对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混合。《打盹》不单是一个摄影作品系列,还是一个带有公共参与的艺术项目,哈格曼建立网站让公众进行评选和参与这场讨论。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的《拷贝艺术家》、帕特里克·扎克曼的《真的假的》都是对中国复制品行业的一种描绘。当然这些作品中不无对中国社会的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带着诙谐,也体现了一种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态度。而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也显示了艺术家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上。
近年来一些西方摄影师的中国影像首先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12年一组名为《中国2050》的作品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这组作品以摆拍的手法,构想在欧美国家渐走下坡但中国经济掘起的时势下,38年后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其作者是生活在武汉的法国摄影师贝诺特·舍扎尔(Benoit Cezard),中文名刘本恩。他在这组作品的说明中写道:“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未来中国的农民工将由西方人取代,所以他们得提前适应一下。”另一组名为《城市的轮廓》的作品也被不少网站转载,其作者是目前生活在中国的英国摄影师贾斯珀·詹姆斯(Jasper James),他在作品中把深圳的城市边际线与人像叠合。不过这组手法简单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中国的理解,如果没有提示,我们很难分辩我们眼前的是世界上的哪座城市。
还有一些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具有多重文化背景。叶仁杰(Daniel Traub)是其中一位值得关注的摄影师,他常年生活在纽约和上海,作为中美混血的西方摄影师,他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有某种耐心,这当然是伴随着他一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工作创作和生活的某种个人动力和好奇心。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多具有全球化经验的摄影师和艺术家,选择用更多元化的角度和手法来切入中国这个主题。他们在给中国带来更丰富和复杂的视角的同時,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性评判也让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自己。
总结
通过对于早期中国一直到当代的不同时期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摄影师对于中国的态度有着非常鲜明的变化,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者心态,到二战时期对于新闻性和客观性的追求,冷战时期对于封闭下社会主义定式的遥望,直至当下更平等和更开放的探讨问题的方式。这种变化是国际政治形势决定的,也是社会文化交流的结果。在任何一个时期,理解西方摄影师的创作方式必然以世界摄影史为背景,因为他们正是这个世界摄影史中的组成部分。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也已成为影响中国摄影进程的重要因素。本文的讨论把重点放在对于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自身的纵向分析,这是进一步厘清中西方摄影互相影响和中国摄影发展的线索之一。然而,对于摄影和摄影作品的研究并非根本,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理解摄影背后的观看方式,从而推断拍摄者所依赖的认知体系,正如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论中的影子和真实之间的关系。几千年后,这个洞穴仍是我们的世界,而面前的影子仍随火光晃动,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影像提供的线索,质疑眼前所见,探讨形成影子的原理,甚至这种原理中各个元素的变化,从而获得最接近的真实,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