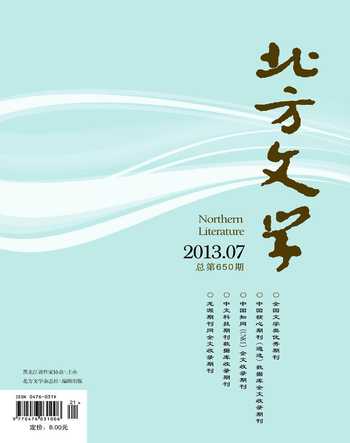舞动的线性艺术——草书浅论
摘 要:书法利用单一的线条和最简单的黑白对比来表达这中国哲学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将对艺术的创作,利用线的变化展现出来。围绕这一思想,利用笔的提、按、顿、挫;搅转启合,将单一的线条,创造出丰富的变化,使书写出的汉字产生出有韵律的舞动之美。
关键词:书法 线条 韵律
中国文字的根源是由原始社会时期的装饰纹样演变而来,而这种原始的象形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演变,然而其本质从未改变。线与形象的结合,行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用线条的变化与通过文字进行文学创作来表达情感相结合的艺术,书法。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是:最为单纯的本质,在道家思想中认为万物由一而生,清代画家石涛则在画语录中写道:“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在《法华经》中:“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而书法正是利用单一的线条和最简单的黑白对比来表达这一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将对艺术的创作,利用线的变化展现出来。围绕这一思想,利用笔的提、按、顿、挫;搅转启合,将单一的线条,创造出丰富的变化,使书写出的汉字产生出有韵律的舞动之美。
传统书写工具毛笔具有柔软的特性,将书法中线条的变化展现的淋漓尽致。在纸本上书写更能既是展现作者即时的情感,从魏晋文的觉醒,同样也是人本主义自身展现的开始,书法更多的与诗、赋等文学作品相结合,直抒胸臆,产生了大量的纸本书法作品流传于后世。“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如《毛诗序》中所写,人们用舞蹈来表现内心的极致情感,而这种纸本上的书写,带有舞动的旋律,这种旋律用线的变化来表现,形成了舞动的线性之美。
书法从汉代末年开始,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在魏晋人文思潮的带动下,大量的书写章法、书法理论的出现,如蔡邕的《九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王羲之《兰亭序》为引领,书法成为主流的艺术形式。在文化的传承下,书法作品也成为人们争相热捧的收藏艺术对象。而在这种发扬自我个性的时代。从汉代开始产生的草书打破了章法的局限,笔势流畅。草书体式的流转变化,更能展现书写者的个性。而看似无法的草书,具有最严格的章法、气韵要求,展现出了狂放、奔腾的舞动之势。这必然要求书者具有高超的技法、精神,来提炼出最为精纯的线条展现这一艺术表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而这种自信带来包容万象的大气势,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书法、音乐、舞蹈不同的文化艺术思潮,都达到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唐人的性格奔放,踏歌起舞。草书的自由挥散与之相契合,在这个自信包容的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迎接这个时代的草书凝萃了狂放不羁的自由情感,自由奔放行笔态势,深邃峻奇的意境,形成了最高的书法笔墨形式:狂草。以张旭、怀素为代表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世人称之为“狂张醉素”。其书法艺术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了时代的标志。
同代的诗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称赞张旭的潇洒狂放:“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李白则在《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相传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得草书真谛。狂草的线条奔放自由,展现了如同剑舞般“来如雷霆收震怒”,“天地为之久低昂”的情感表现,展现出意气勃发的生命力量。张旭的代表作墨迹本,纵为28.8厘米,横为192.3厘米的《古诗四贴》,纵笔如“兔起鹘落”,狂放不羁,潇洒浪漫的气质,如同唐代乐舞般盛大激昂。同样怀素的《自叙帖》,线条穿插摇荡、呈纵横开合之势,犹如暴风骤雨、灵动飞转。
据《国史补》与《自叙帖》记载,张旭与怀素都是在饮酒狂醉后,精神癫狂迷乱的精神状态下进行书写创作。在这种酩酊大醉下,精神完全释放,冲破了理性的禁锢,随心所欲,笔走龙蛇。将内心世界的狂歌乱舞,利用手中之笔,重现于纸面。在这种癫狂的精神状态下,奋笔疾书,正如《自叙贴》所述:“忽然绝交三无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纵观二人书法,犹如欣赏最为大气激昂,肆意放纵的舞蹈,展现出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
观张旭与怀素的书法,像观看一场盛大的唐代乐舞。唐代乐舞几乎已不可见,通过二人的书法,这种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的书法形式语言,狂草展现了线性艺术表现的最高形式,充分的展示了点与线的结合,抽象变形的精髓。非理性的情感抒发,主观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将线的舞动韵律达到了飞扬激荡,肆意放纵的极致。
参考文献:
[1]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陈廷佑.书法之美[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吴慧玲(1984-),女,籍贯:石家庄,河北大学2011级美术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