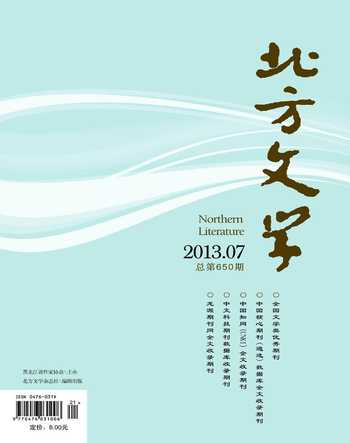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辨析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首次编成十五卷诗集后写的“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廿”。在诗中他对诗集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诗歌的第一句“一篇长恨有风情”,既自诩《长恨歌》是他的压卷之作,又点明了《长恨歌》寓寄了很深的“风情”。“风情”正是我们分析《长恨歌》主题的重要切入点。
自《长恨歌》问世以来,就引发了主题之争。历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三种说法。一是“讽喻主题说”: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指出其主旨意在“惩尤物,治乱阶,垂于将来”,成为了后世讽喻说的滥觞。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表现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二是“爱情主题说”:《长恨歌》由白居易执笔来写,缘由是“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可见李杨爱情故事本身就是很感人的。而从白居易和陈鸿对李杨事迹的剪裁,断定了创作目的是宣扬真正的爱情,诗中饱含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另外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是讽喻诗,也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三是“双重主题说”:持此说者认为,《长恨歌》一方面对李杨因为生活的荒淫招致祸乱,进行了尖锐讽刺,另一方面对杨妃的死和二人对爱情的笃诚,寄予了极大同情。这种主题说看起来很是公允,因此在很长时期里占据了上风,但这种折中取巧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和稀泥,并不值得倡导。
通过综览全诗,了解白居易的生平和主张,笔者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
《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象而成的帝妃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因此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但写作的结果却是作者倾注着作自己感情的爱情描写。
首先从白居易的生平经历可以推出,诗人实际上是在借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来表达自己对往昔美好爱情的追忆。《长恨歌》作于公元806年,而在公元803年白居易作官返乡,与自己的恋人湘灵分别时,写下了一首《潜别离》:“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而在《长恨歌》中,李隆基与杨玉环无可奈何的分别明显有此诗的痕迹。甚至到了作者中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晾晒衣物时,白居易都不由的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仍禁不住思绪翻腾,感叹再三,赋诗抒情,并为此惆怅。近八十高龄时还写下“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之句。同时,全诗的结尾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可谓非有此亲身经历不可为此句!
另外作者在安排《长恨歌》的结构内容时,以“情”为中心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围绕“情”这个中心,诗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杨贵妃相爱到恋情进一步发展的描写,后半部极力表现杨氏死后李对爱情的坚贞执着。诗篇1/3叙述了历史,而白居易用剩余2/3的篇幅,最多的笔墨,最深的情感来表现他们的爱情。用大量的笔墨细致的描述了他们爱情缠绵的情形,当杨归阴后,李面对旧景感慨万千,不由自主,睹物思人,一切如故,却已物是人非。作者非常形象的把李对杨的那种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接下来,白居易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使李于飘渺的仙境中寻找杨氏的踪影,又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做“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主题,结尾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
如果说,杨氏身前,他们的爱情带有物质享受的成分,那么,杨氏死后,执着的思念,是一种完全丢弃物质的精神活动,这种感情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最后,诗人在写作《长恨歌》时,以历史作为素材,但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假如说作者是将立足点放在对李杨二人的批判讽刺上面,那读者难道会全部会错了作者的意思吗?因为绝大部分的读者在读完《长恨歌》后,往往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而李杨之间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婉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纯情的世界,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作者简介:连小华(1978-),女,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自2002年至今任教于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