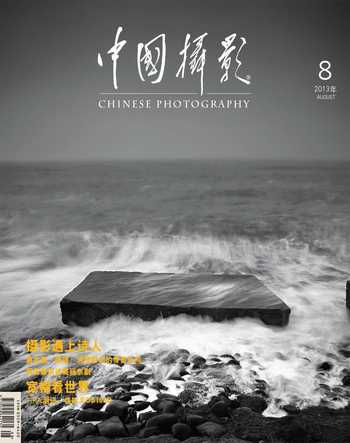这么爱你为什么?
任悦
偶尔会去做一些摄影讲座,每当我使劲打听要讲什么,对方总会这样告诉我:就讲摄影好了。
不少讲座,待我讲完之后,根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气氛,反而有种再见面会非常尴尬的感觉。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有时候,负责联络的家伙也会给我出一些题目,比如—视觉传播的策略什么什么的,这种不提“摄影”两个字儿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也就非常费力地把课件弄得有理论高度。但不幸地是,每次课间,都有人过来给我提建议,能不能把课讲得实用一点儿?有一次,快结束的时候,后面传过来一个纸条:您能不能谈一下照片构图的问题。后来写条子的人还很诚恳地和我交流,他说周围有些初学摄影的同志总喜欢把被摄对象放在画面中央,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样拍很不好看。
这件事儿让我想到某次给一个大学生摄影社团做讲座,中间我们谈到关于北大未名湖的博雅塔,可以在网络上检索出成千上万张相同的照片:构图都很严谨,画面三分之一处是博雅塔,水面也遵循相同的黄金分割法则,这些照片都出自不同人之手,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拍一张“已经存在了的”的照片?就在那次讲座结束的提问时间里,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问:“您看,我拍了一张博雅塔的照片……”他可真的没有跟我开玩笑。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听众,也是一位业余爱好者,羡慕那些搞艺术的,关于他们那里一位特别有范儿的摄影师,他建议我:“你最好回去搜搜他的图,拍得特别漂亮”。
对于这位在当地很有名的摄影师,我还真有点儿好奇。
摄影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职业?在昆汀(Quentin Bajac)所著的《摄影术的发明:第一个五十年》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研讨。作者提到,摄影术诞生初期,走入摄影队伍的,背景非常多元,他们可能曾经是牙医、眼镜工匠、手表匠、制图师、工程师……“任何人都能进入摄影领域,不能完成每日工作量的学徒工,咖啡馆演出团里失声的男高音歌唱家,以及有着艺术梦想的看门人。”尽管早期摄影仍然存在一定技术难度,但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门槛还是很低。摄影俱乐部在1850年代开始兴起,法国某个这样的团体,据说有大约150名会员,但只有30位是职业的,剩下都是业余摄影师。不过,聚在这些沙龙里的多半是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比如作家、科学家等等。
无论怎样的背景以及阶层,这些因摄影而被贴上一个共同标签的人,都心怀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摄影师身份能够显得高级一些,再直白一些,就是照片能够作为艺术品被承认。但现实却非常残酷,最早的摄影展是在工业博览会里举办,照片被当成工业产品。摄影师纳达尔(Nadar)曾画过一个三格漫画:第一格,摄影想进入艺术博览会,谨慎地敲了敲门;第二格,照相机却被调色板一脚给踢出门来……
好在还有第三格,相机最终和调色板手拉手比肩走入艺术殿堂—这个时间是1859年,这一年,摄影在法国被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年度绘画沙龙接纳,得以在其中展出,但展览空间却是一个被单独隔离起来的地方。这就是摄影被艺术圈接纳的开端:“没有完全承认,却也不是完全被拒绝。”
可是,就在摄影师为自己的艺术身份悲悲戚戚的时候,与之对应的现实是,摄影一诞生,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完全接纳。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证之物在自然、科学、城市建设、工业等各个领域的应用,还是作为一种神奇的时光机用来保存美好记忆,以及作为一种信息传递之物被迫切需要,摄影已经被世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摄影的生机恐怕也在此:它的快速复制能力,与时间的化学反应以及咔嚓一声带给拍摄者的快感,这都是摄影的美妙之处。不幸的是,摄影挤进艺术殿堂却恰恰是以牺牲这些特性为代价的:焦点虚化的技术技巧,脱离现实的画意主题,拍得像画儿一样成了摄影作品成为艺术品的前提。这兴许一下暴露了那些声称自己是摄影师的家伙的小秘密—他们都曾有一个未能实现的画家之梦。
总之呢,每当面临台下的诸位听众,我都禁不住要去想,这样一群异质人群聚合在一起,完全是以摄影的名义,但那究竟是怎样的摄影,能让人们如此虔诚地热爱?为何我们应用摄影狂野随性,贴上摄影师标签却变得拘谨而又不自信?而根本问题是,这个暧昧不清的“摄影师”称号究竟是否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