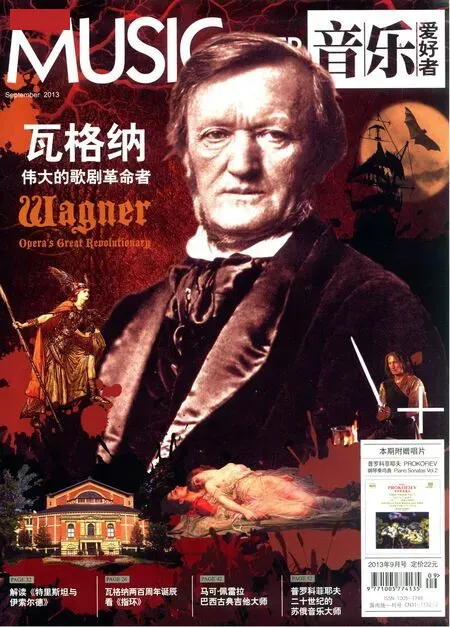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 二十世纪的苏俄音乐大师
陆轶文
1938年,普罗科菲耶夫最后一次在美国巡演,其间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访问。记者形容他“谈吐冷静,令人愉快,喜怒不形于色,看上去更像一位工业主管而非作曲家”。事实上普罗科菲耶夫是这样露面的:秃顶,远远谈不上英俊;喷了香水,身着裁剪精良的套装——这几乎难以与传统的音乐家形象联系起来;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已于两年前选择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定居。
那时普罗科菲耶夫已经为苏联听众写下多部作品,其中的一些例如《基日中尉》、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彼得与狼》如今依然广为人知。然而除了这些审慎的为人民而写的作品之外,普罗科菲耶夫还有更多的创作。初听他那优雅精妙、令人着迷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917年),或是仿佛凶狠咒语般的清唱剧《七个,他们七个》(Seven, They are Seven,作于1917至1918年,于1933年复排),又或是钢琴套曲《瞬息的幻想》(Visions fugitives,作于1915到1917年)中那些具有深刻反讽意味的篇章,都会令人惊奇不已。即使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普罗科菲耶夫仍然写出了诸如《第二弦乐四重奏》(作于1941年)这样的作品,其中他别出心裁且卓有成效地运用了高加索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而此作正是在那里诞生的。
野外的自然风光与乡村的隐居生活对普罗科菲耶夫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早年他在桑佐夫卡(Sontsovka)度过了童年时代,那是乌克兰的一个农业地区,仅有的音乐熏陶便是来自当地的农民以及他的业余钢琴家母亲。每天晚上,他都听到母亲练习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之后是一些肖邦、舒曼和李斯特的较为浅显的作品。五岁时,他已经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钢琴作品;1900年,他随家人去莫斯科,在那里看到了古诺的《浮士德》和鲍罗丁的《伊戈尔王》,大受启发,随即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歌剧《巨人》(The Giant),那时他年仅八岁。他十三岁生日收到的一件礼物是格里格的钢琴作品乐谱,这促使他近乎顽皮地对轻快的、非传统的和声产生兴趣,这种兴趣在他发现了梅特纳(Medtner)为钢琴而作的《童话故事》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那一年,他被介绍给了格拉祖诺夫,后者立刻推荐他前往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普罗科菲耶夫的正式老师包括当时的“活传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同时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私人教师),同时普罗科菲耶夫从他的同学们那里受益匪浅,其中包括他终生的好友米亚斯科夫斯基,他们一起弹遍贝多芬、格拉祖诺夫等人的钢琴作品,尤其是当时活跃在先锋派前沿的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普罗科菲耶夫反抗在他看来死气沉沉的学院派风格,他偏爱更具冒险精神的“圣彼得堡现代音乐之夜”,诸如德彪西和施特劳斯这样的外国现代派们的作品在那里首演,同时也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自己的作品。
即使还只是名学生时,普罗科菲耶夫便意识到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迅速成名缘于他与贾吉列夫的密切合作。1914年,普罗科菲耶夫刚毕业便亲自前往伦敦与贾吉列夫见面,同时还见到了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他受到委约创作的第一部芭蕾音乐作品《阿拉与洛利》(Ala i Lolli)并没有完成,或许是由于贾吉列夫认为这部作品是对斯特拉文斯基具有革新性的《春之祭》的简单模仿,于是他让普罗科菲耶夫重新创作一部芭蕾音乐。而这份成果便是《丑角》(Chout,完成于1915年,修改于1920年),它受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的影响而作,同时也有其自身的辛辣智慧。曾经有一段时间,普罗科菲耶夫与斯特拉文斯基关系友好,普罗科菲耶夫更是热情地回应后者的多部作品,其中包括“歌曲游戏”《俏皮话》(Pribaoutki)。然而当《丑角》最终在1921年上演时(那时普罗科菲耶夫已经离开俄罗斯去了西方),事实证明对于斯特拉文斯基先前伪装得太成功了。1922年歌剧《三橘爱》在芝加哥歌剧院首演,普罗科菲耶夫将此作呈现给贾吉列夫,希望后者能够将其搬上舞台。当时在场的斯特拉文斯基发动了攻击,他加深了贾吉列夫对歌剧的偏见,让后者认为歌剧是一种停滞不前的艺术形式。普罗科菲耶夫后来指责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个“盗墓贼”(grave robbing),他发现后者的新古典主义芭蕾舞剧《阿波罗》(Apollon)的音乐是“从最不光彩的口袋里偷来的,其中包括古诺、德里布、瓦格纳甚至明库斯(Minkus)”。
与此相反,普罗科菲耶夫试图忠于他时代的精神,写出了非常激进的“现代主义”作品,包括创作于1925年的《第二交响曲》以及创作于1926年的关于苏联工业化的芭蕾舞剧《钢铁时代》(Le pas dacier)。后者在西欧获得巨大成功,但当普罗科菲耶夫把作品交给莫斯科大剧院排演时,俄国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RAPM)谴责该作是“反革命的”,并将其禁演。经过这一挫折,普罗科菲耶夫的信心极度动摇,思乡之情加重,此时他开始发展出一种他自称为“新简约主义”(new simplicity)的风格,这种风格的音乐易于被广大听众所理解,而且听众乐于反复聆听。他为贾吉列夫创作的最后一部可能也是最出色的一部芭蕾舞剧音乐便属于这种风格,作品名为《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作于1929年),看起来颇具象征意味。
普罗科菲耶夫的“新简约主义”似乎符合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的理想,这是由斯大林于1932年在苏联国内规定的。此外,在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掀起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于1932年被废除后,苏维埃官员建议普罗科菲耶夫应该成为苏联国内复兴音乐的中流砥柱,这种奉承讨好也对说服普罗科菲耶夫举家回到苏联起了一定作用。普罗科菲耶夫后来违心地宣称,他的新风格是特别为苏维埃听众创作的。更为可信的说法是,他的新风格反映了他对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日益增长的信仰,他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便开始学习其教义。举个例子,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曾说,对于一名基督教科学会教徒来说,艺术必须“是容易理解的,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平等与博爱”。然而,早在普罗科菲耶夫投身于基督教科学会的十年之前,他早年的导师、同时也是“圣彼得堡现代音乐之夜”组织者之一的卡拉蒂金(Vyacheslav Karat?gin),便在一篇具有预见性的文章中展望过了这种“新简约主义”。在一篇发表于1914年的有关《春之祭》的文章中,卡拉蒂金推测科技上的进步,比如“汽车和飞机”,必然会对现代人的心智产生影响,因而也会反映在现代人的艺术之中;他进一步暗示了某些艺术家最终会“在刻意回归简约的过程中寻找一剂解药”。从那时来看,早在普罗科菲耶夫于十月革命爆发后的1918年离开俄国之前,他的现代派风格和“新简约主义”风格便已留下端倪。
普罗科菲耶夫坚持基督教科学会的某些信条,这意味着他甚至对自己的一些作品也采取了敌视态度,比如主题与巫术有关的歌剧《火天使》(The Fiery Angel,创作于1919至1923年,修改于1927年)。然而他从未成为一名清教徒,相反的,他继续从精致的饮食与新潮玩意中获得物质享受。基督教科学会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威胁着普罗科菲耶夫,要将他逼入灵感枯竭的死胡同,这从他1937年创作的那部风格不可名状的《我们的时代之歌》(Songs of Our Days)中便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普罗科菲耶夫在苏维埃时期还是写下了那些令人痛苦的悲剧性杰作,其中就有《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始作于1938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完成。作品中小提琴演奏的急速行进的音阶萦绕不去,作曲家形容这“像是一座冷清的墓地里刮过的秋夜的风”。创作于1947年的《第六交响曲》也是那些杰作之一,充满了令人心痛的怀旧之情以及刺耳的咆哮之声,最后更是迎来了所有交响乐作品中最为凶恶的结尾。这些作品表明,普罗科菲耶夫意识到他可能失去他那富有创造力的灵魂——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发起大清洗期间,作曲家亲眼目睹几位亲密的同事被逮捕乃至迫害致死——于是,他决定向他自己以及他看到的世界保持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