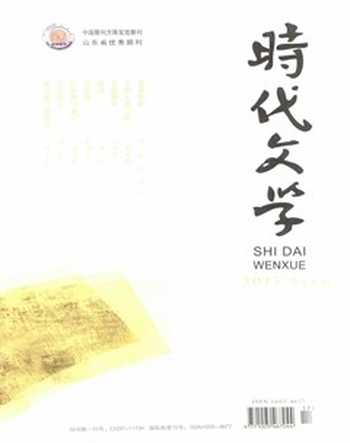半坡春早
向本贵
一
三月的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身子,让人浑身发软,心里还有一种痒酥酥的感觉。水田旁边的林子已经泛起了新绿。两只喜鹊蹲在枝桠上它们刚刚垒好的新家里,身首相偎,一边说着悄悄话,一边恩恩爱爱地做着只有春天里才做的事儿。李玉年看它们的时候神情有些发呆,后来眼泪就出来了。
山风里缠绵着一缕花的芬芳,沁人心脾。李玉年朝旁边的山坡看去,一丛刺玫瑰在春阳下开得正艳,一只蝴蝶探头探脑地在花丛上面飞来飞去。李玉年真想去摘一朵花儿戴在头上,想一想,她又没有去摘。半垭村的人们都说她自己就是一朵开得正艳的花儿哩。这么想的时候,她就看了一眼正在耙田的男人田长松。田长松却没有看她,他当然不知道女人现在的心理活动,更不知道她在默默地掉眼泪。从他嘴里传出一声紧着一声地吆喝。水田再耙一遍,就可以插秧了。只是借来的一头公牛却不怎么听使唤,甚至还有些消极怠工。它的心思早就跑到下边田里那头母牛身上去了。在下边田里做活的是村里张大全。张大全昨天晚上来到李玉年家对田长松说,再不能在家里待了,得打工去了。怎么说在城里打工比在家做阳春划算。
平时,半垭村在外面打工的人都是过年的时候风风火火赶回来,跟家里人吃顿团年饭,除夕守守岁,就又风风火火往城里赶,连挤车赶路的时间算一起,前前后后也不过十天八天。中国人一辈一辈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注重的就是那餐团年饭。不管吃的是什么,鸡鸭鱼肉也好,粗茶淡饭也好,全家人坐在一块吃就行。
田长松和张大全一起在广州一家厂子打工十多年了,每年的腊月二十八九往半垭赶,正月初一初二又得赶回广州去,不过在家住三两天。但他们愿意挤车,愿意赶路,愿意吃苦受累。他们有动力。他们才三十来岁,身强体壮,精力旺盛,想老婆想得发疯。往广州赶虽是依依不舍,也还是有动力的,他们想钱,钱是个好东西,谁都喜欢它。能改变家里贫穷的面貌,能让人腰杆挺直,说话硬气。但田长松和张大全挣钱却是另有打算,他们要送儿子读书,一直让儿子读到大学去,不能像他们那样,一辈子做农民工,做城市的过客,像是浮萍一样,无论漂到什么地方,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来。儿子读完大学就在城里工作,买房子,找老婆,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去年过年的时候,田长松和张大全都没有回来。不是因为火车票难买,火车票再难买他们也能想到办法,想老婆的动力能让他们排除一切困难的。厂里的领导说春节期间工人都不能回去的,留下来加班。厂里接到一个外商的订单,要在春节的时候把货赶出来。厂领导答应涨工资。年关将至,空气里飘散的都是过年的味儿。这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工们归家心切,涨不涨工资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厂领导就动用他的杀手锏,谁在这个时候回去,明年再不要来厂子上班了。工人们就不敢动了。上得好好的班,工资也不错,活儿也不是很累,被开除了,心有不甘。
加班加点,货是赶出来了,正月也将过去,厂里许多人还是陆陆续续往家里赶。父母盼着,老婆孩子盼着。这时,田长松和张大全却改变了主意,这个时候回去,还不如等两个月回去,也好帮着女人做做阳春;再说,过年不回去了,把过年的时间用来加班,就又可以挣一笔钱了。两个男人,肩头挑着一副担子,一家人的幸福,儿子日后的希望,都靠着他们的。即便是夜里想女人想得睡不着觉,想得发疯,都要让位于头等大事。
田长松说:“这次回来算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了,住了十来天。把秧苗插下去,是该走了。耽误十天半月就几百块钱啊。”
就是说,今天把田做好,明天插秧,后天男人就要去广州了。少说也要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九个多月,在李玉年看来,那是很长很长的日子,那是无边无际的等待,那是如饥似渴的憋忍,那是如火如荼的煎熬。要是按男人说的,明年过年的时候再回来,那就不是忍耐和煎熬了,那等于是要命。前年,田长松就隔了两年才回来的。自己把嘴唇都咬出血来,夜里才没有打开那扇让自己能陷入罪恶深渊的房门。
眼泪从李玉年好看的脸上一滴一滴流下来的时候,被三月的太阳一照,就有几个太阳落在她的脸上了。
这天晚上,李玉年杀了一只鸡。往常李玉年办了好菜总要给隔壁郭婆婆送点去的,今天她同样送了些鸡肉去给老人吃。郭婆婆七十多岁了,还上山做活儿养活自己,可怜啊。只是,李玉年没舍得把鸡腿给郭婆婆,她把两个鸡腿全让男人吃了。田长松想把鸡腿给她吃,怎么说鸡腿都应该女人吃的啊。她却不要,只是含情脉脉地看了男人一眼。田长松就不再推辞,把两条鸡腿全都吃了下去。一边吃,他似乎还一边在心里憋着劲儿。他知道,夜里的活儿不比白天耕田耙地轻松。
李玉年洗过,又给男人舀好水,就先上床了,她没有忘记随手拉灭吊在房梁上那只二十五瓦的灯泡。这是催促田长松上床的信号。他们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但李玉年仍然像个大姑娘似的,做那个事的时候是不让田长松开着灯的,她说那样真地羞死人了。
田长松匆匆洗了,爬上床,就被李玉年拥上了身子。田长松把吃下的两条鸡腿全都变成了劲儿。李玉年在田长松的身子下面却不像平时那样哼哼唧唧地发出甜蜜的叫唤,也一动不动。田长松知道她是在做打持久战的准备,他就觉得自己的压力更加大了。
其实,他跟她一样,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想她心里都想开坼了,想发疯了,可是不能因为想她就不打工了,就往家里跑吧。他和她的远大目标才刚刚踏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八岁的儿子读的镇里一所封闭式学校,封闭式学校当然比普通学校要好。按他们的说法,儿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读封闭式学校当然比一般学校的钱要多得多。他们说,用钱铺垫儿子的锦绣前程,值。钱从哪里来,当然靠自己这双手挣来。这是一个连环套。挣钱,就得舍弃身子下面这个漂亮得如美人鱼一样的身子,就得忍着、憋着,就得煎熬着。
田长松还常常想一个很傻的问题,这个事情为什么就不能透支呢,要是能透支的话,回来的这些日子里把今后几个月或是今后一年多时间的活都给做了,那样今后的日子就不用煎熬了啊。这个想法原本不应该从他这个高中辍学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脑壳里面冒出来。这是动物的生理本能,今天再做得精疲力尽,弹尽粮绝,过十天半个月,年轻的身子就又会膨胀起来。
不过,即便不能透支,他还是要连着做几次的。像平常那样,明天夜里还得躺在这个如锦缎一般柔软的身子上面不能下来的。再汗爬水流,再气喘吁吁,再弹尽粮绝,都得坚持着。眼下,她就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不然她怎么连吭一声都不,她是要把甜蜜的叫唤和撕扯都放在后面,她知道怎么给身子上面这个男人鼓劲、加油。当然,那也是给她自己加油鼓劲啊。
田长松正在为自己没有力气坚持下去而懊恼的时候,李玉年却在下面开口说话了:“我想好了,今年你不能去打工的。”
这是田长松没有想到的。这么多年来,他在去打工的先天夜里,李玉年总是搂着他说:“你放心打工去吧,我会照顾好我们宝儿的。”过后,就依在他的胸口跟他算起账来。她算的是两笔账,一笔是他在城里打工挣钱的账;一笔是她在家插田种地喂猪养鸡卖钱的账。算来算去,等到儿子跨进大学门的时候,儿子读书的钱他们已经准备足够了。不过,他们仍然不能有半点松懈,挣的钱还是要存着的。怎么说儿子大学毕业之后,还向爸爸妈妈伸手请求一点支援的话,他们还能拿出十万八万资助儿子的啊。
小两口的话题围绕着儿子打转,但小两口的行动却总是想把他们骨子里想的那个事给对方多透支一些。
今天有点反常,李玉年怎么不让自己打工去了。田长松说:“在家种田养鸡喂猪挣不到那么多钱的。”
李玉年不再说话,泪水却是像泉水一样从眼里溢出来,把田长松的胸口都洇湿了。田长松从李玉年的身子上面滚下来,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哄她说:“我们再坚持几年,把儿子读大学的钱挣够,我就不出去打工了,陪着你在家种田,养猪喂鸡。”
李玉年不说话,只是哭。田长松不知所措,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劝慰她了。这时,李玉年却又把他拥上了身子。
女人这么一哭,田长松心里特别的不好受。不过,现在他就知道女人说的不过是一时撒娇的话,并不是真正不让他出去打工了。他得赶紧调整情绪,让女人高兴才是。
这天早晨,李玉年起来得很早,她说:“今天星期六,我去把宝儿接回来。你明天出去打工,今天就别做活去了,在家陪陪儿子吧,不然,这一年我们宝儿不知道要叨念多少次爸爸的。”
田长松说:“昨天把田做好了,今天刚好一天的活儿。把秧苗插下去,我出去打工才放心啊。”
“我过两天插不就行了嘛。这么多年你不在家,插秧割谷还不都是我一个人。”李玉年是心疼男人,昨天晚上他没得睡觉,白天做活哪有精神。
吃过早饭,田长松还是没有休息,插秧去了,他也心疼女人啊。李玉年也就不去学校接儿子了,说:“那我还是跟你一块去插秧吧。打个电话给学校,说我下午去接宝儿。”
田长松说:“封闭式学校就是好,星期六星期天不回来也不用担心,有老师管着。”
两个人插秧的时候,居然都是呵欠连连。李玉年看看田长松,嗔他说:“今天晚上可不能那样了,明天上午要坐半天汽车,中午坐火车,后天早晨才能到广州。”
田长松这时却想着昨天晚上她不让自己去打工的话,说:“要不,我打几个月工,就回来一趟。”
李玉年说:“那还不如不去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车站了。”
田长松就不做声了,心想再要提起这个话题,只怕明天就走不成了。看了一眼下面水田里正在插秧的张大全,问道:“大全,明天去广州,没有变化吧?”
张大全没说话,他女人刘如卉却是抢着说:“我就怀疑你们在外面有什么名堂,说起打工,那个高兴,恨不得马上就走。”
田长松说:“如卉你这个话说得太没良心,你以为我们想出去打工呀,我和大全除了白天做活儿没机会说话,夜里说的就是你们。”
刘如卉问:“说我们什么了?”
田长松说:“还用问吗,从头说到脚,从上说到下,从里说到外,越说越睡不着觉。”
刘如卉说:“我不信。”
张大全说:“信不信由你。我们的确是这样的。”张大全问李玉年,“你怎么没接你家宝儿去。”
李玉年抬起头来的时候,田长松发现她的脸上全是泪水,心里不由一惊,对张大全说:“她说下午去接宝儿。”
张大全说:“你要是对我娘说一声,我娘就把宝儿一块带回来。”
刘如卉问李玉年:“明天他们要走了,你给长松哥办的什么好吃的啊?”
李玉年没抬头,反问刘如卉道:“你办的什么好吃的?”
刘如卉说:“杀鸡,两条鸡腿全给他吃了,晚上还是要死不活的样子,消极怠工,你说气人不气人。”
刘如卉这话说得太露骨,李玉年的脸早就红到耳根去了。李玉年是个很腼腆的女人,她哪敢像刘如卉这样张张扬扬把两个人夜里做的事情说出来。
这时,刘如卉又说话了,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昨天办的什么好吃的呢。”
李玉年说:“还不就是那些菜。好菜要留给我们家宝儿吃的啊。”李玉年心里却在想,今天还是要杀只鸡的,不过,今天的两只鸡腿他只能吃一只,儿子也要吃一只的。
二
李玉年和田长松是一对好夫妻,这是半垭村人公认的。李玉年长得漂亮,还勤劳,贤惠,在半垭村有口皆碑;田长松劳力好,会攒钱,心疼老婆,这也是半垭村人公认的。
李玉年和田长松从小一块长大,按书上的话说,叫做青梅竹马。两人一块读小学的时候,还坐一条凳子,共一张桌子呢。虽然两人有时也在桌子上划“三八线”,却是友谊多于矛盾。有时两人从家里带了好吃的,还悄悄送给对方吃。做游戏扮演小夫妻,是一定少不了他们俩的。后来慢慢长大了,知道害羞了,他们才不敢像儿时那样过于亲密。那时,俩人读书的成绩也特别的好,从小学到高中,一名二名都非他们俩莫属,于是他们的眼前铺起了一条斑斓的五彩之路,读大学,到城里去工作,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老师也说,要让他们俩为学校争口气,考重点大学。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两人美好的愿望结果都成了挂在天边的彩虹。开始是李玉年因为父亲去世辍学,后来田长松也因为母亲生病辍学了。农村的孩子辍学之后,是说不上再有走进学校去的机会的,两人离大学的门也就一步的距离。十八九岁,两人就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那时,他们都在广州打工,他们都没有忘记对方,有时休息,两人会通通电话,或是到对方的厂子看望对方。后来,田长松干脆就到李玉年的厂子打工去了。他们在厂子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就那样同居了。他们划算着怎么才能少用钱,除了给家里寄钱,还能余下一点钱来。几年之后,他们结婚了。所谓结婚,就是有了一张贴着两人半身照片的结婚证,没有办酒席,甚至连一张结婚彩照都没有拍。那时,李玉年的母亲也已去世,李玉年打工的钱主要是给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弟弟读书。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李玉年才算真正卸去了肩上的负担。
按说,他们的日子应该会好起来了,孩子由田长松的母亲带着,俩人一心一意打工挣钱就是,日后宝儿读书上大学都不愁的。不料,这个时候田长松的母亲却出了事,给猪喂食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居然把腰脊骨摔断了,再也起不来了,这不应了农村人说的那句话嘛,人背时,喝水也能咽死人啊。提着猪潲桶过门坎,摔倒在地就成瘫子了。田长松的父亲去世早,田长松是母亲含辛茹苦养大的。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儿子那个心疼啊。李玉年说:“我回去侍候母亲,带孩子,把田种上,把地种上,再喂养一头猪,比在外面打工差不到哪里去。”
那几年,李玉年忙得两脚不沾地,要给儿子和婆婆做饭洗衣服,要给婆婆洗澡换裤子,水田和旱地也都种上了,还喂养了一头猪和一群鸡。因为这,李玉年在半垭村争得了好名声,田长松的母亲死的时候握着她的手断断续续说:“玉年,你就是我的女儿啊。”
婆婆去世,李玉年的活儿就少了许多,心里的那种负担也没有了。这时,儿子也进了镇上一所封闭式学校。按半垭村人的说法,先苦后甜。李玉年也觉得这话一点都没错,好看的脸上那笑都变得灿烂了。
只是,李玉年脸上的笑容虽然常在,心里的那种幸福感却慢慢就变了味儿,中间夹杂着苦涩,杂夹着无奈,这种苦涩和无奈还不能在脸上流露出来。李玉年不是白天做活儿苦,她是因为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苦恼。睡不着,就胡思乱想,内心深处的那种饥渴和冲动怎么都无法排解。她只能把和男人在一起的一次次的美妙和甜蜜用来回味和咀嚼了,只能给田长松打电话了,她知道田长松也想她,每次在电话里她真地想告诉他,她想他心肝都想开坼了,可是,这个话她不敢说出口,从电话里传过来的叹息声,她就知道他比她想得还要厉害。她是知道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在城里所做的一些出格的事情的。天黑下来之后,城里那些黑暗的小街小巷里就会钻出来一些年轻女人,这些年轻女人专门靠做那个事情讨吃,她们的对象就是那些远离家乡,远离老婆的年轻农民工。李玉年就又不敢多打电话了。
李玉年甚至想,或许那时婆婆就躺在隔壁的房里,现在隔壁房里没有躺着婆婆了,心里的那个冲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心里茁壮成长了。
这个时候,李玉年就会想起一些白天听到的闲言碎语。刘如卉跟赵前生睡觉了,刘如卉跟伍明清有一腿。刘如卉跟赵前生睡觉她不相信,跟伍明清有一腿却是有可能的。
半垭村的人们都说,半垭村李玉年长得第一漂亮,刘如卉长得第二漂亮,长得第二漂亮的女人却跟一个和自己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人睡觉,实在是不可想象。但伍明清有他的优势,他是村主任,在半垭村算得是最有权力的人,况且伍明清在半垭村的口碑还不错,群众的好处能争的他一定会去乡政府争来,村里的事情该他管的他一定会管。刘如卉也许就是想到了这一点,跟伍明清睡觉,解决了饥渴,还能得到好处。
说刘如卉跟赵前生睡觉,只有鬼才相信。赵前生人老实,还肯帮助人,年纪也不过三十多岁,这是他的优势,但他是个残疾人,左脚比右脚短了三寸,走路那样子实在太难看,身子一歪一歪,头像鸡啄米一样。赵前生找不到老婆,打单身,就因为他是个跛子。没有去城里打工,也因为他是个跛子,哪有厂子会要他。跟他睡觉,还真的不知道那只短了一截的脚是怎么安排的。
这天夜里,李玉年一直要田长松趴在自己的身子上面,紧紧地搂着他,像是担心他跑掉似的。天刚亮的时候,张大全在外面叫田长松。张大全的话说得太露骨:“长松,一个晚上还没喂饱呀,六点的中巴车,赶不上,就得再耽误一天。”
田长松想起来,李玉年却是不肯松手:“我不让你去打工。”这个话李玉年昨天夜里又开始说了。现在,李玉年是带着哭腔说这个话的。
田长松却是没有半点犹豫,说:“不去打工,我们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田长松觉得这次回来,女人有些异样,一时不让他去打工,一时又叫他去打工,他真地有点摸不透她为什么要这样了。
张大全在外面叫第二次的时候,田长松就不管不顾地把李玉年的手掰开,去那边房里看了看还在熟睡的儿子,就匆匆地走了。
李玉年没有起来,就在田长松走出门的时候,她却是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长松,我不让你走的啊。”
田长松不由一怔,脚步也就停了下来,只是才停了片刻,他就匆匆地出门去了。
李玉年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李玉年有些发呆,饭也不想做,猪呀鸡呀也不想喂,她就那样呆呆地坐在门前,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远方。远方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李玉年知道一条公路在群山中左缠右绕地翻过去,就到了县城,再走几个小时,就到市里了,一条铁路线从那里过,田长松和张大全是从那里坐火车去广州的。
这时,刘如卉从禾场外面走进来,老远就笑着说:“玉年姐,长松走的时候把你的魂也带走了呀。”
刘如卉其实比李玉年还大一岁,张大全跟田长松同年,比田长松小月份,她是依着男人才叫李玉年姐的。她一脸的笑样,精神也特别得好,看不出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劳累的痕迹,也看不出男人走后的依恋之色。
刘如卉却是发现了情况,说:“玉年姐,你拿个镜子照照自己吧,昨天夜里没让长松哥下身子呀,眼睛周围一个大大的黑圈,脸也像是打了蜡一样。”
李玉年苦笑道:“老鸦别笑猪嘴黑。昨天夜里你就没有做几次。”
“做几次就成你这样了?”
李玉年不再跟她说这些,她问刘如卉:“大全说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才走,就想到什么时候回来了。我才不问他呢。过年的时候买不到车票,就明年三月的时候回来,那时候回来还能帮着做些重活儿。”刘如卉过后说,“秧苗插下去了,当紧的活儿也让他们给做了,多好。走,我们去乡场玩玩去,死鬼回来的这些日子,连乡场都没去了。”
李玉年说:“我家宝儿还在睡觉呢。”
刘如卉说:“把他的饭做好,他起床之后自己吃了就去我家跟我儿子一块玩,一会儿学校的车要来接他们的。”
李玉年说:“你回去,我一会儿去你家吧。”
这样说过,李玉年就匆匆把儿子的饭办好,把儿子叫了起来。宝儿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李玉年说:“你爸爸打工去了,给你挣钱日后好读大学,你要认真读书啊。”
宝儿听说爸爸已经走了,原本想哭的,后来又不哭了,说:“这个话你和我爸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我肯定要努力读书的啊。我们老师也说,不努力读书,日后就出去打工,做苦活、累活,脏累,钱还挣得少。”八岁的宝儿说话居然也像大人的口气了。
李玉年说:“我儿子懂事了就好。”看着儿子吃饱饭,把儿子的衣服收拾好,用一个包装着,带着儿子去了刘如卉家里。
刘如卉眼睁睁地站在自家门口等着她的。李玉年说:“你经常去乡场上逛是什么意思啊?”
“把乡政府那些干部给眼馋死,让他们跟在屁股后面打转转。”
李玉年也是听到过乡干部一些闲言闲语的,说哪个乡干部跟乡场上哪个漂亮女人关系不一般。还说谁谁穿的漂亮衣服就是乡干部给买的。说:“你就那么有信心啊?”
刘如卉一脸无奈地说:“说的玩笑话,他们哪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女人,三十岁,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老女人了,乡场上多少摆摊做生意的年轻漂亮的女人,还不像我们做农活晒得像个黑雷公,还一身的汗臭,人家整天不晒太阳不淋雨,身上洒的香水熏得人头晕。”
两人说话的时候,刘如卉的婆婆从那边屋里走出来。刘如卉的婆婆跟刘如卉的关系不好,快七十岁了,却不愿意跟刘如卉一块过,自己在一边办饭吃。却是把孙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孙子回来,也不让他跟妈睡,要孙子跟自己睡,平时去学校接送孙子,也不让刘如卉去,她自己去。刘如卉懒得跟老人争,你这样,我才省心呢。
李玉年嘴边的话就又咽了回去,对老人说:“校车一会儿就到的吧,我也送我家宝儿去学校。”
老人说:“你要有事你就去,我把他们一并送到学校去就是了。”
刘如卉拉着李玉年的手说:“我们走,他们才不要我们送呢。”
李玉年说:“我们坐便车去乡场,不是更快吗。”
李玉年和刘如卉来到乡场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今天不是赶场的日子,又是农忙的季节,来乡场买东西的人并不多,一个接着一个的店面和那些地摊都十分的冷清。
刘如卉和李玉年东瞧瞧,西看看,却不想买什么,那些摊主们开始还叫着喊着,后来也就懒得答理她们了。
“你们怎么来了?”
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那边店子传过来。抬起头,是伍明清站在那边店子里对着她们笑。刘如卉拉着李玉年的手就走了过去。
伍明清问:“长松和大全打工去了?”
李玉年没有回答他的话,刘如卉却是问他道:“你来乡场做什么?”
伍明清说:“在乡政府开了半天会,准备买点农药化肥带回去。”
刘如卉说:“秧插完了,他们打工去了,我们也要歇歇气啊。伍主任,我们不经常来乡场的,来了也不一定能碰上你,你得请我们的客。”
伍明清似乎很乐意请客,说:“好啊,你们说要吃什么,你们只管吃,我掏钱就是了。”
刘如卉说:“你就知道乡场上没有山珍海味我们吃,最多也就吃碗猪脚粉。”
伍明清笑道:“这可怪不得我。”
刘如卉说:“我们不吃猪脚粉,我们去山妹子酒家点菜,不吃一百两百不出来。”说着就要往山妹子酒家去。
李玉年说:“我没饿,什么都不吃。”
伍明清却是不管不顾地扯着李玉年的胳膊往山妹子酒家拖,说:“别客气,我们一块去吃。”
李玉年生气地说:“大街上,拉拉扯扯做什么。”
伍明清只得把手松开,有些尴尬地说:“我有话要对你们说,你就不愿意听了?”
刘如卉问道:“刚才乡政府领导说什么了,是不是又有什么补贴下来了啊。”
这些年,国家对农民的补贴实在多,一级一级放下来,放到村主任的手里,就算是放到了头,村主任再往下发,就是直接受益的农民了。别看村主任不是个官,手里握着这些东西,就能得到很多的好处,占到很多的便宜。伍明清有几分得意地说:“肯定啊,李玉年你就不想听了。”
李玉年就不做声了,跟着全明清来到山妹子酒家。伍明清说:“要吃什么,你们自己点,我结账。”
刘如卉说:“真要狠狠地放你一次血,我还是有些不忍心。”问李玉年,“你说,吃点什么?”
李玉年说:“我说了,我不饿,什么都吃不下。”
刘如卉就不再问她了,自作主张地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过后对伍明清道:“这个样子,没有放你的血吧。有什么好事快对我们说,还卖什么关子。”
伍明清说:“国家又拨钱下来了,造林,按棵算,造下去有钱,年年培育有钱,林子长大了,卖木材的钱还归自已。”
刘如卉对这个好消息并不感兴趣:“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呢。造林,我们造在什么地方啊。”
伍明清一脸坏笑地说:“你们不都有一片山弯吗,土地肥沃,林子造下去长得就快……”
没等伍明清把后面的话说出来,李玉年站起身就走了。她真的有些脸红,伍明清跟她们的父亲差不多大的年纪,这样的玩笑,他也开得出来。
也许,李玉年这一走,正合他们的意呢,刘如卉没有追出来,伍明清也没有叫她回去,两个人坐那里头对着头说起悄悄话来了。
李玉年觉得来乡场一点意思都没有,还白白地耽误了半天。三月里,草鞭落地都要生根发芽,得赶紧回家做点事情去。
三
这天晚上,李玉年睡了一个好觉,天黑就上床了,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自己都觉得好笑,做那个事,其实也是很累人的啊。
吃过早饭,李玉年去后山坡看稻田里的水。李玉年觉得男人三月回来还真有三月回来的好处,以前到了犁田插秧的时候,她就着急,没有牛,要借;没有人犁田,要请。借牛请人都麻烦,春耕大忙的季节,都忙,再说男人们大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男人就那么几个,除了伍明清,就是老人和赵前生这样的残疾人了。
秧苗插下去了,接下来的活儿就轻松了,管管水,杀杀虫,施施肥,这些活儿女人都能做。
“怎么,昨天插下去的禾苗,今天就来看水了呀。”是伍明清,他扛着一把锄,站在山沟那边的水田旁边。那不是他家的水田,但他是村主任,到处看看,检查检查,是他的工作。说不定什么时候乡政府就会打电话来,问他半垭村的春耕生产进度如何,又抛荒了多少田地啊,他都要能答得上来。这些都是伍明清自己开群众大会时说的,他说他这个村主任拿的钱不多,管的事却不少,操的心也不少。
李玉年不想跟他说话,接上腔他就没完没了了。伍明清却不管这些,一边往这边走,一边说:“我刚才在你的水田边看过了,你那水田得放点水进去,就把水沟旁边的一股山泉水往你禾田里放了。水浅了,刚插下去的禾苗难得起身。”
李玉年果然看见水沟旁边新挖了一道小水沟,一股泉水正往自己禾田里流。她有些感动。心想,他百样都好,村里的工作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就是有点打年轻女人的主意,趁着人家男人在外面打工一年半载不回来,就占别人的便宜,不然他是会受到大家的敬重的,自己对他也会高看几分的。
李玉年往回走的时候,伍明清却赶了上来,笑着说:“长松这一走,又要几个月才能回来啊。”
李玉年知道他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心不由怦怦跳起来,脚步也就加快了许多。伍明清说:“过几天来你家,你可不能又不肯开门啊。”
李玉年回头瞪了他一眼,说:“你要脸不。”
伍明清却是笑着说:“要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李玉年说:“也不想想你有多大年纪了。”
“怎么,你嫌我老了。”
李玉年再没有跟他说话,逃也似地走了。
回到家,刘如卉却来了。刘如卉今天穿了一件新衣裳,老远就问李玉年:“看看我这件衣裳漂亮不漂亮?”
李玉年看了一眼,还真的很漂亮,问道:“大全给你买的?”
“他知道给我买衣服?他只知道要我的身子。”
李玉年说:“他不会给你买衣服,给你钱你自己买不一样的吗。说起来还是大全给你买的啊。”
刘如卉笑说:“昨天你要是不走,你也有这样一件漂亮衣服的。”
李玉年就知道她穿的衣服是谁买的了,说:“我不喜欢穿这样的衣服。”
“自己可以挑啊,喜欢哪件挑哪件,他付钱不就是了。”
李玉年道:“乡场才多大,才多少店子,谁不认得谁,你就不怕别人说你?”
“这样的事情算什么事情啊。你没听说吧,乡里领导给一些姑娘买的衣服那才叫衣服,几百块钱一件。我们没她们那样的本钱,得不到那样的好衣服穿,只有穿这样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了。”
李玉年不想跟她说这些,问道:“还没吃中午饭吧。我去办饭,就在我家里吃。”李玉年知道刘如卉的婆婆不会给刘如卉做饭,她自己却有点懒,儿子不回来,她一天就做一次饭。
刘如卉跟着她往灶屋走,说:“对你说个话,你可不能说出去。”
李玉年看见她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不知道她要说什么话,看着她。刘如卉说:“几天前的晚上,孙小环去敲邹如娜的门,碰上了伍明清,伍明清狠狠地扇了孙小环几个耳光,伍明清还去乡派出所报了案,把孙小环弄去关了三天。我一直就想不通,孙小环谁都不怕,就怕伍明清,在伍明清面前就像老鼠见着猫。真是一物降一物。也不知道伍明清是怎么把孙小环给降住的。”
李玉年浑身不由打了个寒颤,她说:“孙小环怎么会去敲邹如娜的房门?”
“他怎么不会去敲她的房门?他还敲过我的房门呢。不过,跟他睡觉可没有想头,那只烂眼坑里流出的眼泪又臭又腥,熏得人死。赔了身子还要贴饭菜。他说他睡累了,要给他弄好的吃补身子,世上哪有这样无赖的男人。他就没有敲过你的门?”
李玉年连连摇头说:“没有。”心里却想,一个刚刚劳改回来的劳改释放犯,夜里也敢敲别的女人的门呀。
刘如卉道:“这就怪了,他怎么不来打你的主意?等着吧,他肯定会来的。”
李玉年说:“你可别吓我。”
刘如卉说:“吓你做什么,一杆枪,还是劳改释放犯,破罐子破摔,谁的门他不敢敲。”
这天夜里,李玉年躺在床上许久没有睡着,后来她觉得自已的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动弹不得,她哭啊,叫啊,挣扎啊,醒来,是一个梦,浑身的汗水像是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李玉年就更加地睡不着了,脑壳里面老是晃动着那个被叫做一杆枪的男人。他是孙小环。孙小环三十来岁,半垭村人,有一只眼睛瞎了,瞎的这只眼睛凹陷下去很深,像一个铜球坑,特别的吓人。这只瞎眼还有一个毛病,只要他一激动,就流出一种黄黄的稠稠的水,又腥又臭。
孙小环的这只瞎眼是他自己给弄瞎的。孙小环的父母去世早,他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从小没有管教好,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爷爷死后,生活没有了着落,又不认真做农活,也不去城里打工,整天在乡场上跟几个年轻人鬼混。一次,跟几个年轻人干仗,却输了,不服气,回来关着门在家做火枪。他想把火枪做成之后就去报仇。那样,乡场上就再也不会有人敢跟他说不了。还别说,他的火枪还真地做成功了,一根指头粗的无缝钢管套在一个木头做成的枪盒子里面,无缝钢管下面套着一个用铁丝做成的扳机,扳机上缠的是橡皮筋,点火用的是乡场上能卖到的那种纸炮子,一打一个响。只是,孙小环在枪管里灌了些火药之后,扣动扳机的时候,纸炮子响了,枪管里的火药却没有点着。孙小环就把枪管对着自己的左眼,他想看看什么原因枪管里面的火药没点着呢。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响,一股火焰从枪管里喷出来,他的那只左眼球就不见了,眼坑里却是一坑的血浆。孙小环用手握着那只没有眼珠的眼坑,却是庆幸枪管里只放了些火药,没有放铁弹儿,不然,就不仅仅是眼珠变成了血浆,整个脑壳都变成一摊血浆了。
当时正是中午,村里人做活回来在家吃中午饭,孙小环的邻居听到隔壁屋里的声响,过来一看,吓得可不轻,连忙去叫伍明清。伍明清和几个人把孙小环送到乡医院住了半个月,那眼就成一杆枪了。伍明清觉得这家伙不给治一治还真不行,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坏事来,去乡派出所对姚所长说了孙小环造枪的事。姚所长一听也吓得不行,私自制造枪支,还了得,犯国法啊,连忙向上面汇报,就把孙小环送到西湖农场去了。
前不久,孙小环刑满被放了出来,居然没有半点改变,还是好吃懒做,还是偷鸡摸狗,居然夜里还敲女人的门。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半垭村的人们更加地怕他了。那只瞎眼像一口深井,又像一个弹洞,还像一个藏着罪恶的深坑,让人见了心里发毛。孙小环没有出去打工,也不做阳春,吃的什么,人们不知道,白天夜里他都干了些什么,人们也不知道。用伍明清的话说,孙小环那样的人,最好的去处,应该还是劳改农场。也许,就因为担心再去劳改农场,孙小环就怕伍明清一个人。伍明清跟孙小环约法三章:你孙小环干什么勾当我伍明清都不会管,但你孙小环不能在半垭村干什么,我是半垭村的村主任,我要保半垭村一方的平安和谐。你要敢在半垭村干什么,我就对你不客气。伍明清碰着孙小环夜里敲女人的房门,那还了得,当然是会出手重重地抽他的耳光的。
李玉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孙小环来。孙小环回来这么多日子,李玉年也没有看到孙小环几次,有一次看见了,李玉年就远远地避开了,实在说,她至今还不知道孙小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天天刚亮,李玉年就起床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起床,呆呆地坐在那里,直到天亮明白,她才生火做饭。
吃过饭,李玉年就上山做活儿去了,家里还有一片地没有种上,她想种点黄豆,过年才有豆腐吃。田长松最喜欢吃豆腐了,他曾对她说过,要是把豆腐和猪肉摆在面前,问他喜欢吃什么,他会说他喜欢吃豆腐。
山地就在屋子的后面,李玉年挖了一个上午的地,整好,太阳偏西的时候开始下种,天黑的时候才种完,回到家的时候,累得腰酸背疼,但李玉年高兴。心想今天晚上会睡个好觉了。
吃晚饭的时候,邻居郭婆婆来家里要她给她穿针。郭婆婆手里拿着一件破烂的衣服,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针和一根线。实在说,平时李玉年只觉得郭婆婆可怜,却不怎么注意这位老人,有时办了好菜,给老人送点去,却不愿意听老人说的那千恩万谢的话,更不愿意看到老人眼坑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泪水。
抬头看了老人一眼,李玉年的心里不由生出许多的同情来。饭也不吃了,接过老人手里的针线,穿上,又把老人的那件破衣服拿过来,慢慢地缝补。郭婆婆蹲在一旁,昏花的眼坑里又有浑浊的泪水流出来。李玉年想劝老人几句,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把衣服补好,从箱子里找了几件旧衣服给老人,说:“也不知道这些衣服你穿得穿不得。”
郭婆婆的眼泪更多了,说:“怎么穿不得,冬天不冷着就行。”
李玉年说:“要是能穿,我有空就再找点你穿。”
郭婆婆千恩万谢地走了。李玉年饭也不吃了,把门关上,一个人坐那里看电视。她不想睡觉,担心躺在床上胡乱地想这想那。
直到电视荧屏上出现了晚安两个字,李玉年才站起身准备进房去。就在这时,她突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不由吓了一跳,接着,她就镇静下来,她没有去开门,她知道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开门的,问道:“谁呀?”
外面的回答有些不耐烦:“你说我是谁。”
是伍明清的声音。李玉年说:“伍主任,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你开门,我对你说。”
李玉年说:“半夜了,有事明天说吧。”
“明天一早我要去乡政府汇报。”
“你去汇报村里的工作,与我有什么相干?”
“当然与你相干。要填一份表呢。”
“什么表,要我填啊?”
“插禾补助表。每亩插下的禾有三十块钱补助。”
李玉年知道填表不过是他想进来的由头,白天多长啊,怎么不来。她说:“我家那一亩水田插上禾了,你还给管过水呢。你要愿意,你就给我填上;你要不愿意,那三十钱我不要了。”
伍明清说:“国家关心农民,你不领情呀。”
李玉年说:“我当然感谢国家啊。”
伍明清说了一句什么,李玉年没有听清楚,她也不想听清楚他说什么,这个时候,他能说什么呢。伍明清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李玉年躺在床上,她又失眠了,她不知道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伍明清堵在门外,是好还是不好,但要自己像刘如卉那样,她还真的不得干,不说对不起男人,也对不起自己啊。二十多岁,长得漂漂亮亮的,怎么就和一个跟自已父亲一样大年纪的男人上床呢。
四
李玉年是掰着手指头算着日子的,开始的时候,那日子似乎还过得比较快,加上她又有意地找活儿做,整天在劳累中度过,夜里睡得还算踏实。过了四月,又过了五月,李玉年就觉得这日子是越来越慢了,白天太阳落下得慢,夜里就更长了,眼睛盯着那扇窗,那扇窗总是一片迷蒙,怎么都不见那一缕曙光从窗口透进来。
以前使用的办法也失灵了,白天再累,夜里还是睡不着,躺在床上像是翻烧饼。就是睡着了,做的梦还是那个事,跟田长松要死要活的,醒来的时候,浑身大汗淋漓。李玉年特别的烦恼,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了什么病了。于是,她有意无意地问村里几个跟她一样年纪,留在家里带孩子侍候老人的女人。不问则罢,一问可把她吓了一跳,这几个女人中间,虽然也有跟她一样,把身子看得重,守得紧的;其余的几个,早就没有把身子当回事了,她们说,那样还不如这样,重活累活,还有人帮着做,大小事情,还有个照应呢。李玉年心想,这是什么事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是决不会这样的。忍吧,憋吧,熬吧,长松总会回来的啊。
六月,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插下去的稻禾青葱葱的一片。后来,就开始打苞了。这个时候,水田里是不能没水的。按农民的说法,叫做养苞。李玉年去自己那片水田也就勤快了许多。那天,李玉年来到自己水田边的时候,她看见伍明清正在给刘如卉水田里灌水,手里拿着一把锄,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
禾苗插下去之后,刘如卉就再没来自己田边看过禾苗。施肥呀,杀虫呀,中耕呀,这些苦活累活是赵前生帮着做的,管水这样轻松活儿则是伍明清帮着做的。李玉年常常想,这个刘如卉,一块骨头,哄着几只狗摇头摆尾啊。
伍明清说:“玉年,我原本是想给你田里也放一些水的,只是,上面水坝的石堤涨端午水的时候被冲垮了,水坝里没水,山沟里的一丝泉水还不够灌如卉的禾田。”
水坝被山洪冲垮,李玉年早就知道,她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的,要是今年风调雨顺,水坝就不用修了。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啊。李玉年站在干涸了的水沟旁,看着从山脚石头缝里淌下的一丝山泉水,汩汩地流进了刘如卉的水田里。只是,这一丝山泉水在六月的烈日下也无济于事,刘如卉的水田其实也干了的。李玉年还是相信伍明清的话的,要是水沟里有水,他也会给自己水田里放水的,禾苗刚插下那阵,他不是给自己水田里放过水的嘛。
“这条水坝,除了你们两家,还有郭婆婆的水田也用水坝的水,你们三家得赶紧想办法把水坝修一修,这天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呀。”
李玉年心想,郭婆婆七十多岁了,怎么好叫她来修水坝,就是把她叫来,她也做不起这样的重活儿。
伍明清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说:“这几天我要去乡政府开会,不然我就来帮着砌一下水坝,怎么说我这个做村主任的不能看着大家的水田减产。”
李玉年说:“我去对如卉说,石头我们自己抬,你只抽时间帮着砌一下石堤,好吗?”这是这么多年来,李玉年对伍明清说的一句求他的话。
伍明清说:“我说了,我要去乡政府开会,三天会开完,就来不及了。”
李玉年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再没有说话,匆匆找刘如卉去了。
刘如卉坐在禾场前的梨树下乘凉,一副十分悠闲的样子,也不知道她心里有什么高兴事,嘴里还哼着歌子。她婆婆则在那边屋里剁猪菜,咚咚的声响似乎是在跟这边的儿媳妇唱对台戏一般。
李玉年说:“如卉你真悠闲啊,我们两家的稻禾快旱死了。”
刘如卉说:“禾苗插下去之后,我就没去田边了,你刚才到那里看了?”
“涨端午水的时候,水坝被冲垮了你也不知道?”
“听说了。”刘如卉看着李玉年,问道,“长松哥打电话来了吗?”
“没有。大全打电话来了?”
“那个死鬼,出去三个多月,才打过两个电话回来,我就怀疑他在外面找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不然他怎么不把我当回事。”
李玉年就不做声了,心里想,这么多年来,也都是自己给长松打电话,她要不给他打电话,他是不会打电话回来的,他说可惜钱。她说:“别说他们了,我们说当紧的事,水田干了,你说怎么办?”
“砌水坝啊,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们不会砌堤啊。”
“叫他们砌吧。”
“你说谁?伍主任说他这几天要去乡里开会,几天才能回来。”
“那就叫赵前生砌。每天给他开八十块钱,他还不高兴死了。”
李玉年当然是心疼八十块钱一天这样高工钱的。可是,没有办法,工钱再高,也得请他来才行。她说:“石头还是我们自己抬吧,总能节约几个钱。”
刘如卉说:“抬石头的活儿多累,六月天,太阳又大,还不把皮给烤脱呀。再说,郭婆婆抬得起石头。”
李玉年笑她道:“看你,被谁娇惯成这样了啊。以前六月天就不做活了。”顿了顿,李玉年又说道,“郭婆婆就不要摊上一份了吧,可怜啊。她就半亩水田,坝修好了,让她放点水不就是了。”
刘如卉懒洋洋地说:“那好吧。什么时候开始啊。”
“水田干开坼了,不能等的。我们今天去抬些石头摆那里,明天叫赵前生去砌堤。”
刘如卉说:“还不如现在就叫赵前生一块去。他砌堤,我们抬石头。”
李玉年说:“这样当然更好。”
两人来到水田上面溪沟里的时候,赵前生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们的。他是刘如卉打电话叫来的。赵前生三十来岁,高高瘦瘦的个子,五官端端正正,说话也是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要不是因为左腿短了三寸,还真是个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小伙子。看着赵前生,李玉年就想起一件事情来。听说去年八月的一天晚上,村里两个女人不知道跟赵前生是怎么约定的,居然同时出现在村口那间米碾坊里,那天天气不好,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全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两个女人听到脚步声,就迫不及待地把对方紧紧地搂住了,直到发现对方的胸口有些不对,赵前生的胸口是平的,可对方的胸口却是鼓着丰厚的两坨。咬着对方耳朵的时候,才知道对方并不是赵前生,而是跟自己一样的长头发女人。两个女人连忙松开双手,就那样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吃苦的当然是赵前生,第二天两个女人把赵前生狠狠地抽了两巴掌。赵前生捂着火辣辣的脸,才知道她们是误会了自己,其实他并没有答应她们,是她们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别的什么,自己多情起来了,造成了误会。
看着赵前生,李玉年心里不由生出一种苦涩,跛子也成香馍馍了。说:“前生,要辛苦你几天的啊。”
赵前生不看李玉年,盯着刘如卉说:“你们把石头准备好,也就两天的活儿。”
刘如卉笑道:“你是想给我们节约钱吧。不过,我们每天只出得起八十块钱的。”
赵前生说:“给别人做活,每天收的一百,你们说八十就八十吧。”
李玉年不由一惊,村里没有男人,跛子做一天活居然要一百块钱一天呀。
刘如卉道:“这样说,你给我们多大的情了。玉年姐,我看这样吧,两天,我们各人给他六十块钱,再供他一餐饭。对郭婆婆说,她出四十块钱就是了。”
李玉年说:“她那四十块钱我出,我共计出一百,再供前生一餐饭。郭婆婆那个样子,怎么好开口向她要钱,坝修好了,她田里灌点水要什么紧。”
刘如卉笑说:“那阵村里选妇女主任的时候,怎么没让玉年姐做村妇女主任啊。秀玲选上妇女主任,没管村里的事,到城里打工一年都不回来几天的。”
李玉年说:“村里几个村干部,除了伍明清,谁还在家里,不都打工去了吗。”
刘如卉笑道:“不过,伍明清就希望他们都出去打工,他又做村主任又做村妇女主任。”
李玉年不想跟她说这些,母狗不摆尾,公狗不爬背。你不开门,他伍明清爬窗子进你的房去不成。
赵前生一只脚有毛病,手上的活儿,却是没有影响的,把李玉年和刘如卉抬来的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再填上土,溪沟里的水慢慢地就往上涨了。
下午的时候,刘如卉对李玉年说:“今天你给赵前生做饭,明天我给他做饭。”
李玉年说:“那我现在就回去做饭去了。”
刘如卉说:“人家帮我们砌堤,你要办好菜给他吃啊。还要多放点米,等会儿我懒得回去做饭了,一块来你家吃吧。你炒的菜好吃,却从来不叫我去吃饭的。”
李玉年说:“好,收工的时候你和前生一块去我家就是了。”
李玉年这天晚上认真办了一桌子饭菜,有腊肉,还杀了一只鸡,还炒了许多可口的菜,人家赵前生是给自己做活儿,再说刘如卉提出要来家里吃饭,不办好菜不好,人家会说自己小气。饭菜办好,赵前生和刘如卉还没回来,李玉年就用碗盛一些好菜送给隔壁郭婆婆,郭婆婆眼睛不怎么好,耳朵也有些背,看见李玉年端了好菜过来,眼泪就出来了,嘴里说:“玉年啊,你是好人,菩萨保佑你的啊。”
李玉年原本想对老人说说修水沟的事,想一想她又没有说,钱呀饭呀说了老人会怎么想,她哪来的钱给赵前生,她哪办得好饭菜让赵前生吃。
郭婆婆命苦,二十多岁男人就死了,带着一个几岁的儿子过日子,把泪水和着饭菜一块咽进肚子里。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成人,老人也该享福了吧,没想到儿子在外面打工时偷东西,案子还犯得大,劳改去了。老人的眼泪流尽,还得煎熬着把日子往下过啊。
现如今政策好,农民年满六十岁了每个月就有五十块钱。对于有钱人来说,五十块钱也就两包烟。困难人有那五十块钱却能活命。郭婆婆自己说,她今年七十五岁了,可她的那五十块钱却没有拿到,她还得种那半亩水田过日子。郭婆婆没有拿到那五十块钱的原因是她的年龄上出了问题,她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至今还不到六十岁。郭婆婆不识字,当时领户口本和身份证的时候也没有请别人看看年龄上是不是有错,当然更不会想到今后国家会给农民“发工资”。发工资这话是农民自己说的,他们高兴啊,他们感谢国家啊,国家居然也给满了六十岁的农民发工资啊。
郭婆婆的年龄往后写了二十年,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少写二十年的错在乡里还是在村里,伍明清去乡里找姚所长,又找民政委员,要他们改一改,他们说改年龄那是很难的,后来郭婆婆自己去乡里,他们看到这样一个勾腰驼背的女人才五十岁,年龄只怕是真地弄错了,答应改,却是一直没有改下来。因为这伍明清去乡里吵过几次架了,乡里工作人员说,吵也没有用,等吧。伍明清和郭婆婆心里都明白,这个等是遥遥无期的,田坪乡谁不知道郭婆婆的儿子是个大盗窃犯,那年抓她儿子的时候,姚所长还带着县公案局的人去她家里搜查过的呢。谁愿意把一个大盗窃犯母亲的事情放到心里去。
李玉年有时办了好菜,就会给老人送点去,她常常想,郭婆婆过得苦啊。有时,李玉年还想,郭婆婆二十多岁就没有了男人,她是怎么过来的啊。
天快黑的时候,赵前生和刘如卉才相邀着来到李玉年家。李玉年说:“如卉你这个监工也太厉害了吧,天不黑不收工。”
刘如卉不跟她说这些,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饭菜就不松开:“啊呀,玉年姐办了这么多好菜呀。”
李玉年说:“你说了,要办好的吃啊。”
“我没说要你杀鸡,也没说要喝酒。你看,鸡呀,腊肉呀,酒呀,过年也就这个样子。玉年姐,你真地很心疼前生的啊。”
这话让李玉年的脸不由就红了,说:“请人家做活,不办餐好吃的,怎么好意思。”她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你自己才更应该给他办好吃的啊。给赵前生倒了一杯酒,说,“前生哥,辛苦你了,喝杯酒,解解疲劳。”
刘如卉又嚷了起来:“怎么不给我倒酒?”
“你也要喝酒呀?”
“我怎么不能喝酒。前生哥,有好菜,我们俩把这瓶酒给干了。”
赵前生不说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夹了一块腊肉往嘴里塞。看来他真地是饿了。
刘如卉也就不说话了,一仰脖子,把一杯酒全倒进喉咙去了。
李玉年说:“如卉,这样喝酒不行,要醉的。”
“我就想醉一回。”刘如卉拿起瓶子自己把酒倒满,对赵前生说,“快喝,我好倒酒。”
赵前生只得把杯子里的酒喝干。李玉年见状,也就不说他们了,只是把好菜往他们碗里夹。
一餐饭吃到天黑一阵才放碗,一瓶酒还真地被刘如卉和赵前生给喝光了,刘如卉看样子是喝醉了,说话有些放肆,说:“前生哥,玉年姐办这么好吃的饭菜,你还要收她一百块钱呀。”
赵前生的脸有些发青,却不说话。
李玉年说:“不要你让我钱,讲好一百块钱,我这就给你。”这样说的时候,李玉年就从房里拿了几张票子给赵前生。
刘如卉抢过钱,从中抽出一张二十元的票子退给李玉年:“饭不能白吃,二十块一餐饭,前生你值。”过后就骂起张大全来了,“我家那个死鬼,出去打工他就像是过年,也不问问女人在家过的什么日子,钱不叫寄他就不寄回来,以为我在家就不要用钱了。前生,我的工钱要记账的啊,我没钱。”刘如卉这样说的时候居然就哭了起来,泪水成沟儿地流淌。
李玉年把那二十元钱拿在手里,趁着刘如卉不注意,又给了赵前生。没有料到,却让刘如卉看见了,她用手在脸上一抹,说:“玉年姐,我对你说,你别做起那个样子。把身子裹得紧紧地,谁都别想沾,留着让长松哥回来,我说你是何苦啊。”这样说过,就对赵前生说,“送我回去,我醉了。”
李玉年说:“他喝酒了,我送你。”
刘如卉说:“不要你送,你送我没有想头。”
李玉年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心想张大全的老娘就住在一个屋子里,你就不怕她对儿子说吗。
刘如卉这时已经把赵前生的手搂住了,对李玉年说:“你以为他是个跛子就不行了,除了走路不好看,干别的只怕你家长松哥都不如的。”
李玉年再没有说话,看着两人摇摇晃晃地走了,心里想,这个刘如卉,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第二天,李玉年早早就去了溪沟的水坝上。刘如卉没有来,赵前生却来了。赵前生看见李玉年,有些不怎么自然,李玉年说:“前生哥,你怎么不讨个嫂嫂,三十多岁了,年纪不饶人啊。”
赵前生叹了一口气,说:“谁愿意跟我?”
这些年,农村的女孩都往城里跑,进了城就不愿意回来了,长得漂亮一点的,找个城里的男人,年纪大也好,结过婚也好,都无所谓;找不到城里男人的,就找家里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农村小伙。田坪乡这样偏远落后的山区,女孩只有往外面跑的,没有女孩嫁进来的。许多的小伙就成单身汉了。半垭村这样的地方算得是田坪乡最穷的村,小伙子找女人就更难。有人算过,半垭村三十多岁的单身汉就有几十个,像赵前生这样的残疾人,找女人更是难上加难了。
李玉年就不再说话,一个人默默地扛石头。赵前生说:“你不用扛石头,累,等会儿我扛点石头把石堤往上再砌一点,水就进禾田里去了。”
李玉年有些感动,心想还是一个会心疼人的男人。
刘如卉来水坝的时候,已经半晌午了,她好像还没有睡醒,老远就说:“你们来得真早啊。”
赵前生说:“你就别做活了,在旁边休息,今天的活儿不多。”
刘如卉说:“也好。过一会儿就回去办饭,玉年姐,你今天去我家吃晚饭。”
李玉年说:“不去了,昨天晚上还剩了许多的菜,再不吃,就馊了。”
刘如卉就不再邀她了,坐了一会儿,果然就回去了。
赵前生对李玉年说:“你也回去算了,你们的要求不过就是田里有水吗,我把水赶到田里去就是。”
李玉年说:“我还是帮着做一会儿活,不能说给了你工钱,就让你累到天黑还收不了工吧。”
天气太热,李玉年做了一会儿活,已是满头大汗,赵前生再不让她做了,她就坐在旁边看着赵前生做活儿。赵前生做活儿踏实,劳力还真的不差。李玉年不由又旧话重提,说:“前生哥,你真地就这么过一辈子啊?”
李玉年的话里有话,但她没有说出来。赵前生何等聪明的人,说:“她又不是我一个人。”
李玉年说:“就是啊。”
赵前生再没有说话,勾着头认真地砌堤去了。李玉年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心想刘如卉的工钱是肯定不会给他的。这样的男人也可怜呢。
五
日子在半垭村那些独守空房的年轻女人的企盼和煎熬中,一天一天往下过着。那天,李玉年锄黄豆草回来,办了饭吃,天就黑了。半边月儿斜斜地挂在天上,把四周的山影变得黑魆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李玉年总觉得半垭村没有过去热闹了,到了夜里,村子就是一副寂寂封音的样子,几点昏暗的灯光从窗口透出来。就连狗也懒得叫了。李玉年就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的寂寞和压抑。
李玉年想去刘如卉家对她说说,明天一块到学校接儿子去。儿子要放暑假了。
刚走到刘如卉家门口,看见刘如卉提着一个保温盒往外走,李玉年就站住了,说:“到哪里去啊。”
刘如卉说:“给前生哥送点吃的去。”
李玉年说:“送什么好吃的?你还真地投入感情了呀,大全回来看你怎么办啊。”
刘如卉说:“什么感情不感情,前生哥起不来了。”
“病了?”
“被打了。”
“被谁打了?”
“伍明清打的。”
“什么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打的,你怎么知道。”
李玉年就不做声了,不用说,肯定是夜里两个男人撞一块了。
刘如卉匆匆就走了,李玉年问她:“明天接儿子去不?”
刘如卉说:“要办饭要做家务,还要给他送饭,哪有时间。”
“儿子放暑假了,也不去接一接。也好问问老师这一个学期的表现啊。”
刘如卉说:“我忘了对你说,我儿子放暑假不回来的。学校办了个预习班,学下学期的课程。别人的孩子学,我们的孩子也得学啊,不然,怎么赶得上班。”
李玉年问:“一个暑假要多少钱?”
刘如卉说:“再多的钱也要学。”
李玉年想问一下到底要多少钱啊,刘如卉已经走远了。李玉年就只有往回走了,心里想,明天多带点钱去,报个名,也让儿子读那个预习班吧。
回到家,坐了一阵,李玉年就睡了。天气热,电扇吹出的风也透着一股热气,李玉年把关着的窗子开了半扇,想让屋后面的山风吹进房来。
开始的时候,李玉年还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的,后来实在热得不行,她就把衣服脱了,只是穿着一条短裤。二十五瓦的灯泡挂在房梁上,灯光不是很亮,却是透着一种暧昧,李玉年就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身子上瞅。
以前,李玉年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自己的身子,她害羞。田长松平时总是说她的身子长得如何好,她就红着脸问他好在什么地方。田长松还真能说出很多的好来,皮肤白得像煮熟的鸡蛋膜儿,脚杆又长又直,奶子像棉花团,肚皮像是门前怡溪六月的水面……
李玉年当然是最喜欢听他说这些话的,但她没有去认真地想他说的这些话的真伪,她已经被一种幸福的浪潮覆盖。今天,她想起男人说的这些话,男人却不在身边,也就涌不起那种幸福的浪潮把自己淹没。借着迷蒙的灯光,她要好好看看自己的身子。
李玉年的脸不由得红了。她果然看到了一具美如玉雕的身子。她真地想不明白,一个从小吃苦受累的山野女子,一个过去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穿的山野女子,一个直到现在也没有用过什么护肤膏之类东西的山野女子,怎么就有这样一副冰清玉洁的身子啊。这时,她心里不由怦怦地跳了起来,她想起田长松每次跟她做那个事的时候的情景了。她跟田长松结婚快十年了,但他们做那个事的时候从来都是把灯关着的。好多次田长松要开着灯,她不让,她说那还不羞死人呀。田长松说看着你的身子,我就会激情万丈。李玉年嗔他说,没激情你就不要做那个事,开着灯,休想。不管他在身子上面怎么的拳打脚踢,她在下面怎么地享受着那种要死要活的甜蜜,都是在黑暗之中,让黑暗把他们的幸福和甜蜜悄悄地消失。现在,李玉年突发奇想,要是两个人在电灯下做那个事,该是一种什么样子。
突然,李玉年就想起刘如卉来,刘如卉不会像自己这样想男人的,张大全去也好回也好,她一点都不在意。张大全回来了,她接纳他,张大全去打工了,伍明清和赵前生会时不时地去她家里,现在孙小环回来了,去她家里的男人就又多了一个,她没有饥渴感,她被这些野男人宠着,爱着。有男人做活儿,有男人买衣服。可是,自己不会,也不能那样的。那样,还是一个女人嘛。
李玉年什么时候睡着的,她不知道,她只知道睡着之前她哭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她只知道眼泪像断线的珠儿,没完没了地流。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玉年觉得田长松回来了。田长松跟过去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她的身子。如果是晚上,那是没得说的,她也特别想做那个事,顺理成章,两个人躺在床上尽情地做就是了。要是在白天,就有点麻烦,虽说她也火急火燎的。可是,不行,儿子在家里。儿子不在家也不能做啊,要是来个人怎么办,不能说阳天白日的关着门在家里睡觉吧。
田长松却是不答应,软磨硬缠的。田长松那样子可怜啊,他想啊,他憋着的啊。作为女人,她得想办法让他满足才是。想什么办法?她依了他,但她提出一个要求,要快。像吃饭一样,狼吞虎咽,快餐。也就解解饥渴吧。晚上再慢慢享受。田长松当然会依着她,只要能沾她的身子就行。
今天也跟平时一样,田长松二话没说就把她压在身子下面了。李玉年当然也享受到了那种甜蜜,那种欢悦。她说:“你真好,知道我想你了。”
只是,田长松却不像平时那样,会说:“这一年来,我的心肝都开坼了。”他只是用嘴紧紧地把她的嘴堵住,像是不让她说话似的。
就在这时,李玉年突然闻到了一种刺鼻的腥臭味,哇地一声就呕吐起来。
李玉年醒了,是个梦。只是身子上面压着一个男人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身子上面的这个男人还在使劲地扭动着,那样子像是要把她吃下去一样。李玉年不由大惊,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把身子上面的男人推开,可是她怎么都推不开,身子上面的男人力气真大,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了。李玉年就哭着叫喊起来,那个男人就像刚才那样,用自己的嘴想把她的嘴给堵住。李玉年就又闻到了那种恶心的腥臭味了。
李玉年似乎已经知道身子上面这个男人是谁,她被吓坏了,连哭都不敢了。
一阵,身子上面的男人似乎是满足了,从她的身子上面滚下来,一边穿衣服,一边恶狠狠地说:“跟谁都不能说我们的事,不然,我要你儿子的命。”
是那个一杆枪孙小环啊,他怎么进得房来了啊。
孙小环从从容容地开门出去了。这时,李玉年才看见那半扇开着的窗子,她真的后悔呀,夜里贪凉,却引进来一个恶棍啊。李玉年把窗户关好,躺在床上悲悲凄凄地哭了半夜,想起孙小环留下的那句话,她的身子就不由哆嗦起来,她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二天起床之后,李玉年还是决定去乡派出所报案,姚所长不把他抓起来,他还会来的。李玉年早饭都没有吃,她不想让村里的人看见她这么早就去乡政府,她没有走那条简易公路,她想从一条小路出村去。
没有料到,她还没有走上小路呢,孙小环却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像是在这里等着她的,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你走进派出所的时候,你儿子也许就已经没有命了。我是进过笼子的人,又是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家伙,我怕谁呀,你要是不相信,敢跟我打赌吗。”
李玉年抬头看了他一眼,她发现那只深陷下去的眼坑陷得更加的深了,那只好眼却是射出一缕凶光。她浑身不由打了个寒颤,站那里就不敢动了,她担心他真地会去杀自己的儿子的。
孙小环说:“你去啊。你不去我可是要去了。我不会让你儿子死,先让他断一条腿吧。”
李玉年嗵地一声就跪倒在地上了,说:“你不能……我求你了。”
“行。我们就说定了啊。”这样说过,孙小环扬长而去。
李玉年回到家里的时候,伍明清却来了,伍明清老远就对李玉年道:“这次你要请我的客才是。”
走进屋,伍明清不由就呆住了,问道:“玉年你哭什么?”
李玉年没抬头,说:“我没有哭啊。”
“脸上有泪水,眼圈也是黑的。昨天夜里想长松了?”
伍明清来李玉年家里,也许就打的那个算盘,三句话,就离不得那些事了。李玉年还真想把昨天夜里孙小环爬窗子进房强奸她的事情对他说一说,他毕竟是村主任,再说,孙小环又那样怕他。
只是,话到嘴边她又咽了回去,对他说这个事,只怕他不但不会管,还会幸灾乐祸的,我敲门你不开,却让一杆枪给干了。活该。李玉年还想,他要是管这个事,怎么管呢。他不可能天天跟着孙小环的啊,那家伙可是个恶棍,他自己也说了,他是头上长疱,脚底流脓,什么都不在乎了。稍不留神,他真地对儿子动手怎么办啊。
李玉年不敢说,她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事严严实实地保密才是,怎么说都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件不光彩的事,村里人要是捕风捉影地说开了,自已的脸往哪里搁,在半垭村怎么待得下去。李玉年抬起头来,问道:“有什么好事要我请客?”
“插下去的禾苗,每亩三十块钱到位了。”
“半垭村人人有,为什么要我请客。”
伍明清笑着说:“我不这么说,怎么好来你家啊。田长松不在家,担心别人说闲话。”
李玉年说:“你不往那上面想,别人怎么说,人正不怕影子斜。”
伍明清说:“我人不正,影子就更加的斜了。”
李玉年说:“伍主任,你就没有一句正经话吗。”
伍明清说:“没有。今天夜里要给我开门啊。田长松打工去四个多月了,你还不想,我给你来解解渴吧。”
李玉年说:“你敢来,我让人打断你的腿。”
伍明清惊道:“你有人了,谁有胆量敢打断我的腿?”
李玉年也觉得这话说得不好,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
伍明清却是盯着她:“告诉我,你跟谁有一腿了。是那个跛子吗。他除了年纪比我小,别的能跟我比?”
李玉年差点就把孙小环的名子说了出来,她不是要用孙小环来吓唬他,她是想告诉他,她遭他强奸了。可是话到嘴边,她还是没敢说,眼泪簌簌地流淌着,说:“你快走吧,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想去乡医院弄点药。”
伍明清一脸狐疑地看着她,他想问问她哪里不舒服,张了张嘴,又没有问出口,只得走了。
李玉年看着伍明清远去的背影,心里若有所失,就哭得更加的厉害了。
这天晚上,李玉年睡觉之前把窗户认真地检查了一遍,把门闩好之后,还用几条凳子堵着,觉得万无一失了,她才躺下来。只是躺在床上,她怎么都睡不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口。窗口是灰蒙蒙的,她知道那是星星洒下来的光亮。一只萤火虫落在窗台上,像一盏闪着一点光亮的灯,又像是一颗星星从遥远的天空掉了下来,搁在了窗台上,像是要窥探躺在床上这个年轻女人的什么秘密。
李玉年突然想起田长松来了。刘玉卉说,她就是怀疑她家张大全在外面找小姐,不然他不会在外面打工一年不回来。刘如卉还对她说张大全跟她做那个事的一些细节,她说张大全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做那个事的,即便她身子不干净,他也强要做,她说这样的男人能做得到一年不沾女人的身子吗。那他还不疯呀。李玉年心想你说的这些我家田长松也一样的,男人么谁不那样啊。离开了自己的女人,他们就真地管不自己了吗。
李玉年是经常给田长松打电话的,她觉得田长松并没有像刘如卉说的那样,不在厂子里,或是说话吞吞吐吐,或是旁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问他,他不是说在床上躺着,就是在加班。田长松说他经常加班,加班有钱,时间也过得快。李玉年知道他话里的话,躺在床上,他想自己啊。
今天,李玉年又想给田长松打电话。田长松有手机。李玉年坐起身,把电话拨了过去。田长松接电话了,田长松说,今天没有加班,他也躺在床上睡觉呢。李玉年听到男人的声音,她就想哭。她有一肚子的屈辱要对他说。可是,她不敢。田长松问她:“你有事吗,电话通了你怎么不说话?”
李玉年把想说的话强咽了回去,说:“没事,我们宝儿也听话。你放心吧。”
这时,李玉年却听到田长松在那边轻轻地说:“我想你。”
泪水就哗哗地从李玉年的眼眶里溢了出来,她说:“多挣点钱,我们宝儿长大了好读大学。”
田长松说:“我知道,你要保重身体。”
李玉年说:“你也要保重身体,离过年还有四个月,那时你就可以回来了。”李玉年准备问问张大全的,可是,她没有问,刘如卉守不住,就编些话来说自己的男人。
李玉年在床上才躺了一会儿,她就听到窗子外面有轻轻的脚步声,李玉年浑身不由发起抖来,心也不由得提到嗓子眼了。
“开门,我来了。”
现在,李玉年就不仅仅是心提到嗓子眼,浑身发抖,眼泪像是决堤的坝水,哗哗地流淌,她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啊。
孙小环在外面说:“不开门,我就敲门了,让全村的人都听到是我在敲你的门。”这样说的时候,孙小环敲门的声音果然就大了许多。
李玉年哭着说:“昨天才来,今天又来呀。”
这话一出口,李玉年就后悔得不行,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果然,孙小环就在外面说话了:“你说,隔几天再来。”
李玉年说:“你不能再来这里了。”
孙小环说:“那就今天开门吧,我等不及了。”说着又咚咚地敲起门来。
这个时候,村里许多人家都还没有睡觉。不知道是谁家的狗首先吠了起来。李玉年哭着说:“小环,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
孙小环说:“就这一次,我就不会再来了。你要不开门,我就只有把我们睡觉的事情说给大家听了。”
李玉年万般无奈,只得开了门。孙小环进了房,就把李玉年抱到床上去了。这时,李玉年又闻到了那股腥臭味,不由哇哇地呕吐起来。她说:“这样一股腥臭味是从哪里来的?”
孙小环说:“我的眼睛流出的泪水有一股味儿。要是你不喜欢,往后我戴个眼罩就是了。”
李玉年说:“你刚才说就这一次……”
李玉年的话没有说完,她已经被压在他的身子下面喘不过气来了。
一阵,孙小环才心满意足地从李玉年的身子上面滚下来,还有些意欲未尽地说:“我睡的女人,就你最好。”
李玉年说:“你睡过多少女人了?”
“只要我喜欢,想睡谁就睡谁,有的女人我不想睡,人家夜里还开着门等我呢,不像你,让我动了许多的脑子。”
李玉年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女人正正经经过日子?”
“村里多少男人找不着女人,打单身。我这么个样子,还是劳改释放犯,谁愿意跟我。”
李玉年说:“你怪谁呀。我说,你不能破罐子破摔,好好做人,还是有女人愿意跟你过日子的。”李玉年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了,自己为什么跟他说这些呢,这不是像两个通奸的狗男女,做完那个事,再说些家务话吗。
孙小环这时却说:“跟别的女人睡觉,人家会向我要钱,你怎么不开口要钱?”
“我不是那种女人,我没同意跟你睡觉,昨天你是爬窗子进来强奸了我,今天是我自己开的门,我是担心别人知道了,没脸面见人,还担心你对我儿子下手。往后,你不要再来这里了。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孙小环不说话,心里想,身边这个女人,把儿子看得重,把面子也看得重。他说:“我还要一次。”
李玉年说:“你答应我,往后不再来这里了。”
孙小环说:“好。”
李玉年只得又让他睡了一次。孙小环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李玉年就又哭了起来,她哭得特别的伤心。直到五更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起来,李玉年突然想起隔壁的郭婆婆来,孙小环又是敲门又是叫喊的,也不知道郭婆婆听到没有,虽说老人的耳朵不好,有点背,日子久了,只怕纸是包不住火的。
办好早饭,李玉年盛了一碗饭,还夹了许多好菜送了过去。以前给郭婆婆送饭送菜,是因为同情老人,现在给郭婆婆送饭送菜,是不是掺杂了别的什么,李玉年心里都说不清楚了。
郭婆婆还没有起床,门闩着的。李玉年知道郭婆婆平时起来早,今天怎么还不起床,是不是病了啊,她大声地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李玉年就走到房子的后面,想问问郭婆婆,要是病了,她就给她弄点药来,无儿无女,可怜啊。
问了几声,郭婆婆还是没有答应。李玉年就趴在窗子上往里面看,这一看可把她吓得半死,连滚带爬就往伍明清家里跑去。还在伍明清的大门口李玉年就哭叫起来:“郭婆婆吊颈死了啊。”
伍明清正在吃早饭,放下碗就往郭婆婆家里跑。把郭婆婆颈根上的绳子解下来的时候,郭婆婆的身子早就硬了,也不知道老人是什么时候吊死的,也不知道老人是病了动不得吊死的呢,还是因为老了生活艰难吊死了。儿子在劳改农场,不会回来的。伍明清把赵前生叫了来,还叫了几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屋后面的半山坡上挖了个坑,钉了一副棺材,把郭婆婆草草埋了。
伍明清对李玉年说:“还真地要感谢你,要是你不给郭婆婆送吃的,她臭了都没人知道的。郭婆婆对我说过多次了,你经常给她送吃的。还真看不出,你心还这么好,下一届换届选举,村妇女主任我让你来当。”
伍明清说的话李玉年一句都没有听进去,眼泪却是成沟儿地流淌,她是想起郭婆婆来了,郭婆婆二十多岁就守寡,一辈子吃了多大的苦,到头来却上吊死了。
六
李玉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里发呆,还默默地哭泣。她常常想起郭婆婆来,她为什么要上吊死,大家都不说,其实李玉年知道,老人心里有事情想不开啊,老人日子过得苦啊,老人饭都弄不上口了啊,在这个世界艰难地熬日子,还不如死了好。
当然,让李玉年哭泣的还有孙小环。李玉年无法忍受孙小环经常来纠缠她。她要不开门,他就威胁她。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他的威胁,他的凌辱。她连死的想法都有了,像郭婆婆那样,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一切就都了结了,可是,她舍不得儿子,她舍不得男人,她还舍不得这日子,虽说有苦有累,有说不出口的苦涩,但怎么说这日子还是好过的啊,日后还要看着宝儿读大学,在城里工作呢。
“玉年姐,多久没有听到你叨念长松哥了,你不想他了?”
刘如卉一副高兴的样子从禾场外面走来,李玉年抬起头,把脸上的愁苦收起来,问刘如卉:“又有什么高兴事,看你那嘴都合不拢了。”
“能有什么高兴事。前生哥前几天帮着把油菜种下去了。你那田怎么不种油菜。九油十麦。去年这个时候,你家田里的油菜苗已经长好高了啊。”
“没心思种了。”李玉年有些懒洋洋地说。
刘如卉说:“我说,还是别憋着,熬着,找个男人解决一下,还可以帮着你做点重体力活儿。”
李玉年不做声,她像是想别的什么事情去了。刘如卉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个事情的,伍明清这次是长脸了,乡里领导准备奖励他。”
刘如卉把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像是要吊李玉年的胃口。李玉年不由得问:“什么事,让他长了脸?”
“孙小环昨天夜里偷郑美秀家里的猪,被伍明清发现了,抓孙小环的时候,让孙小环咬了一口,胳膊被咬伤了,伍明清那个气,狠狠地抽了孙小环几耳光,硬是把孙小环送到乡派出所去了。乡领导说,伍明清五十多岁了,还敢抓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偷。保一方平安,有功。”
李玉年心里不由一阵怯喜,说:“那个孙小环,这次又得劳改三年的吧。”
刘如卉说:“我真地希望他劳改去就别回来。前些日子的夜里敲开我的门,睡过之后就要我给他煮饭吃,还要吃鱼吃肉。我真地想对伍明清说的,让他好好收拾收拾他,想一想又没有说。伍明清会说我自己也想他来敲门呢,还不把我也弄得一身不干净呀。我希望那个孙小环遭雷劈死就好。”
这个话李玉年其实早就听她说过了,却是脱口道:“你也遭他的手了?”
刘如卉眼睛盯着李玉年,说:“你刚才的话说得不干净,那个一杆枪是不是把你也给睡了啊。”
李玉年连连摇头说:“没有。”
刘如卉说:“我不信。孙小环说,半垭村他想睡谁就睡谁,你这样的女人他不想?”顿了顿,刘如卉又说,“孙小环这人做那个事还真行,就是那只瞎眼里流出来的臭水让人受不了。”
李玉年问:“如卉呀,你那样,你家婆婆就不知道?”
“她知道要什么紧,有意见,把她儿子叫回来啊。”
刘如卉说了张大全母亲的许多处不是。过后,就说她听来的许多有关田坪乡男人和女人的事情。李玉年对她说的这些都不感兴趣,刘如卉说了一阵,只得没趣地走了。
刘玉年站起身,从柜子里拿了几个鸡蛋,用手巾包着,就出去了。
李玉年是去看望伍明清的。人家是村主任,怎么说对自己还是很关照的,听得说了,不去看看情理上过不去。
来到伍明清家里,把鸡蛋放在桌子上。伍明清的女人忙着给她倒茶,伍明清则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李玉年不离开。
李玉年说:“刚才如卉说伍主任被孙小环咬伤了,也不知道伤得重不重。”
伍明清摇晃着胳膊说:“小事,要你看什么,还拿了鸡蛋来。”
其实,李玉年来伍明清家有三个目的,一是来看看伍明清;二是想打听孙小环会不会去劳改;她还想打听一下孙小环被抓到派出所去之后姚所长会怎么审问他。一般情况,乡派出所抓到坏人,先要审问的,孙小环要是把他跟自己睡觉的事情说出来,自已这辈子怎么做人,别的不说,伍明清还不知道会怎么报复自己啊。
伍明清什么都不说,却是骂开了:“孙小环那个狗东西,把我们半垭村的名声都弄坏了,走出去人家说我们半垭村有个劳改释放犯,听起来让人矮三分。他居然还不改,还要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你怎么就把他给抓住了啊?”李玉年心里还真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郑美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女人,伍明清不可能夜里去打她的主意的嘛。
伍明清说:“你以为我这个当村主任的就只是拿着国家补贴的钱不做事的吗。孙小环回来之后,夜里我总要起来几次,到村子里走一圈的。村里青壮年男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治保主任也打工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再就是一些在家带孩子侍候老人的年轻女人,村里有了这么一个头顶生疱,脚底流脓的坏蛋,我放心吗。孙小环几次要爬人家的窗户,都被我赶走了,这次他动手的时候,我打了响声的,他不听,我只得把他抓起来,送到派出所去。”
李玉年问:“这次只怕又有几年吧?”
“乡派出所姚所长说,他肯定要把他送到县里去的,怎么发落就是县里的事了。”
李玉年坐了一会儿,伍明清的女人要给她办中午饭吃。李玉年就不好再坐了,几个鸡蛋,怎么好意思吃人家的饭。
李玉年没有回家去,她去了乡场,心里的一块石头似乎还是没有落地。
半垭村到乡场其实并不远,也就翻过几个小山坡就到了。还有一条简易公路,是伍明清前年向县里要来的钱修通的。比过去走那坑坑洼洼的山间小路要好多了。
来到乡场,李玉年又不知道自己来乡场做什么了,去对派出所姚所长说,一定要把孙小环送到县里去,判他几年。自己怎么好说那个话,对他说孙小环不仅仅是偷盗,他还强奸女人,这个话她也不敢说,证据呢,自己没有留下证据的。再说了,现如今有几个人会相信这个话。刘如卉跟半垭村好几个男人都睡过觉,跟孙小环也睡过,能说是男人强奸她吗。
李玉年在乡场上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阵,她去了一趟学校,看了看儿子,在老师那里问了一下儿子的情况,才回来。
这天夜里,李玉年睡得特别的踏实,她不再担心孙小环会来敲她的门了。
第二天,李玉年居然到禾田里整地种油菜去了。迟点就迟点,不把油菜种上,明年就没油吃了。
季节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魔力,已经把满目绿色的山野变成了一片枯黄,没有了春天的生气,也没有了夏天的活力。秋风瑟瑟,万物萧条。但李玉年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她觉得秋天也十分的美妙,瑟瑟秋风那是弹奏出的动听的音乐,几朵野菊那是点缀秋天的美丽。太阳高高地挂在蓝天,几片白云飘呀飘的,格外的清闲自在。
李玉年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把干得开坼的水田锄过来,整好,把油菜籽播上,又施了肥,再有十来天,油菜苗就会从地里长出来,绿油油一片。
只是,李玉年还在憧憬着明年收油菜时的丰收景象,李玉年才放心落意地睡了半个月的安稳觉,孙小环又来敲她的门了。开始的时候,李玉年还以为是伍明清,说:“你不要有那个想法,我不会开门的。”
没有料到,外面的敲门声变成了撞门声了,还传来恶狠狠的话语:“再不开门,我就放火把这屋子给烧了。”
李玉年的浑身就发起抖来,问道:“你没去劳改农场?”
“你想我去劳改农场?”
李玉年知道自己这个话没有说好,说:“我求你了,不要来找我好不好。”
“你开门,我有话要对你说。”
李玉年知道不开门的后果。只得把门打开。孙小环带着一股恶腥臭的气味冲进屋来,恶狠狠地说:“在县公安局拘留半个月,吃了多大的苦,你还希望我去劳改呀。”
李玉年说:“不学好,偷人家的猪,拘留半个月真地便宜你了。”李玉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她觉得这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就像他是自己的什么人似的。
孙小环不跟她说这些,把她拖进房,三下两下把她的衣服扒光,就压在自己身子下面去了:“你知道吗,在拘留所我还想着你的。”
心满意足之后,孙小环没有像平时那样匆匆就走了,对李玉年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偷郑美秀家里的猪吗?告诉你,这次偷猪是因为你。”
李玉年吼他道:“我让你偷人家的猪了?”
“我想给你买衣服,却没有钱。”
李玉年的眼睛就瞪大了,过后就哭了起来:“你强奸我,我没报案就便宜你了,今后你再要来找我,我一定要报案的。”
孙小环却说:“你要是想报案还不早就报案了,你其实是喜欢我的。我想好了,要跟你结婚。你不是说要我讨个女人成个家,好好过日子么,我就讨你。”
这是李玉年万万没有想到的,她说:“不可能。我有长松,我有儿子,怎么可能跟你结婚。”
“你跟长松离了,我们再结婚。”
“你是痴心妄想。跟你结婚,还不如去死。”
孙小环却不跟她再说下去了,穿好衣服,扬长而去。
李玉年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可怕。哭了半夜,第二天起来,早饭也没有吃,就出门去了,她想好了,这次是一定要去报案的,不然还不知道孙小环会弄出什么后果来。
乡派出所姚所长李玉年认得,不过三十来岁,长得十分帅气,态度也十分的和蔼。三年前,姚所长来半垭村抓孙小环的时候,还来她家里调查过孙小环的情况的。那时田长松的母亲还没有去世,躺在床上起不来,李玉年接屎接尿侍候老人。因为这,她还被乡政府评为全乡孝敬老人的好儿媳呢。姚所长那天来家里的时候,还对她说起这个话来,姚所长说,他就喜欢那些孝敬老人的女人。姚所长说他也是农村人,他女人也在家里做农活,带孩子,侍候他的母亲。那个时候,李玉年心里就像是灌了蜜一样,腰上别着一支短枪,穿着一身制服,多么威武帅气啊,他的女人居然跟自己一样也是农民,身上也有汗臭味儿,她仿佛觉得自己跟他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她还想他女人的命真好,嫁的男人是国家干部。
可是今天自己却要去对他说遭孙小环强奸的事,要是孙小环一口咬定说不是强奸,是自己开门让他睡的呢,要是姚所长详细地问起这件事情,自己该怎么说。自己能说孙小环已经睡了自己多少次么,自己为什么不早报案呢,是不是像孙小环说的是通奸。那样,姚所长不但不会把孙小环怎么样,还会把自已看扁了啊。
李玉年没有勇气去找姚所长了。她去了伍明清家里。
伍明清没有起床,他女人坐在门前哭泣,这让李玉年有些吃惊,伍明清的女人算得是半垭村最贤惠的女人了,支持男人的工作,还不听人们的闲言闲语,别人就是把一些话说到她的耳朵里去,她也就一句话:“你们说这些没用,我男人我自己知道。”
今天怎么了啊。李玉年问:“婶婶,伍主任在家吗?”
女人抬头看了李玉年一眼,说:“我就知道你们一个二个都不是好东西,没有安好心,男人不在家,你们守不住了,夜里谁敲门都会接纳。我家明清也被你们哄得团团转,到头来,还要受你们的害。”
李玉年的脸红一块,白一块,说:“我没有啊。婶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还不说这话,我家伍明清昨天夜里差点被别人打死了。”
李玉年不由吃了一惊,问道:“谁打伍主任了?”
“大全昨天夜里回来了,他能不打他?”
李玉年想好的话也不敢说了,心想张大全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他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了,还是他老娘给他打电话了。她想去张大全家问问长松还好吗,他会不会回来。走到张大松家门口,她还是没敢进屋去。人家家里出这样的事情,自己怎么好掺和啊,说不定还会弄得一肚子气怄的。
七
李玉年不敢去乡政府找姚所长,也不敢去对伍明清说,孙小环却是天天夜里来她家,对她说跟她结婚的事。孙小环像是跟女人商量家务事,教李玉年怎么跟田长松离婚,教李玉年怎么才会要得一些家产,还要李玉年把宝儿分给田长松,他要和她再生一个他们自已的孩子。李玉年怎么哭,怎么求,怎么拒绝,甚至同意在田长松没回来之前让他来家里睡觉。孙小环却是一句话:“我就喜欢你。我要跟你结婚。你要不同意,我们就走着瞧。”
那天,田长松打电话回来,问儿子读书的成绩好不好,听老师的话不。当然,田长松打电话回来,还有悄悄话要对李玉年说,他想她。田长松却是没有想到,他在千里之外打电话的时候,李玉年的眼泪已经成沟儿地从眼坑里滚了出来,田长松的话还没说完,李玉年却是带着哭腔说:“长松,你快回来。”
田长松听到李玉年的声音有些不对,着急地问道:“玉年,你怎么了?”
李玉年还是一句同样的话:“长松,你快回来。”
“村里出什么事了。张大全没对我吭一声,就回来了,你现在又叫我快回来。”
李玉年仍然是那一句话:“你快回来。”不过,声音已经带着哭喊了。
放下电话,李玉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她想等着长松回来之后,她就不让他出去打工了。他在家,孙小环是不会来家里了吧。
这天晚上,孙小环又来了。李玉年没有拒绝他,她知道拒绝也没有用。心想这么多日子都熬过来了,再受委屈,再受凌辱,也就这两天了。
孙小环来到家里之后,还是跟过去一样,首先是要和李玉环做那个事,之后就跟她说离婚和结婚的事情。
李玉年说:“我家长松过几天就回来了,不再出去打工了。”
孙小环开始还怔了怔,后来就说:“这是怎么了,张大全也说不出去打工了,要在家守着女人。不过长松回来更好,我就开诚布公地对他说说我们的事。”
李玉年着急地说:“你可不能说啊,那样我真地只有死了。”
孙小环脸上流露出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穿好衣服就走了。李玉年的心就悬了起来,她不知道田长松回来他会做出什么来。
田长松是第二天天黑的时候赶到家的。田长松说,他接到李玉年的电话之后,连夜买了一张火车票,转了一次火车,又转了两次汽车,才赶到家:“玉年,听你在电话里说要我回来,我那个急呀,玉年,你怎么了啊?”
李玉年扑进田长松的怀里,哭着说:“往后,你不要去打工了,在家跟我一块种田。”
田长松着急地问道:“快告诉我,谁欺负你了?”田长松看到女人比过去瘦多了,脸也没有了过去的红润,眼里还隐隐含着一种恐惧和忧虑,眼泪却是簌簌地淌落,心疼地搂着她,“快说,我这就去收拾他。”
李玉年不肯说,她只有一句同样的话:“我们在家种田、养鸡、喂猪,也一样能挣到钱的。我们家宝儿到时候还是能读得起书的。”
哭了一阵,李玉年准备去给田长松办饭。田长松说他还是早晨在火车上买了盒方便面吃了的,早就饿得肚皮贴后背了。李玉年那个心疼呀,她一定要给他弄些好吃的才是。
就在这时,李玉年听到禾场外面传来叫喊她的声音。孙小环又来了。李玉年只是怔了片刻,她就走了出去,她不能让孙小环走进门来。
十月下旬,一丝凉意袭上身来,李玉年走出门,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这天夜里没有月亮,天上的星星也被云彩遮住了。李玉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走路都有些跌跌撞撞了。
“听说长松回来了,我想跟他说一说我们的事情。”也许,孙小环还是有些怕田长松的,不然,他怎么不直接走进屋去,而是站在禾场外面叫喊李玉年。
李玉年说:“你不要做梦了,快走吧。”
“我不走,我要让田长松知道我们的事情。”这样说着,孙小环就想往屋里去。
李玉年拦住了他,带着哭腔说:“我求你了,不要再说那个话了。”
孙小环说:“你答应我了?我不说,你自己去说吧,我在这里等着的。”
李玉年仿佛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我们去那边说吧。”
“到哪里去说?”
“不能让长松听到的地方。”
孙小环说:“为什么不能让他听到呢,就是要让他听到,事情才办得好啊。”
李玉年不再说话,往禾场外面走去了。
孙小环只得跟在她的身后往禾场外面走,口里说:“也行,我们先商量好,怎么开口说那个话。”
禾场外面是一片水田,水田里的油菜种得早,长得青枝绿叶的样子,可是今天却是什么都看不见。孙小环似乎有些不耐烦了,问:“还要往哪里走,就在这里说。”
孙小环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他就觉得脑壳上像是被什么重重地敲了一下,他才啊那么一声,就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
当时,田长松还在想呢,黑天黑地,谁在外面叫玉年,玉年怎么不让他进来,却是带着他往禾场外面走。田长松跟了出来。才走了几步,他就又踅回身子,外面太黑,他想找玉年用的手电筒,却是没有找到,只得从口袋掏出打火机,借着打火机的光亮走出禾场。
田长松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那一声响了,像是菜刀切西瓜的声响,过后,他又听到了啊的一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边往前走,一边问:“玉年,谁叫你啊。”
田长松听到一串脚步声正匆匆地往前面的那条简易公路去了,却是看不见是谁。
田长松心里不由生出一团狐疑,女人怎么了,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啊。就在这时,田长松的脚突然踩着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可把他吓了一跳,勾下头,他被吓得半死,借着打火机的那一星点光亮,他看见孙小环躺在地上的,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着气,那只没有瞎的眼睛瞪得老大,血从他的头上喷出来,把一片油菜都染红了。
田长松似乎已经觉出了什么,大叫:“玉年,快跟我把孙小环送到医院去,不然会出人命的。”
那一串匆匆的脚步声就停了下来,过后脚步声就又响了过来。借着打火机的光亮,田长松看见自已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柴刀,柴刀上还沾着许多的血。“玉年啊,你怎么能这样,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啊。我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李玉年勾下身子,伸手在孙小环的鼻子下面试了试,过后就扬起柴刀,狠狠地向孙小环砍去。孙小环就不再喘气了,他的脑壳,已经被李玉年劈开了。
田长松想去抢李玉年手里的柴刀,李玉年却走了,一阵零乱的脚步声向远处去了。
田长松声嘶力竭地叫道:“玉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李玉年这时回他的话了:“长松,带好我们的宝儿……”
李玉年的声音在空旷的黑夜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沉默的夜,是那样的深沉,那样的迷惘……
责任编辑 王宗坤
邮箱:wangzongkun20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