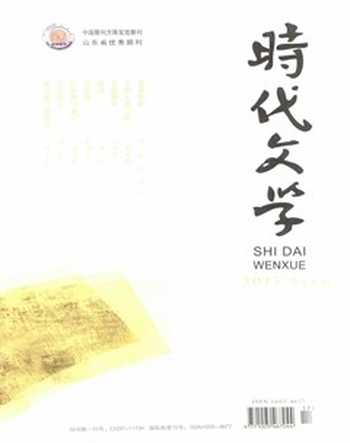老宅
郝炜华
1
我父母住在一个老住宅区,五层的红砖小楼,没有暖气,没有天然气,没有单元门。10户人家,除了一楼的老太太,三楼那对妻子患了强迫症的夫妻,我的父母,父母对面离了婚的男人,其余全是租房的男女。那些男女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一帮男人租一套房子的,有一帮女人租一套房子的,也有男女一起租一套房子的,这些人回家没有规律,经常半夜时分喊着叫着从楼外归来,有人醉了酒就在单元门口呕吐,也有年轻姑娘从五楼吐着瓜子皮与痰一直走到一楼。楼里的“原住户”都感到愤怒,却没有人敢指责他们,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些人的底细,担心他们一个砖头扔到窗户上,然后一溜烟跑到祖国的某个地方藏起来。我的父母信仰基督,善良得有些糊涂,那些醉酒吐在单元门口的污物,总被母亲扫到垃圾堆去,楼道里的瓜子皮与痰迹也被她清理干净。父亲用他的退休金做了个铁门安在单元门口,给每户人家送去一把钥匙,每晚9点半,他去锁闭单元门。最初租房的男女记得带钥匙,一段时间下来,钥匙不是忘在屋里就是丢了,刚开始他们还在楼下喊我父亲:“大爷,大爷,麻烦你开一下门。”喊过几次,突然心烦,就把锁眼给堵上了。父亲换了几次锁,他们堵了几次锁眼,父亲一下子明白,这些人是坏了心的,换上千百把锁,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心。于是,父亲不再换锁而是打算搬家,这个时候,房价已经很高了,我的钱加上父亲的钱不能够在城市买一处新房子,父亲打消了买房子的念头,天天坐在客厅里,对着移来移去的日影唉声叹气。这个时候,一楼的老太太被他的五个儿子送去了养老院,儿子说:“带你逛商场。”将她骗上出租车,老太太的小叔子骑着三轮车在不远处看着他们,张着嘴想说话却又一副不知道说什么的样子。妈妈站在窗户前面掉眼泪,一边掉眼泪一边跟老太太摆手,老太太欢天喜欢地说:“我一会儿回来,回来就找你玩。”老太太去了养老院不久,她的儿子粉刷了房子,租给一个单身女人,那女人进门就挂上粉红色的窗帘,防盗门换上粉红色的窗纱,屋里喷着味道奇怪的香水,然后就有不同的男人陆陆续续出入她的房门。再过不长时间,三楼男人也到她房子里去了。三楼的女人轻易不出门,她在家里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洗手,但是为了自己的男人,她出门了。她先找住在父母家对面的男人,要他去派出所告那个女人。父母家对面的男人姓牟,叫牟有树,离了婚,但是家中从来不缺女人,找的女人有退了休的女教师、下了岗的医药厂女工,也有菜市场卖猪头肉的。他自己整天换女人,就不好意思管一楼女人的事情。于是三楼女人就来找我的父母,父母知道从基督角度讲,一楼的女人犯了罪,死后必然下地狱,但是他们不知道从生活里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唯有日夜向上帝祷告,乞求上帝解决这个难题。兴许祷告起了作用,一个月后一楼女人不声不响地搬走了,接着房子里又搬进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良家妇女,为什么?衣着朴素,面貌平常,并且带了一个患了痴呆症的女儿。
因为租房客的所作所为,楼里的“原住户”都对这个女人抱着敌视的态度,但是不长时间这个女人就用行动消解了所有敌视。搬进楼里的第二天早上,她把单元门口扫得干干净净,这本是母亲星期六必做的功课,她以此敬献爱心,证明信仰基督的强大力量。女人将单元门口扫得干干净净,无形中剥夺了母亲敬献爱心的机会。母亲想去找她,被父亲训斥一通,只好作罢。女人又买了五个声控灯泡,安在了一楼至五楼的楼道里,这使晚间黑幽幽的楼道有了人间的光明与鲜亮。最叫“原住户”佩服的是女人有一天跟个陌生男子吵了一架。那男子半夜时分到楼道里涂广告。楼道里全是这样的广告,乌黑的自喷漆喷着蜈蚣样的字:办假证、贷款等等。父母家门口的墙上是几个大字:办证复仇,后面一串手机号码。套着电线的PVC管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小广告纸,像人长了牛皮癣一般。
天晓得女人为什么半夜时分还没有睡觉,“原住户”被吵闹声惊醒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单元门口厮打在一起,陌生男人显然想跑,女人抓住他不叫他跑,嘴里还一连串地喊:“叫你弄脏我们的墙,叫你弄脏我们的墙。叫你恶心人,叫你恶心人。”“原住户”都趴在窗户上看,没有人敢下去拉架,等到警车亮着雪亮的灯开进住宅区,警察大声训斥那名男子时,“原住户”才跑到楼下,弄明白事情的原委,自然对女子佩服与尊敬起来。
好印象油然而生,父亲被这种好印象驱使又买了一把新锁挂在铁门上,每家每户送去钥匙后,他在铁门旁边贴了一张字迹不算规整的告示,意思是单元是我家,人人都爱它,只有维护了单元的安全与宁静,才能保证回家的温暖与温馨。这张告示果真起了作用,很长一段时间,那些租房的男女没有再忘记带钥匙与丢钥匙。
好的人总是叫人喜欢,“原住户”不再用冷漠的淡然的目光扫视女人,而是主动跟她打招呼,送点好吃的给那个孩子,女人的名字自然而然地被问出来,刘兰花,是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名字。应该是农村来的吧。为什么从农村来到这里?为什么独自带了一个患痴呆症的孩子,这些却问不出来。
不长时间,住宅区门口支起来一个夜宵摊子,摆了七八张小方桌,卖炒菜、啤酒、馒头、面条还有羊肉串。摊子的主人不是别人,就是刘兰花。
2
住宅区门口其实是个巷子口,左边拐角是一家火锅店、一个药店、一个洗浴中心,右边是个堆满建筑垃圾的空地,向前不远处是一座大楼的背面,再走一点是个垃圾堆,住宅区的居民都将垃圾放在那里。巷子口没有灯,刘兰花在炉灶上方挂着一盏灯泡,照着她炒菜的同时,也给食客一点光亮。食客大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面目不详的男女,光着脊梁、胳膊上有刺青的男人;还有晃着大腿,肥胖粉白的女人。巷子口不是个干净地方,虽然每次刘兰花都用心打扫,但是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从地面蒸腾到空中,加上灰暗的气氛,散落在小方桌下面的剩菜、花生皮、毛豆皮、啤酒瓶子、痰迹等等,使这个地方看上去根本就不适合吃东西。但是总有人到这里吃东西,特别是夜间8点到12点,刘兰花忙得要命,切菜、炒菜、端菜、收拾桌子,一顶雪白的帽子压在眉头上,忙得抬不起头来。
最先给刘兰花帮忙的是母亲。刘兰花弄了个婴儿车放在摊子旁边,她那患了痴呆症的女儿就塞在婴儿车里,吃手指头或是玩张纸片或是盯着一个地方发呆,累了就歪着头睡觉,倒是不哭不闹。母亲看着心疼,搬了个板凳坐在旁边,帮着照看刘兰花的女儿。然后父亲又来给刘兰花帮忙,父亲年龄大,做不了什么事情,就帮刘兰花收钱、找钱,钱放在一个空的豆瓣酱瓶子里,盖子都不盖,也没有记账。再后来三楼的男人也来了,他做的事情多,端菜、收拾卫生、搬啤酒,忙到夜间十点,回家伺候妻子睡觉。第二日凌晨二时或是三时又出来,帮刘兰花收拾摊子,两人将炉、灶、小方桌、凳子等等架到三轮车上,在幽深的巷子里,推着,叮叮当当地回家。
没有帮忙的是牟有树,他不仅不帮忙,还说闲话,说:“三楼的男人心野了,刚刚散了那个女人,又搭上这个女人,唉,都是一楼的,他与一有缘呀。”牟有树故意将“一”说得含糊不清,听上去就像“日”一般。他的闲话传到了三楼男人的妻子那儿,那妻子不应声。第二日晚上端了脸盆到巷子中间,一遍一遍地洗手,一边洗嘴里一边嘟囔:“洗净这天下最肮脏、最肮脏、最肮脏的东西”。食客一边吃饭一边惊讶地看着她,三楼的男人脸色苍白地坐在一旁,刘兰花生意也没心思做了,小声说:“快叫她回家吧。以后不要来帮忙了。”男人说:“现在不能惊动她,惊动了就不得了。”女人足足洗了两个小时,端起脸盆,走到右边堆满建筑垃圾的空地上,哗地一声将水倒到一个窝棚上面。
只听“啊”地一声,窝棚里面钻出一个男人。父亲、母亲、三楼的男人,包括牟有树这才发现空地里多了一个窝棚,多了一个男人。这窝棚与这男人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他们浑然不知。按道理他们天天从巷子口经过,对这里的东西与景物很熟悉的,多了什么,少了什么,确实应该知道。可是他们就是不知道。
男人冲着三楼的妻子啊啊大叫,三楼妻子 “呀”地一声,丢了脸盆就往后跑,跑到三楼男人身后,探出个脑袋来,说:“打他,打他。”
三楼男人说:“好,好。”丢了女人就往前冲,这个时候,正在切菜的刘兰花突然举着刀过来,挡在三楼男人面前,说:“敢动他,敢动他一下试试。”
三楼男人没想到刘兰花会有如此举动,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说:“我哪里会真打他,我老婆有病,我只做个动作,安抚一下我老婆。我哪里会真地打他。”说完,挥手对着空气做了几下打的动作,他妻子在身后拍手,“打得好,打得好。”
那晚上,三楼男人没来帮刘兰花,刘兰花自个将炉、灶、小方桌、凳子等物架到三轮车上,吱吱呀呀地推着回家,单元门口,三轮车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炉灶、小方桌哗啦啦掉到地上。黑影里面钻出一个人,先将炉灶抬起来,又将小方桌扶起来。刘兰花抬头看,不是三楼的男人而是我的父亲。母亲则站在客厅的窗户前探头张望。父亲毕竟年龄大,帮刘兰花将东西摆到地下室后累得气喘吁吁,刘兰花请他到屋里喝水,他摆手说不用,又说刘兰花,怎么着是个年龄不大的女人,虽说带着残疾孩子,但是是个女儿,不算负担,找个男人嫁了,不比这样辛苦好吗?
刘兰花的眼圈红了,眼睛盯着一角,应该是努力将眼泪憋回去,她说:“嫁什么嫁,我这样的女人。”
“其实牟有树不错的,虽然有些乱说话,过日子还是靠谱的。”最近,牟有树屋里的女人走了,新的女人还没有搬进来。
“那哪行,那哪行?”仿佛怕父亲再说下去,刘兰花转过脸看父亲,“窝棚里的男人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悄悄地就多了一个窝棚,然后就多了一个人?”
“是呀,什么时候多出来的?我以为你知道呢。”
“我哪里知道?哪里会知道?”
“你为什么要护着他?好像你认识他一样。”
“一个穷人,一个老年人,怎么经得起打,即使是条老狗,也不能随便叫人打的。”
3
第一个给窝棚老男人送东西的是母亲。刘兰花抢占了母亲清扫单元门口的机会,母亲就用救助窝棚老男人来敬献爱心。反正她总要做一件事的,否则她的心里总不安定。早晨起床,母亲到菜市场买了油条、豆浆送到窝棚门口,说:“这个人,吃早饭吧。”
老男人从窝棚里出来,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一张脸因为长年不洗已经看不出本色,他扬手要打母亲,吓得母亲向后一跳,差点摔倒,说:“我又不占你便宜,你打我做什么?”一边说一边将油条、豆浆递过去, “热的,吃吧。”
老男人抓过油条、豆浆,手一扬,油条、豆浆化成一条曲线,飞了出去,特别是豆浆,白白的,带着热气,就像电视里面的牛奶广告。
妈妈忍不住骂道:“怎么有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回家,正好遇到刘兰花,告诉刘兰花。刘兰花说:“他神经有问题,不要理他。”走两步,又回头说:“如果真要送吃的,挂在窝棚门口就行。”
母亲为刘兰花的话感到奇怪,她不也刚认识窝棚老男人的吗?她怎么知道老男人有神经病?
事实证明刘兰花的话是对的。第二日,母亲将油条、豆浆挂在窝棚门口,九点左右就被老男人拿到窝棚里吃了。
老男人非常影响刘兰花的生意,他的窝棚与食客的小方桌仅一墙之隔,窝棚内难闻的气味总要飘进食客的鼻子。偏偏生意忙的时候,老男人就从窝棚里钻出来,靠着一堆废弃的水泥块冲刘兰花的摊子不断地张望。尿急了或是屎急了,就跑另一处墙角撒尿与拉屎。有一次他撅着屁股找擦屎的纸片,食客冲他嗷嗷叫:“啊,啊,啊。蛋蛋露出来了。”更有人将羊肉串签子扔过去,试试能不能扎到他的屁股上。
这些还是小事,最可怕是有天晚上,老男人趁母亲没来,突然冲到婴儿车旁将刘兰花的痴呆女儿抱起来。刘兰花正在切菜,“嗷”地一声,菜刀往案子上一拍,吓得老男人手一松,孩子掉到了地上。
母亲、父亲与牟有树都觉得老男人的存在是个错误,他们与刘兰花商量将老男人撵走,撵的方法当然很多,找城管、找民政或者是找人吓唬他一通。刘兰花摇头,说:“叫他在这吧。”
母亲说:“你跟老男人都是可怜人。按理我们也应该可怜他的,可是在两个可怜人之间我们总得有个选择,老男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先管你。”
刘兰花依然摇头,说:“叫他在那,叫他在那吧。”
牟有树背地里跟母亲说:“刘兰花好怪的,收摊的时候总拿些吃食放在窝棚门口,她可不放油条、豆浆,她放的是炒菜,有次还放了油炸的馒头。对了,她送了老男人一床毯子。”
噢,竟然有这样的事。母亲与父亲有些生气,刘兰花守着他们的面对老男人拍菜刀,背着他们却敬献爱心,做好事哪有这样的?要做就光明正大地做,干吗偷偷摸摸地做呢?
父亲说:“基督教讲究做善事不声张。刘兰花大约也是基督教徒吧。”
兴许是基督教徒吧。可是牟有树又怎么知道刘兰花给老男人送东西呢。
牟有树最近有点奇怪的,上个女人走之后,他家里没再来新女人。他本是个游手好闲、不关心别人,好搬弄是非的人,现在却对地下室的一只老猫和几只小猫大献爱心。老猫是只野猫,野混怀孕后生了五只小猫,养在地下室的纸壳子里,日夜不停地喵喵叫。牟有树每天到菜市场买小鱼,放到小白碟里喂它们。
牟有树说:“猫就是猫,送小鱼不能离它们近,一近,母猫就张牙舞瓜地吓我,以为我要抢它的小猫呢。只能放得远远的,等着它们自己过来吃。”
既然窝棚老男人不能搬走,父亲与母亲就祷告上帝,不要那老男人出来惹事,叫他像正常人一样作息,白日出来游荡,晚上呆在窝棚里睡觉,免得影响了刘兰花的生意。祷告了一个星期,老男人的窝棚突然失火了,所有的东西烧个了精光。父亲与母亲大吃一惊,不知道哪里出了错误。他们跑到窝棚那看,正看老男人守着一堆灰烬哇哇大哭,这样傻的人还知道哭呢。
父亲、母亲摇头,说:“趁这个机会走了就行。”
老男人却没有走,虽然身无一物,仍旧在建筑垃圾中间呆着,白天躺在地上晒太阳、睡觉,睡着睡着一张肚皮就露出来,口水顺着嘴角流到前胸上;晚上就倚着水泥墩冲着刘兰花的摊子胡乱张望。刘兰花做生意越来越心不在焉,炒菜不是忘记放盐就是搁多了盐,弄得食客三番五次冲她大骂。
母亲还是给老男人送早餐,午餐与晚餐大约都是刘兰花送,每日都有吃食,又什么事情不做,老男人虽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是脸色日益红润,身子也胖了起来。
4
巷子里面多了个人,就是第一个租老太太房子的女人,她突然卷土重来,在住宅区的另一处租了房子。这女人老了许多,脸上抹了厚厚的粉,但是仍然遮盖不住沟壑一样的皱纹。
租老太太房子的时候,女人是呆在屋子里等男人,这个时候,她蹲在巷子口的一块圆石头上等男人,男人从她身边经过,她就扬手,斜着眼看他,不说话。遇到相中她的,就站起身,领着男人回出租屋。
母亲、父亲对这个女人厌恶之极,每每看到她就恨不能一口唾沫吐到她的脸上去。但是后来,有一天下大雨,母亲与父亲看到女人穿着极少的衣服,浑身发着抖,仍然蹲在圆石头上等男人的时候,突然对她同情起来,说:“她也不容易呀。肯定有难以言说的苦难,否则谁来做这种事呢。”
他们有心帮助她,可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只能远远地看着叹气。
与父母一同远远看着女人的还有牟有树,牟有树一边看一边摇头,说:“三楼男人肯定后悔死了。他竟然跟这样的女人有交情,肯定后悔死了。”
三楼的妻子也下楼来了,她没想到那个女人会重新回到住宅区,她担心她的男人又会去找她。三楼的妻子没有别的招数,只会面前放着一盆水一遍一遍地洗手,洗得十个手指头快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了。
三楼男人陪在一边,小心翼翼地说:“我跟她什么也没干,就是帮她修修水龙头,通通下水道。喝了一杯茶,什么也没有干。你这么爱干净的人,我哪敢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
还说那天下大雨的事吧。父母为什么知道那个女人仍然蹲在圆石头上等男人,是因为父母突然想起窝棚老男人。晴天白日的时候,老男人可以在阳光下晒太阳,在月光下睡觉;大雨的晚上,他躲到哪里?他知道躲雨,懂得躲雨吗?
父母举着一把伞,拿着一把伞去空地找老男人。找来找去没有找着,心下宽慰,虽然傻,总知道爱惜自己的。
第二日天晴,老男人仍然没有出现,似乎一场大雨将他像污垢一样冲进了下水道里。空地上没有他脏肮的身影,没有他面目不清的面容,空气清新了许多,阳光也分外灿烂了。父母相信,今夜刘兰花的生意会比往日兴隆。
但是夜间,刘兰花没有出摊。那些经常到摊子上吃饭的食客转悠几趟也没有找到刘兰花的身影。那个蹲在石头上等男人的女人等来一个大方的男人,肯请女人吃饭,他领着女人也找刘兰花的小吃摊,没有找到,就站在空地前骂:“难道要叫我空着肚子日吗?你,空着肚子,愿意叫我日?”
父母去敲刘兰花的门,敲半天,屋内没有应声。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刘兰花除了做生意、买菜就是呆在家里,人规矩得很,生活规律得很,这一下子不规矩了,不规律了,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父母跑到巷子口张望,那里车来车往,人来人往,没有刘兰花的身影,没有父母认识的人,在这个不太大的,按照某种秩序机器一般运转的城市,消失一个人竟是如此的简单与容易。
第二日,第三日,刘兰花依旧没有出去。父母决定找她,如果找不到就报警。他们动员牟有树一起去,牟有树摇头,说:“一个陌生女人,我才不管。我得给小猫送食,小猫长大了,大猫就偷懒,经常跑出去玩,不管它们。”
动员三楼的男人,三楼男人一口答应。他们出门找刘兰花,商场、医院、住宅区、河边,各种能够想得到的地方,都去了。护城河的一个树丛里,一群人围着一个水淋淋的男人,一个女人趴在水淋淋的男人身上哭。母亲挤进去,一眼就看到哭的女人是刘兰花,水淋淋的男人是谁呢,仔细一看,真地吓了一跳,竟然是窝棚老男人。
老男人必须送医院,刘兰花没有足够的钱,父亲从银行取出一笔钱替他垫上。刘兰花在医院护理老男人,母亲帮她看孩子,三楼男人自告奋勇送饭。牟有树起初骂这些人是神经病,后来却被感动,买材料又给老男人搭了一个窝棚。可是这个窝棚一点用没有,因为老男人出院后,住进了刘兰花的家里。
这下子所有人都不理解了。送饭,找老男人、护理老男人还可以理解,爱人,救助弱者,从“小我”上升到“大我”,至情至真至善,是值得学习、歌颂与理解的。可是将老男人,一个没有家的,有些痴呆的老男人接到自己家里住,这就太、太、太过分,太、太、太难以叫人理解了。
父母与三楼男人与牟有树面面相觑,感觉事情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5
刘兰花出摊的第一天,又有男人领着蹲圆石头的女人来吃饭。母亲主张刘兰花不卖饭给她,或者直接在饭里下上毒药将女人毒死。刘兰花却是炒好菜端到他们面前,并且赠送了一盘煮花生。
蹲圆石头的女人扭扭捏捏地说:“谢谢。”
刘兰花说:“谢什么。跟你比,我又好到哪里去。”
这话恰巧被母亲听见,母亲就插空跟刘兰花说:“你哪能这样作贱自己,哪能把自己跟她比。虽然你是农村来的,虽然你穷,虽然带个痴呆孩子,但是你是干净身子,你的钱也是干净的。”
刘兰花低着头切菜,不说话。正在吃饭的女人却头一歪,眼泪哗哗地掉下来。
老男人在刘兰花家过得并不好,虽然衣服干净了,脸上的灰也洗去了,但是刘兰花经常跟他吵,有时候会用难以入耳的肮脏语言骂他。虽然刘兰花对别人是礼貌的,恭敬的,谦让的,但是对于老男人却恶劣得像只母狼。父母,连同牟有树都看不下去了,跟刘兰花说:“你帮他是个好事,可是这样虐待他,倒像件坏事。”牟有树说:“那个窝棚反正还在,叫他再回窝棚住。”
刘兰花看看父母,看看牟有树,看看,看看,又看看,突然“哇”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砰”地一声关上门。
刘兰花的哭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形容,父母与牟有树一齐敲她的门,怎么敲也敲不开。刘兰花在里面一声接一声地哭,间杂着老男人喊“救命”的声音。天呀,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要杀了老男人?是不是,是不是呀?
着急之中,牟有树想到了三楼男人,刘兰花是信任他的,他敲门,刘兰花应该会开的。牟有树喊来三楼男人,他妻子端着一脸盆水紧紧跟在身后。母亲将三楼的妻子拉到我家,说:“到我家洗手,兑点热水,兑点热水洗得干净。”
听得三楼男人敲门,一声接一声地叫“刘兰花,刘兰花,刘兰花。”
哭声停了,门真地开了。然后又闭了。
三楼男人来接妻子。母亲问他怎么样,老男人是不是被打死了?虽然刘兰花是个好人,虽然救助老男人,但是这样骂他打他是不对的。
三楼男人目光怪异地看着母亲,说:“我是第一次到刘兰花家里,墙壁涂得那个白呀,雪窟窿一般。桌子、门也是白的,床上的被单、枕头套也是白的。我从没见过这么白这么干净的房间。老男人,老男人的脸上有血……”
“天呀,她要打死他,她要打死他。”
三楼男人继续说:“刘兰花一边哭一边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男人到一个村庄,见个女人在坟头哭,男人问女人坟里埋的是谁,女人说:公公的孙子,丈夫的兄弟,娘的心肝,我的儿呀。那男人想半天,也没想明白坟里埋的是谁。”
母亲琢磨了又琢磨,突然一拍腿说:“天呀。天呀。”
“刘兰花说,她遇到的事比这个还过分呢。坟里埋的是谁呀?刘兰花遇到了什么事呢?”
是呀,刘兰花遇到了什么事情?刘兰花与老男人是什么关系?三楼的男人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可是我的父母似乎想明白了。他们商量着是否去报案,他们觉得眼下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上帝管辖的范围,非得找政府或是警察解决。但是没等他们做好决定,刘兰花、她的痴呆女儿连同那个老男人一同消失了。
父母得以进入刘兰花的房子,它果然像三楼男人描述的那样,从未见过的白,从未见过的干净。刘兰花竟是如此的爱干净,如-此-的-爱-干-净。
好人没有好命。父母一边看一边摇头。
从刘兰花家出来,父母就有了新心事,担心蹲圆石头的女人重新回来租这套房子。三楼的妻子同样担心,端着盆水在单元门口一遍一遍地洗手,三楼男人蹲在一边,一遍一遍地说:“放心吧,她不来,就是来,我也不会找她。我嫌脏呢,这样的女人谁不嫌脏。”
牟有树站在一边啮着牙笑,“脏,这个世上哪有干净的东西。你老婆的手天天洗,它们干净吗?如果干净,干吗要天天洗?”
事实证明,父母还有三楼女人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政府准备拆迁这片老住宅区了。拆迁的说法起码有五年了,没有人将它当回事,但是它一夜之间就来了,不断地有人上门送材料、讲政策,楼房的墙面上也写了大大的拆字。
我一直盼望老住宅区拆掉,父母得到一笔拆迁款后,我可以帮他们在新小区买上一套新房子。那样的小区有电子单元门,有保安,有电梯,有有钱的有文化的住户。
我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愿望,就是随着老小区、老房子的迁拆,这些隐蔽在生活表象下的,无法向人言说的,给人造成无尽伤害的幽暗、肮脏之事会随之一起被拆迁、被摧毁、被埋葬,取而代之是干净的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新生活。
这个时候,牟有树义务喂养的那些小猫全都不见了。那只丢失了孩子的老猫趴在墙脚,一声接一声地哀嚎。父母到地下室找了许多遍,也没有找到小猫,他们断定小猫被牟有树将拿到市场卖了。五只小猫,二十元一只可以卖一百元,超过他买小鱼的钱了。
父母去找牟有树,牟有树不说是他卖的,也不说不是他卖的,他只是嘴角挂着一丝冷笑,身子倚在门框上,一下一下晃荡着他的腿。
本栏责编 赵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