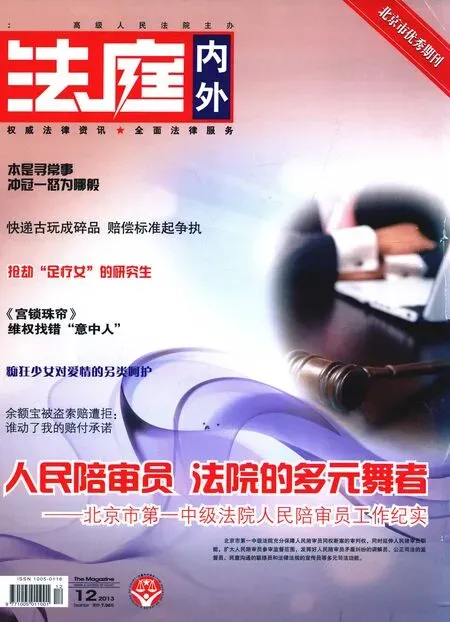余额宝被盗索赔遭拒:谁动了我的赔付承诺
文/胡小静
余额宝被盗索赔遭拒:谁动了我的赔付承诺
文/胡小静
新闻背景
余额宝是支付宝公司2013年6月份新上线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它一面世,即受到热烈关注。支付宝承诺:账户安全有保障,资金被盗全额补偿,万无一失。据中国经济网披露,2013年8月,两名用户因余额宝账户被盗,向支付宝提出索赔却遭拒赔。作为首例“账户被盗且遭拒赔”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热议。
支付宝“万无一失”宣传涉嫌虚假表示
支付宝·余额宝的官方主页上,详细列明了其种种优处:收益高;使用方便,可实时用于网上购物支付、转账等;安全有保障,资金被盗全额补偿,万无一失。
一般可以认为,“万无一失”是支付宝为吸引消费者的参与而作出的表示,特别是在官方网页上注明,更可视作支付宝对产品相关性能的表述。但是作为一项收益与其他金融产品相挂钩的金融理财产品,且由支付宝代为保管、管理的互联网账户,其收益风险与网络技术风险并存,再加上众多网络不可控因素,当真能“万无一失”?两名用户账户被盗即可视作打开了“万无一失”的缺口。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此处,支付宝公司将余额宝的安全性能描述为“万无一失”,刻意规避了对商品安全隐患的说明,甚至予以绝对化、模糊化处理,涉嫌违反法律规定的充分说明和警示义务。支付宝应在官方界面上,对余额宝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作警示说明,如基于网络技术风险及其他网络不可控因素可能导致用户的损失等等,并作出相应的风险提示,采用一定技术手段保证用户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
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网络商品经营者和网络服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交易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不得作虚假宣传和虚假表示。支付宝“万无一失”的宣传标语,容易让消费者自然认为这种产品毫无风险,从而作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经济决定。实际上支付宝对商品性能带有夸张,甚至虚假的表述,难逃“虚假宣传和虚假表示”之嫌,且已达到“引人误解”的程度,侵害了消费者对其购买商品全面、真实信息的知情权。
支付宝赔付条款法律效力值得商榷
虽然对用户宣称“资金被盗全额补偿,万无一失”,但实际上,支付宝已预见到余额宝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经济风险及责任承担问题,于是自制了赔付条款。《余额宝服务协议》(下文简称《协议》)规定:用户只有在不违反有关协议且不能归责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财产损失,才可申请补偿;能否得到补偿及具体金额取决于支付宝一方判断;用户须同意且认可支付宝最终的补偿行为并不代表用户资金损失可归责于支付宝,亦不代表支付宝为此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然而账户被盗事情发生后,在与支付宝交涉后,两名用户均获知其是在“可信网络环境下进行的操作”,不符合补偿条件,支付宝不负有赔付义务。不妨从法律层面来探讨以上支付宝自制赔付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
首先,用户申请赔付须满足“不违反有关协议且不能归责于自身原因造成财产损失”。支付宝应充分释明哪些事项为“不可归于用户自身的原因”,哪些事项为“可归于用户自身原因”,对界定双方责任而言,这是争议的焦点,应当以详细且可实际操作的标准予以界定。在账户被盗事件中,支付宝以“用户是在可信网络环境下进行的操作”为由拒绝赔付,但作为余额宝规则的制定者、裁判主体,当支付宝置身于具体纠纷之内,成为争议一方,其是否有权予以界定何为“可信且安全的网络环境”?支付宝此番拒赔,逃自定义赔付规则来推卸自身责任之嫌。
其次,支付宝宣称“能否得到补偿及具体金额取决于支付宝一方判断”。大而化之的描述,没有对任何实质事项,特别是赔付标准等与消费者权益重大相关事项的说明。《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网络商品经营者和网络服务经营者应按照公平原则确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采用合理和显著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权益有重大关系的条款,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据此,支付宝就赔付申请中的各项具体事宜,如争议事项的界定标准、责任划分原则、证据固定等举证内容,赔付办理流程和时限,赔付数额及具体计算标准等,应在公开页面上采用技术手段向公众作出明示,并做好咨询答复、释疑解惑等工作。
再次,《协议》规定:用户须同意且认可支付宝最终的补偿行为并不代表用户资金损失可归责于支付宝,亦不代表支付宝为此承担其他任何责任。这里需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支付宝强调其承担的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二是用户须同意且许可支付宝对自身责任承担的相关法律描述。看第一个问题,补偿责任与赔偿责任,虽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是天壤之别。一般认为,赔偿责任是相关主体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的赔付责任,体现的是对违反义务的惩罚。补偿责任则是相关主体在不违反相关义务的前提下,基于利益衡平的考虑,所提供的人道主义补救,体现的是公平负担的法理精神。借由这一字之转化,支付宝将自身责任形态巧妙转移,其角色定位也从纠纷一方,化身为案外之主体,可以说是将可能不利于自身的责任情形“择得干干净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支付宝自以为巧妙的责任设定,其实是排除了消费者法定的索赔权利,是有悖于法律规定的。第二个问题,消费者须同意且许可相应补偿不可归责于支付宝,且支付宝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此款明显是用户不得不接受的,支付宝借以限制、排除自身责任的免责条款。《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网络商品经营者和网络服务经营者提供电子格式合同条款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照公平原则确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得以电子格式合同条款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经营者义务、责任或者排除、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规定。支付宝此番对自身责任的限定,于消费者而言,是强加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定,有违自愿、公平及经营者与消费者权利责任对等的原则。所以,从法律规定及其内在的精神出发,探讨支付宝自制的赔付条款,只能说其法律效力如何,值得商榷。
用户维权主张遭遇多重困难
作为虚拟网络世界中的交易载体,余额宝呈现的特性迥异于现实中的实物商品,正是受制于现行法律规范、网络技术发展及消费者自身维权能力的制约,用户在自身权益受损后,其维权请求容易遭遇众多现实受阻因素。首先,侵权对象不明且难以追回损失。用户账户被盗后,其资金会被迅速转入别的账户,实践中并不容易直接找到真实的资金流入主体,侵权活动难以追踪到个人及向其主张索赔请求。而且对于账户被盗信息,用户未必能及时知晓,也就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事后救济,随着时限拖延越久,挽回损失也就越难。其次,救助渠道有限且难有成效。网络交易活动一般具有跨地域性的特点,侵权行为实施地与损害结果发生地难以精准界定,不便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实际上,其中一名用户账户被盗时身在老家,当其回到常住地报警求助时,警方以案件不在当地发生为由不予受理。除此之外,警方展开立案调查对损失金额也多有要求,现实中的小数额金钱损失多被排除在外,难以寻求公力救济渠道,只能单方面与支付宝协商交涉。再次,我国并未有健全的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很多关于证明事项、举证责任划分、证明要求等内容未有清晰界定,不能在双方出现纠纷时提供具体可行的裁判标准。再加上消费者个人金融法制知识的缺乏及获取、保存证据的能力较弱,在与享有优势资源的经营者对抗时,多处于不利地位,维权主张难以得到肯定。
互联网金融产品将纳入监管视野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作为互联网科技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载体,在制度监管与法律规范上显现出不明朗状态,难以界定其监管主体与法律规范依据。厘清互联网金融产品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系统安全风险,将其纳入国家总体的监管框架中去,并探讨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意义重大。前不久,国务院批示决定成立由央行牵头,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信部、公安部、法制办共同组成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研究小组,并已赴相关地方进行实地调研,探寻互联网金融业态的监管秩序与制度机制的建立。
责任编辑/项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