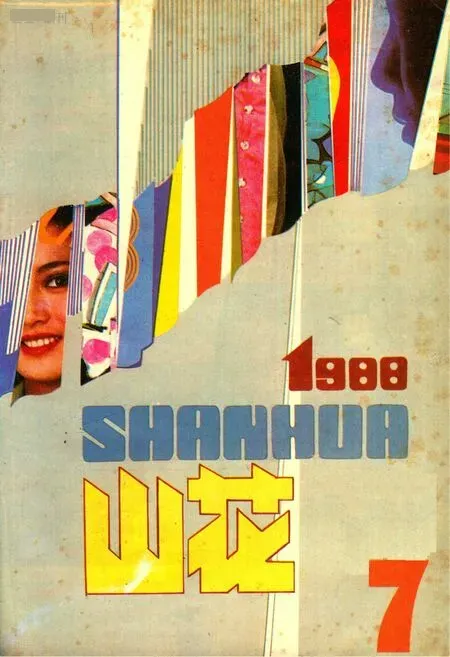当下诗歌:骑着木马赶“现实”——新世纪诗歌精神的考察
霍俊明
在当下的诗歌批评语境谈论一首诗歌并不难,甚至更多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容易。但是平心而论认认真真地读一首诗,负责任地评价一首好诗却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不仅与整个当下的诗歌生态相关,而且也与每个生存个体的困窘有关,更与如此广阔的差异性的“现实”有关。在我看来当下众多诗人的文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一个诗人的一首孤立的诗作,而是会牵涉到很多当下中国具有“特色”的诗歌现象、诗歌问题和“现实”境遇。在一个看起来加速“前进”的高铁时代我们诗人离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仍然在自我沉溺的木马上原地打转,而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是在追赶“现实”。由此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首首诗歌中的“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现实的内部”是如何不易。在一个“新乡土”写作已经成为热潮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在很多近期的诗人那里我强烈感受到了一个个所谓的“旁观者”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这“沉默”和那扇同样无声的“拒绝之门”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隐秘声部。诗人试图一次次张嘴,但是最后只有一次次无声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是对当下那些在痛苦和泪水中“消费苦难”的伦理化写作同行们的有力提醒。
这是一个飞奔“向前”的时代,但是同时那一块块钢化玻璃窗也模糊了我们内心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我们与窗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我们正在经受着去地方化的命运。那墙壁上一个个出自强壮的拆迁队之手的粗糙甚至拙劣的巨大的白色的“拆”字也在一同拆毁着族群的方言和地方的根系。而暧昧的时代“敌人”尽管不如极权年代那样如此具体和直接,但是更为庞大的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的规训和对手却让人不知所措。而吊诡的则是在一个“乡土”和“地方性”不断丧失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各个省份的文化造势(比如名人故里之争、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甚至连县乡的草台班子都在争抢所谓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过。仍有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现实”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当我们坦陈我们曾经一次次面对了那些“拒绝之门”,我们是否该侧身进去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沉暗的刺痛?尽管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寓言化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
当我们的诗歌中近年来频频出现祖国、时代、现实和人民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错觉和幻觉,即诗人和诗歌离现实越来越近了。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更多的关涉所谓“现实”的诗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样的仿写与套用,诗歌的精神重量已经远远抵不上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寓言化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很多作家想象能力的极限。而在此现实和写作情势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写作有更为辽阔的可能?而在一个“非虚构写作”渐益流行的年代,诗歌能够为我们再次发现“现实”和“精神”的新的空间吗?作为一种文本性的“中国现实”,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境遇和困难。也许,诗歌的题材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伪问题,但是令人感到吊诡的却是在中国诗歌(文学)的题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个大是大非的背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会牵涉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想象。新世纪以降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显然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诗歌中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经远离了现实,或者它们早已经死去。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仅诗歌在介入,而且小说、散文甚至时下最为流行的“非虚构”文本也在轮番上演着“乡村”叙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众多的相关文本就为写作者们设置了极大的难度。换言之,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
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在现实和写作面前,诗人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的诗歌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具有“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吗?曾记得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陈红旗作品-人像局部4
在时代匆促转换人们都不去看前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在一个极权时代远去的当下,我们的生活和诗歌似乎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生活和诗歌的迷津中自我搏斗。我们的媒体和社会伦理一再关注那些日益耸起的高楼和城中村,一再关注所谓的农村和乡土乃至西部,但是我们的诗人是否足以能够呈现撼动人心的具有膂力的“原乡”和“在场”的诗句?我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新世纪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艰难。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与此相应,我们每天与那些看起来无比真实和接近现实的诗歌相遇,但是他们几乎同时走在一条荒废的老路上。我们的当下有那么多的艰难情势被我们的诗人可怕地忽略,与此还有那些更为斑驳不自知的灵魂渊薮。我们的诗歌都成了自我的关注者,个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体验从来没有在诗歌中变得如此高调和普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
在我看来,当下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成为带有伦理化倾向的一种潮流和趋势。面对当下中国轰轰烈烈的在各种媒体上呈现的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似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换言之中国正在成为“寓言国”。首先应该注意到目前社会的分层化和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多层次性,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甚至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歌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和个体命运的复杂程度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诗人的虚构的限阈与想象的极限。诗人们所想象不到的空间、结构和切入点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诗人和作家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受到空前挑战。由此,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会“奇观”和现场事件的媒体直播,我们的诗歌和文学还留下什么能够撼动受众的特异力量?在此情境之下,写那些“现实”性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相反,我们涉及到属于更小范围内的诗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图景时,其可能性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反倒容易些。所以,我们也据此应该重新认识以往的一个怪论——诗人只对自己负责,不要写什么重大题材和现实题材。
从整体上而言与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热议现象、重大活动和民生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诗歌数量是相当庞大甚至是惊人的。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加之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软实力的角力和宣传活动也需要文学和诗歌的鼓吹,诗人们似乎与“现实”的胶着关系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贴近和激烈过。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小的危机。但是是否如一位诗人所偏激地强调的“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
而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进当代的诗歌写作,我们最终会发现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当下的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的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换言之,诗人试图反映现实和热点问题以及重大事件时,无论从诗歌的材料、构架、肌质还是诗人的眼光、态度和情怀都是有问题的。
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诗歌是通往现实的入口。这个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
由此我想到了很多诗人文本中的“城市”、“小镇”、“乡村”和一个个陌生的“地方”。以这些“地方”为圆点,我们在多大的范围内看到了一种普遍化而又被我们反复忽略不计的陌生性“现实”的沉默性部分。这一个个地方,除了路过的“旁观性”的诗人和当地的居民知道这个地方外,这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陌生的角落——一再被搁置和忽略的日常。而我们早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异乡”和“外省”让诗人无路可走。据此,诗歌中的“现实”已经不再只是真实的生存场景,而是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地理学场域携带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和挽歌性。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深山褶皱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个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现实”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而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镇和曾经的农耕历史被不断迅速掩埋的“新文化”时代,一个诗人却试图拭去巨大浮尘和粉灰显得多么艰难。而放眼当下诗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们毫无精神依托,写作毫无“来路”。似乎诗歌真的成了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时代个体的精神把玩和欲望游戏。在一个迅速拆迁的时代,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也不能不是分裂和尴尬莫名的。因为通往圣洁的“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渊薮之上的独木桥所取代。当我们胆战心惊终于下定决心要踏上独木桥的一刻,却有一种我们难以控制的力量将那根木材抽走,留下永远的寒风劲吹的黑暗。语言的温暖和坚执的力量能够给诗人以安慰吗?过多的时候仍然是无物之阵中的虚妄,仍然是寒冷多于温暖,现实的吊诡胜于卑微的渴念。当然我所说的这种“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出生地”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迷茫而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由此,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现实感”的诗歌写作的缺席则成了显豁的事实。

陈红旗作品-人像局部5
然而,更为令人惊惧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永远失去的。多少个年代已经在风雨中远逝,甚至在一个拆迁的城市化时代这些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一切都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而那些当年的车马早已经销声匿迹。幸运的马牛们走进了坟墓之中,不幸的那些牛马们则被扔进了滚沸的烹锅之中。那些木质的轮车也早已经朽烂得没了踪迹。我们已经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些已逝之物,我们只能在灰蒙蒙的清晨在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偶尔看到那些从乡下来的车马,上面是廉价的蔬菜和瓜果。而我们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听到这些乡间牲畜们吃草料的声音,还有它们温暖的带有青草味的粪便的气息。说到此处,我也不由有了疑问。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怀乡者并不难,这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写作的惯性气质。但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却会使得“怀乡者”的身影又过于单薄。“历史”和“现实”更多的时候被健忘的人们抛在了灰烟四起的城市街道上。我们会发现,在强大的“中国现实”面前历史并未远去,历史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相反历史却如此活生生地出现在被我们反复路过却一再忽视的现实生活里。这多像是一杯撒了盐花的清水!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这杯水的颜色——与一般的清水无异——但是很少有人去喝一口。颜色的清和苦涩的重之间我们的人们更愿意选择前者。而诗人却选择的是喝下那一口苦涩,现实的苦涩,也是当下的苦涩。当然,还有历史的苦涩!而诗歌只有苦涩也还远远不够!
“一无所知”的“过客”性存在,实际上是每个生命的共同宿命性体验,同时人的认识和世界是如此的有限而不值一提。而在当下的时代,这种遗忘性的“一无所知”还不能不沾染上这个时代的尴尬宿命。我们自认为每天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我们仍然对一切都所知甚少,甚至有些地方是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最终到达的。有的地方我们也许一生只能经历一次。“单行道”成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诗歌的最后部分提升了整首诗的空间高度和视阈广度,从而避开了类同题材的粘滞和表象化处理。
“中国的一天”应该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走得却是如此艰难和漫长。因为它所牵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观感,而是牵涉到整个中国的现实,还有诗人的精神现实。我们所见太多,遗忘也太多。我们在隔着车窗高速度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双脚和内心都同时远离了大地的心跳声。我们在城市化的玻璃幕墙里只看到同样灰蒙蒙的天空,我们最终离那些“远逝之物”越来越远,直至最终遗忘。是的,多少年代,多少车马,都已经远去了!还有那沉默的巨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