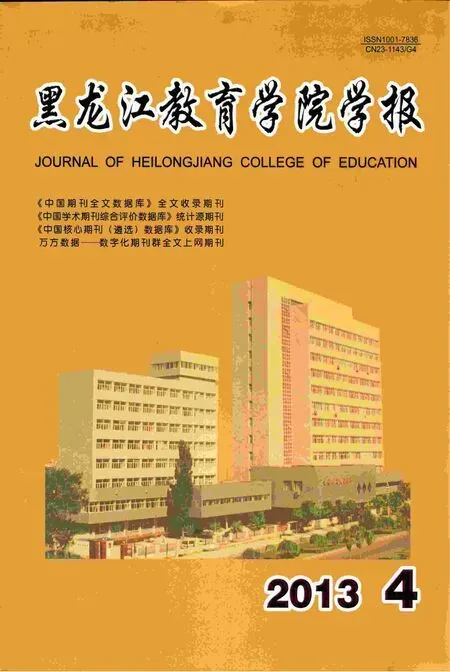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国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150010)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发展
“女性主义”一词起源于1880年第一次法国妇女参政权会中提出的“feminisme”。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并逐渐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在争取公平的选举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政治实践中,人们发现了从文化领域打破父权社会语言体系赢得女性说话权利的重要性,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口号。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者首先将女性主义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开启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之先河。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竭力汲取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力量,极力谋求译者和女性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西蒙指出:“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比喻。女人和译者同被纳入话语的低等地位。”[1]
在西方尤其是加拿大,戈达尔德(B.Godard)、弗洛图(L.Flotow)、哈伍德(S.Lobbiniere-Harwood)等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原作者充分合作,将原作中为实现其政治意图而采取的激进写作策略,在英文中体现出来,使翻译“扩张并发展原作的女性主义意图”[2]。译者在实践中从女性主义独特视觉出发,主动改变女性和译者自古以来的隐形、被动、边缘地位,力图达到“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以维护女性尊严和权力为目的,通过否认传统二元对立思想中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地位,否认传统翻译标准中的模仿论、“忠实”论及女性化隐喻。
(二)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是在女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翻译的结合是从传统意义上人们把译者地位比喻为女性的边缘地位入手,彻底解构男性费斯勒文化,旨在推翻将译者看做“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观点[2]。女性主义翻译认为译者的创作属于“一项读者和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翻译活动不是两种语言间的机械转换,译者的意识形态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语境因素都对其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其翻译观点可主要概括为:(1)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消除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地位;(3)翻译不但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3]。
在翻译实践中,弗洛图(Louise Yon Flotow)指出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是女性主义翻译惯用的干涉文本方式,通过这种颠覆性的创造性活动确立自身主体身份。
然而,从该理论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批评,评论者对女性主义翻译者对原著的过度改写与劫持提出反对意见,并质疑其对解构主义应用是出于偶然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被他们归结为以女性主义政治权利斗争为目的的过激性理想化行为,其中翻译作品也被认为歪曲事实过多,使读者得不到应得的效果,偏离了翻译者的本职。女性主义翻译内部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为不同流派。并且女性主义翻译“太过情绪化、宗教化、理想化和主观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4],女批评家阿茹雅(Rosemary Arrojo)提出了女性主义翻译中存在着“机会主义”(opportunism)、“虚伪性”(hypocrisy)和“理论的非连贯性”(theoretical incoherence),分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非理性地进行政治参与、采用双重标准的激进态度,其理论主张具有矛盾含混的特点[5]。
无论如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现实语境层面背后意识形态及语言建构的关注给翻译研究带来了突破性的转机。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理论,在批判其不足与缺陷的同时致力于为其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构架,从而更好地应用到翻译实践中。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在翻译界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于21世纪初介入中国。该理论向中国的传入势必对中国翻译界产生巨大影响,但进入中国后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否依旧保持其原始味道?本文试图通过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观点阐述其涉足中国后产生的变化。
赛义德曾最早在1982年出版的《拉里坦季刊》(Raritan Quarterly)中提出:“理论旅行”理论,指出“与人和批评流派一样,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性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6]在该观点中,赛义德将理论旅行分成四个阶段:首先,使观念得以产生或进入话语的环境。第二,使观念的重要性慢慢凸显的通道。第三,使观念得以接纳或容忍的条件。第四,使观念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而进行的改造。
正如赛义德“理论旅行”理论所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行至中国的途中也受到了中国文化背景环境的挤压和改造。首先,从大量有关研究在核心期刊上的发表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探索都说明该理论在中国翻译界的接纳程度。对于该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孔慧怡、费小平、刘亚儒、王晓元、孟翔珍、杨柳、徐来、张景华、廖七一、穆雷、刘军平等人。
在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初始阶段,穆雷注意到译者性别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7]。廖七一开始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8]。真正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从2002年才真正开始,在全国的期刊上开始集中发表女性主义翻译的相关文章。
2005年开始,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开始呈现出比较快的增长势头。纵观近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最初的以评介为主,到对女性主义翻译进行梳理,再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化运用,经历了从介绍到综述批评,再到借鉴发展,进行本土化研究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视角分别从译者的身份、女性主义翻译的本质、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女性译者主体性研究、生态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等方面展开多角度的探讨,为拓宽翻译研究的视角以及其他翻译模式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此外,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在研究深度上不断进行挖掘。在探讨译者主体性方面,从以往关注译者到关注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从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译者到翻译过程中男性译者的双性视角,角度的拓展和层面的深入,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和完善。
然而,该理论从一种文化迁徙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经历的碰撞与冲突也使其磨掉了部分政治激进思想的棱角,并始终处于边缘文化地位,不能彻底被主流翻译思想接受并运用。究其缘由,要从女性主义东西方不同发展状况及中国千年历史背景文化方面进行追论。
西方女性主义自诞生伊始便旗帜鲜明地追寻女性独立及平等地位,并在多次有规模、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中赢得女性解放,从父权制社会牢笼中的解放,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与此不同的是,由于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的桎梏及对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压迫,女性意识在中国要羸弱温和许多。另外,由于政治体制及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集体意识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不能像西方女权主义那样从真正的政治运动等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的女性主义思想。因此,单从五四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并不足以使中国女性产生如同西方女性一般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的译者和译论研究者无法像接受并投身女性主义运动的西方译者和译论研究者那样,自觉地将性别同翻译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
因此,在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忠实”主流仍不能被彻底改变,从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提出的对原文“操纵”、“控制”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运用到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之中。虽然西方激进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一面也未被吸收进来,中国女性译者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倾向于改动原文选词和语调来表达其性别意识形态,并特别倾向于女性作品的翻译传播,有意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以挖掘其中潜藏的女性主义思想。
三、结语
由于发展形式及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吸收了部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改变并丢掉了部分不适合目前国内翻译背景的内容。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前往中国之旅并未终结,该理论的发展需要译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输入它新鲜的理论养料,使该理论在中国得以发展下去。
[1]Simon 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2]Godard Babara.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C]∥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r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90.
[3]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
[4]Flotow 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M].Manchester.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97.
[5]Arrojo Rosemary.Feminist,“Orgasmic”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Their Contradiction[J].Tradeterm,1995.
[6]赵建红.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与越界”说探讨[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7]穆雷.心弦——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1999,(2).
[8]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